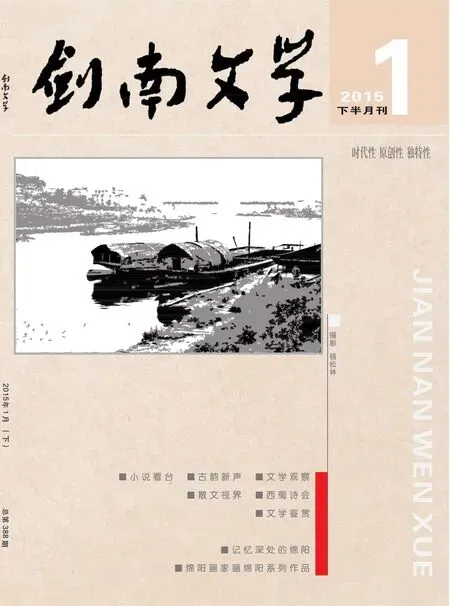嚴羽《滄浪詩話》興趣說和妙悟說的話語權
■羅太穎
引言:《滄浪詩話》是宋代最重要的一部詩話,提出有關詩學理論的著名論說。詩人通過自身在學詩與品詩、作詩的體悟中,提出了 “興趣”和 “妙悟”說來闡述自己獨特的詩歌理論,還將興趣說和妙悟說引入宋元詩歌美學中,宋元詩歌美學比較注意審美意象本身的分析。
“話語權”簡單說就是影響力。在文壇里話語權影響著文學的走向。話語權不僅是文學的專屬,也是文化與傳媒研究中的常用詞。有葛蘭西的 “領導權”、福柯的“權力話語”、哈貝馬斯的“合法化”、羅蘭·巴特的 “泛符號化”等話語極大地豐富了美學理論,為研究者提供了理論基礎.隨著文學的發展,滲透力越來越強。話語權也指其他的話語,本文主要討論的是詩歌美學方面的話語權。
一、興趣說的內涵及話語權
文學話語權是在特定的歷史時期形成并逐漸盛行,興趣說就是在這樣的時期形成的,嚴羽對于“興趣”這個概念的闡述,主要出處于這段:
“夫詩有別材,非關書也;詩有別趣,非關理也。然非多讀書、多窮理,則不能極其至,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有盡而意無窮。”(《滄浪詩話.詩辯》)
在南宋初期,蘇、黃詩盛行一時,尤其是江西詩派的影響尤為顯著,他們崇尚形式的理論和創作,引起世人的不滿。嚴羽的 《滄浪詩話》展開了批判和抨擊。為什么能進行有力的批判?除歷史和社會因素,他提出了重要的詩歌理論 “興趣說”并在詩歌中推廣盛行,而且為人們所接受。她的中心范疇是“興趣”。什么是“興趣”?有人說“興趣”就是藝術形象,是 “意境”。我認為是有所牽強的,在這段話中,“興趣”、“別趣”、“興致”基本上是同一個概念。這個很容易理解,這與“賦”“比”“興”中的 “興”這個理解明顯是相關的。“興”就是詩人對于外物的感受,引起詩人情趣的感發,這種感發是感性的觸發,單單說 “興趣”是“意境”就有些勉強。興的表現比較淺隱,因為 “興”在古代詩論中有多種解釋。例如 《文心雕龍.比興篇》說“興”是起興依微以比擬,鐘嶸 《詩品》說:“文已盡而意有余,興也”。他說的“興趣”,就是從“興”的本義伸展出來的范疇,指詩人對對象所發的情感。這種審美情感是由外物自然而然發出來的,而不是理性特意編排的。“興趣”和 “興象”這兩個概念都和 “興”的美學本意相聯系,但它們的涵義有所不同。“意象”的感觸是 “物”對于“心”的一種自然的觸發。殷潘標舉 “興象”,特別推崇盛唐詩歌,嚴羽標舉 “興趣”,也特別推崇盛唐詩歌,就說明了這一點,也就有了當時在詩歌美學方面的話語權。
“興趣”是詩的生命,一些詩人卻不理解其中的意義,他們 “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其作多務使事”,“用字必有來歷,押韻必有出處”,其結果是破壞了 “興趣”,破壞了審美意象。嚴羽竭力要把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區分開來,所以他強調:“詩有別趣,非關理也。”“所謂不涉理路、不落言筌者,上也。”強調的理論說教、堆砌事實、雕琢詞句,都不是審美情趣,這是我們在一般的詩歌學習中也有同樣感受,沒有審美情趣,也就不能產生審美意象。反過來,有了審美情趣,就有可能創造精妙的審美意象,集聚豐富而又力量的詩歌話語權,對江西詩派的抨擊又有力又到位。
二、妙悟說的內涵及話語權
嚴羽既然強調 “興趣”是詩的生命,他認為詩歌意象在審美感興中產生,他稱之為 “妙悟”。他說: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然悟有淺深、有分限、有透徹之悟,有但得一知半解之悟。漢、魏尚矣,不假悟也。謝靈運至盛唐諸公,透徹之悟也。(《滄浪詩話.詩辯》)論詩如論禪,禪道在妙悟,詩道亦在妙悟,只有創作中對前人作品和作詩過程深入理解和感受,才能寫出言有盡而意無窮的詩作。“妙悟”是指 審美感興,也就是指在外物直接感興下產生審美情趣的心里過程。這是構成詩人的本質的東西,所以說:“惟悟乃為當行,乃為本色。”“妙悟”是一種感性的、直覺的觸興,它與每一個人的學歷并無必然的聯系。嚴羽又把這種“妙悟”的能力稱之為“別材”。他說:“詩有別材,非關書也”,“且孟襄陽學力下韓退之遠甚、而其詩獨出退之之上者,一味妙悟而已”。這是一個深刻的區別。當一個詩人在創作的時候,他要擺脫現實東西的束縛,擺脫抽象思維,讓整個生命直接去體悟,去把握對象。一個人的審美感興能力同一個人的學歷確實是性質不同的兩回事。比如多出于勞動人思婦之口,他們不一定是讀過多少書,但是他們的審美感興能力卻很高,反過來,讀書多的人,審美感興能力并不一定就高。
但是,一個人的學歷與他審美感受能力并不是相斥的,在一定條件下是可以和諧統一的。大學問家固然未必就是大詩人,大詩人卻往往是大學問家。這一話語權的形成,豐富了他的詩歌理論,也在那個時期有強力的話語。
三、興趣說和妙悟說的區別和貢獻及它們話語權的影響
嚴羽說的“興趣”,與宋代詩論家經常談的“情”和 “景”這對范疇中的“情”,并不是完全是一個概念。差別主要有兩點:第一,“情”的意義不僅有寬度也有廣度,有審美的情感,也有非審美的情感;“興趣”則專指趣。第二,“情”不朱總產生的源頭及過程;“興趣”注重,指明情趣是由外物形象直接感發的,即從 “妙悟”中產生的。他的興趣說和妙悟說,在美學史上是有影響的。興趣說的主要貢獻在于聯系,把意象和感興緊密聯系來,從最本真的感興出發,對詩的意象 (主要是其中的“情”)作了一些重要鋪墊。妙悟說的貢獻主要在于分離,把感興和一般邏輯思維區分開來,注重感興是構成詩人本質的東西,從而對詩人的什么創造力輕輕作了一個潛在的范圍。《滄浪詩話》是最有理論彈性的詩話,為什么說是彈性?它沒有把審美框釘住,才能在中國古代詩歌理論上占有一席之地。說是彈性的詩話有點勉強,但能很全面的詮釋這部詩話的精髓,它的總綱,“興趣說”和“妙悟說”等是其精義所在。它的爭議也最多,在古代能有一部這樣的詩話備受爭議的作品,對于文學審美有一個全新的呼吸。受爭議的作品,生命力越能顯現,經過時間的洗禮,它是有位置的。
它的話語權影響主要表現在,第一,在宋代時期,影響最深,雖有不足之處,但它進入人們視野并被討論。一部文學理論著作,當被人們開始討論時,爭議越多,說明越有生命力。第二,對后面美學家的影響,特別是對王夫之和葉燮的影響。王夫之的文藝批評著作 《姜齋詩話》、《古詩評選》、《唐詩評選》、《明詩評選》,動靜學說,還有關于“勢”的文學理論,王夫之提出了一整套很有見地的詩歌創作理論,“勢”便是其中一個重要范疇。“把定一題、一人、一事、一物,于其上求形模,求比擬,求詞采,求故實;如鈍斧子劈櫟柞,皮屑紛霏,何嘗動得一絲紋理?以意為主,勢次之。勢者,意中之神理也”。他認為文意是第一位的:“意猶帥也。無帥之兵,謂之烏合”,那么無意之文也就是濫造之文了。對葉燮的影響體現在他的 《原詩》上,葉燮在 《原詩》中討論了詩歌歷史發展的規律,提出了文學變化發展的 “正變”說。他認為文學是向前發展的,不能走文學復古的老路,文學的發展和變化是一種必然的趨勢。他說:“蓋自有天地以來,古今世運氣數,遞變遷以相禪,……此理也,亦勢也,無事無物不然,寧獨詩之一道膠固而不變乎?”葉燮的這種樸素的唯物主義發展觀,從總體上把握了文學應該是變化發展的,一代文章應該比一代文章強,但文學發展變化有時也很復雜,不能一概而論。但是它的話語權也越來越多,越來越有爭議,引起后面美學家的更多思考,影響著一個時代的文學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