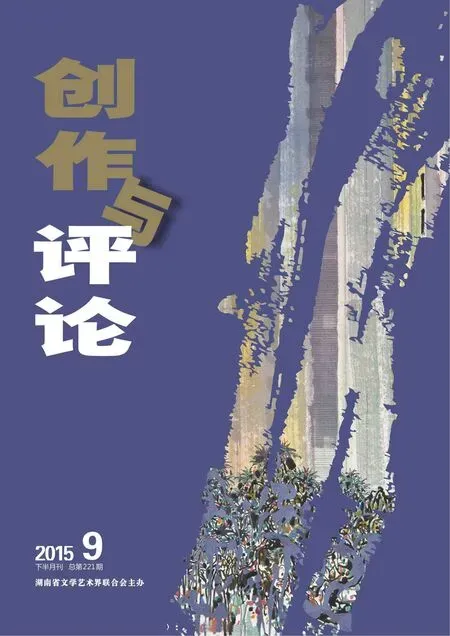三十年后說“尋根”
——韓少功訪談錄
○佘曄
三十年后說“尋根”
——韓少功訪談錄
○佘曄
編者按:一個時代文學思潮的產生是特定歷史時期的社會思潮、歷史經驗、社會心理等在文學上的反映。1985年“尋根文學”思潮的誕生便是當時知青一代文人集體經驗的表達。三十年后,這一思潮在現代性語境下又形成了新的文學經驗并構成對歷史的現代性回應。在“歷史/現實”的話語鏈條與“在場/不在場”的話語張力所建構的“后尋根”文學場域中,重讀“尋根文學”便有了學理的支撐和文學史的指歸。本刊特辟“重讀尋根文學”專題,以歷史當事人的追憶反思為基點,對產生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并對當代文壇產生重大影響的“尋根思潮”進行高潮褪去后的宏觀把握和微觀透視,立足“文學之根”,回歸“文學本體”,敘述“歷史經驗”,重塑“現代話語”,根植當下,其意義就是文學本身。
佘曄:非常高興能和您以訪談的形式重讀“尋根文學”。不少學者認為,1984年11月在杭州128陸軍療養院召開的文學討論會是“尋根文學”出現的重要契機。您當時是為數不多的與會作家之一。您能不能跟我們回憶一下會議召開的基本情況和您當時的發言內容?與會作家、評論家當時談論的文學話題有哪些?爭論的焦點是什么?
韓少功:那次會議有一批活躍的作家與批評家參加,談及的話題也多種多樣。與會者周介人有一個簡約的記錄,曾發表在多年后的《文學自由談》雜志,其余的記錄好像至今未見。從那個提綱式的記錄來看,文學“向內轉”、現代主義、反思“傷痕文學”等,都是熱門話題。本土文化傳統也是話題之一,就此發言的好像有李杭育、李慶西、阿城、李陀等,還有我,但從發言比例來看,這個話題并未占有主導位置。在后來有些人的描述中,好像有一個“有組織、有綱領、有預謀”的“尋根運動”在這次會上閃亮登場,其實是夸大了。還有些后人津津樂道“先鋒派”與“尋根派”的兩條路線對峙,更屬無中生有。事實是,當時與會的新派人士親如一家,對阿城、馬原等人的新作都是齊聲叫好,沒出現過爭論。大家共同的興奮點,主要還是如何擺脫那種僵硬化、圖標化的政治小說模式,覺得當時很多“傷痕文學”“改革文學”作品,不足以擺脫這種舊模式。
佘曄:在您看來,批評家們用“尋根”一詞來解讀您的文學主張,與您的本意有一定的差距。但談及“尋根文學”,必然繞不開《文學的根》這篇產生重大影響的短文。您能談談當時寫作這篇文章的初衷是什么?靈感來自哪里?主要想理清什么問題?
韓少功:杭州會議后,恰逢《作家》雜志約稿,我就把會上的發言略加擴充,寫成了這一篇,強調作家在目光向外的同時,也要目光向下,不能脫離本土文化傳統的根基。“文革”中流行“橫掃四舊”,“文革”后流行“全盤西化”,雖然政治方向逆轉,但前后雙方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恨不得給中國整體上來一個“文化大換血”。我對此非常懷疑。第一是可不可能“大換血”?第二是即便能夠“大換血”,其利弊得失到底如何?“五四”運動以來無論“左”“右”的文化激進主義,在這個問題上都很任性,包括胡適、魯迅等新文化旗手,都曾主張廢掉漢字,現在看來當然是太簡單化了。把蘇俄現代化或歐美現代化的模式,當作中國只能復制和照搬的必由之路,看來也太天真了。文化自卑作為文化自大的倒影,是窮國最常見的通病,是國門開放過程中繞不過去的坎。從五四運動到新時期,這個“坎”困擾了國人近一個世紀。《文學的根》算是從文學角度捅破了這個話題。后來有人說,這實際上是新時期對創新“中國道路”的最早涉及,比法學、經濟學、社會學等學科的類似討論早了一、二十年。
佘曄:《文學的根》有著理性的清醒與自覺,它與您的《爸爸爸》《女女女》《歸去來》等一系列優秀的尋根文學作品有著怎樣的關系?您認為當時這種“尋根”意味濃厚的作品產生的歷史契機是什么?它的社會語境有哪些?
韓少功:觀念歸觀念,作品歸作品,我從來不認為一個好觀念就能孵化出一窩好作品。沒這回事。不要相信這種“創意工廠”。文學除了“根”,還有葉,還有枝,還有水土和氣候……條件一二三四五湊齊了,才會有一個好作品,某個觀念充其量只是其中原因之一。被稱作“尋根”作家群體的通常多用鄉土題材,喜好本土文化元素,如此等等,但具有這些識別標志的作品,很多也是垃圾呵。正像“先鋒派”和“寫實派”,也有很多垃圾。這就是我更愿意談具體作品、不愿意談“派”和“主義”的理由。有些批評家總是喜歡把文學史描述成一種“團體賽”,各有旗幟和統一制服的那種,其實與實際情況相去甚遠。
佘曄:您又怎樣看待自己與其他尋根作家之間的共同性和差異性?
韓少功:所謂“尋根作家”,大部分是有鄉土經驗的人,特別是一些具有“下鄉知青”或“回鄉知青”經歷背景的人。他們在敏感的青春期游走于城鄉之間,感受到文化的斷層、裂變、震蕩、撞擊,有很多故事和心情需要釋放。這算是一個共同點。當然,有的對鄉土充滿厭惡,有的則充滿同情;有的執著于思考,有的則來一把玩味;而且不同態度中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有不同的主體精神配方,勾兌出不同的寫作效果。但他們都形成了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對話關系,構成了全球化時代里來自發展中國家的一些重要的精神回應。至于我的作品,自己說了不算,可能是旁觀者清,得由別人去說。
佘曄:三十年前,您就提出:“文學的根應該深植于民族傳統的文化土壤之中,根不深,則葉難茂。”經過三十年的發展,您覺得咱們現在的文學算是根深葉茂了嗎?如果有欠缺,當下應該怎樣“尋根”?或者說,當年懸置的問題如何尋找一種更好的解決辦法?
韓少功:這事還遠遠沒有完。這種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對話還將深入、廣泛并且艱難地進行下去,直到像錢穆先生說的,要到東、西方經濟發展水平接近的時候,文明的比較和文明的對話才可能心平氣和、實事求是地展開。到那時候,熱衷“復古”或熱衷“西化”的膚淺情緒,文化自大或文化自卑的扭曲心理,才可能被大體上打掉,理性和智慧才可能最大化。但即便到了那時候,也沒有文學“根深葉茂”的必然性。市場化所催生的消費主義,互聯網所催生的文化生態巨變……也都構成了對文學的重大挑戰,其它問題還多著呢。我們所說的“根”,也許是文學發展的一個必要條件,但并不構成全稱條件和充分條件。比如現在有些作家最要命的問題,是不認真寫了,是成為市場奴隸了,“尋根”這貼藥能管什么用?再好的眼藥或者耳藥也治不了心臟病吧?
佘曄:韓老師,您一直不太認同批評界賦予您的“尋根”作家標簽,也沒預想《馬橋詞典》竟在九十年代的文壇產生軒然大波,成為許多人觀察九十年代文藝思潮、文學批評、學術風氣、文學接受的機會。您認為作家與批評家之間需要怎樣的一種解讀機制和相互激發?能否談談您對當下文學批評的一些看法?
韓少功:批評家最好要有一點創作經驗,作家最好要有一點理論修養,而且雙方都得有一些摸爬滾打的生活底子。這樣事情就好辦些。當然,做到這一點很難,與現有的教育體制、學術體制有沖突,與“應試教育”、學歷崇拜、邏各斯霸權格格不入。把文學知識當作文學,是有關教育的最大誤區。把文學觀念當作什么靈丹妙藥,是有關批評的最大誤區。可惜有些作家也樂意制造這樣的誤區,以便把自己的泡沫或垃圾包裝得有模有樣。不過,創作與批評如果不能“互相激發”,也沒太大的關系吧。《紅樓夢》一直被太多批評家誤讀,天塌了沒有?地陷了沒有?惡劣的批評環境只能誤導三流作家和三流讀者,對有主見、有定力的人從來不會有什么影響,文學的地火照樣運行。
佘曄:在全球化的語境中重讀“尋根文學”,您怎樣看待這種重讀與新啟蒙主義和后現代性話語的某種關聯?
韓少功:什么是“新啟蒙”,什么是“后現代”,可能歧義會太多。我們不如說,隨著中國與外部世界更深度的融合和互動,隨著“道路自信”“文化自信”一類話題應運而生,廣義的“尋根”其實已遍地開花,甚至進入了民眾的日常生活。連《三字經》《弟子規》眼下都在中小學大舉卷土重來,甚至進入商業化炒作,“尋根”還用得著再說嗎?回頭來看,三十年前的那一場文學討論,推動作家在政治視角之外增加文化視角,在對外開放時重視本土國情和傳統資源,對全球的文化版圖和文明流變有更多了解……當然是整個過程的一部分。在地圖上掃一眼,那些全面復制和大舉克隆西方宗教、教育、文字、政體的發展中國家,像非洲、南美州、南亞、東南亞的很多地方,一直在“大換血”的地方,至今還陷于貧困和動亂。看來中國很可能走上另一條路,有些孤獨、費解卻讓某些人士惶恐不安的路。“尋根”就是發生在這個全球背景下的一個小事件,如此而已。
佘曄:不可否認,“尋根文學”是“新時期文學”發展中的第二次高潮,是“新時期文學”走向多元化的一個標志性開端,借1985年的“文化熱”完成了與“宏大敘事”的疏離,在創作上存在多種可能性和內部多樣性。也許,高潮褪去,歷史的距離與檢驗讓這種多樣性、豐富性變得更加清晰和明朗。您能否為大家解讀一下“尋根文學”思潮的歷史地位以及這種重讀的當代意義?
韓少功:“超現實主義”當年出現在歐洲,它并不能使卡夫卡們生生不息。“魔幻現實主義”當年出現在拉丁美洲,它也沒法讓馬爾克斯傳人輩出。歐洲和拉丁美洲眼下也是文學低谷期么。任何文學現象都不是文學的全部,而且都是緣聚則生,緣散則盡,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時水土養一時的人”,沒有什么持續升級不斷擴張的一條直線。“高潮褪去”太正常了,而且下一個高潮肯定不是前一個高潮的重復。我可能更關注創作,因此更愿意盯住下一個高潮的可能性,包括它的條件、動力以及種種跡象。至于過去了的事情就讓它過去吧,交給文學史家們去說可能更好。作為當事人之一,我喜歡向前看,對有關歷史評價從來不在意。
(作者單位:湖南省文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