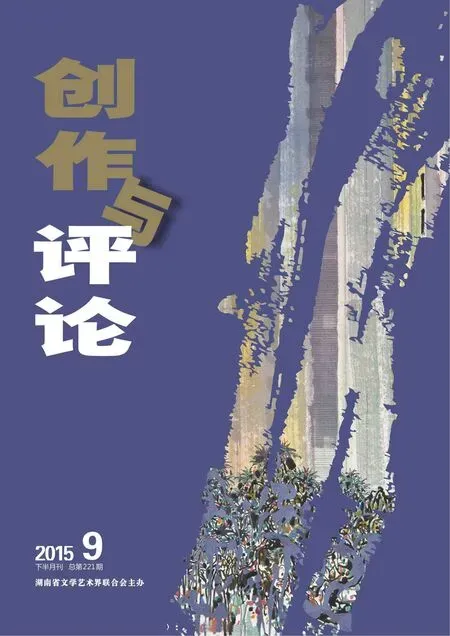侯孝賢“新電影”的個體關懷與藝術精神
○ 劉于鋒
侯孝賢“新電影”的個體關懷與藝術精神
○ 劉于鋒
在大眾電影的商業化和娛樂化的發展到極致且言必票房的當下,一部電影似乎只有擁有足夠的娛樂性和高票房紀錄才算是成功。而作為臺灣新電影領軍人物的侯孝賢,其電影在20世紀80代以來形成了以電影的藝術性為主要追求的風格,這與商業化、娛樂化格格不入,以至于被認為“他的作品屬于近三十年來最難取悅這個世界的電影……藝術電影和大眾電影的類型日益融合,而侯孝賢的作品通常抗拒這種妥協”①。侯孝賢也被一些論者認為:“只重視電影的藝術性、實驗性和思想性,卻漠視電影的通俗性、觀賞性、娛樂性及商業性”。②但這恰恰證明侯孝賢電影對藝術精神和文化品格的自覺追求,包括對個體生命的關懷和對時代精神的展現、對生存成長體驗的表現、對日常生活細節的記錄、對情節淡化的處理和敘事的詩化表達,體現了作為臺灣新電影代表人物的藝術追求。
一、個體關懷與時代展現
從侯孝賢電影風格的轉變上來說,20世紀80年代初期的《就是溜溜的她》(1980)、《風兒踢踏踩》(1981)、《在那青青河畔草》(1982)幾部作品,主要表現青年男女主人公的愛情,總體上的情感基調清爽歡快,敘事線條簡單流暢,音樂設置清新悅耳,再加上偶像派演員鳳飛飛、鐘鎮濤等,取得了較好的商業市場,被稱為“商業三部曲”③。因而這一時期電影被稱為“前新電影”④,是侯孝賢新電影運動之前電影的風格。自1983年至1993年期間的作品,包括《風柜來的人》(1983)、《冬冬的假期》(1984)、《童年往事》(1985)、《戀戀風塵》(1986)、《尼羅河女兒》(1987)、《悲情城市》(1989)、《戲夢人生》(1993)是侯孝賢發生轉折的重要時期,通過長鏡頭的使用,主要表現對生命個體的關注與“自然法則”下人的生命進程,特別是《悲情城市》獲得第46屆威尼斯國際電影節金獅獎,《戲夢人生》獲得第46屆戛納國際電影節金棕櫚獎,被認為是達到了巔峰高度。此后的作品如《好男好女》(1995)、《南國再見南國》(1996)、《千禧曼波》(2001)、《咖啡時光》(2003)、《最好的時光》(2005)、《紅氣球之旅》(2007)等,在敘事風格和鏡頭表現上有了新的變化,出現現代因素,《海上花》 (2008)又為侯孝賢增添了新的美學風格,對個體關照和時代因素展現主要表現在1983至1993年間的作品中。不可否認的是,侯孝賢形成的電影風格與敘事特點一直延續至今,《刺客聶隱娘》雖然是一部武俠片,但繼承了侯孝賢形成的以藝術精神為目標的敘事風格。
侯孝賢所關心的是個體的人,首先是個體生命的成長與對生死的體驗。《冬冬的假期》改編自朱天文的《安安的假期》,冬冬到鄉下外公家度暑假,電影注意力放在冬冬在外公家與小朋友之間的樂事上,同時,也放在了作為童年的冬冬對大人世界的感知、困惑和理解的經歷上,以孩子的眼光觀察成人世界,所以詹姆斯·烏登認為:“這不是一個無憂無慮的夏天,對小男孩來說,變成了冗長乏味的人生大道理說教。他已從一個簡單的生命,成為有了痛苦意識的生命。”⑤冬冬的個體成長也來自對成人世界的體悟。《童年往事》體現侯孝賢自己對過往童年的記憶以及對生老病死的體驗。侯孝賢稱:“《童年往事》算是我自己的自傳,因為我在念‘國立’藝專的時候,我就已經把以前的事都整理出來了,大概一些童年已經忘掉的。所以有機會就會拿出來拍。”⑥所以作品中融入了本人的生活經歷和生命體驗,特別是對生老病死的關照。《童年往事》拍攝就是在廣東梅縣老家熟悉的環境所拍,更是打上特殊的童年記憶。影片中兒時的玩耍、跟隨祖母迷路時帶回芭樂、追打送回祖母的人力車夫、逛妓院收到紅包、打架等種種經歷不免直接或間與個人體驗有關。電影以父親、母親、祖母三位親人的離世為主要結構片段,阿孝父親患肺病身亡,整個家庭的支柱突然坍塌,而母親對家庭苦苦支撐,最終也患病離世,直到最后祖母離開人世,在這個過程中,主人公經歷了生老病死的體驗,也有從無憂無慮的童年到少年的成長蛻變。
其次,表現個體成長中的青春困惑。《風柜來的人》《戀戀風塵》等電影展現臺灣一代人的成長經歷,以及在青春十字路口的困惑與選擇和愛情苦澀的體會。《風柜來的人》中,澎湖列島中一個名為風柜的地方,一幫年輕人,賭錢打架,無所事事,無聊之極,于是決定去高雄尋找工作。阿清暗戀鄰居小杏,當得知小杏學習日語,阿清不顧朋友的嘲笑也認真地學習日語。雖然二人關系也逐漸密切,但結局并未出人所料,小杏毫無先兆地離開了高雄而去臺北,即使是面對阿清的挽留;而留給阿清的只是無盡的惆悵和苦澀的滋味。所以《風柜來的人》被稱為是“電影創作的真正開始,也是他作品中較為質樸、較少修飾,將青春記憶和寫實風格發揮得最為極致的一部影片”。《戀戀風塵》的主線是謝文遠與阿云青澀無果的戀愛經歷。阿遠從小鎮到臺北闖蕩謀生,女友阿云也到臺北一家裁縫店工作,阿遠收到入伍通知,等返家時,阿云已經嫁給了一位郵差。阿遠痛不欲生,青澀的戀愛就此結束。不管是從阿遠的角度還是從觀眾的角度來說,二人的愛情肯定會有圓滿的結局,但是事實就是這樣,成長過程中,青春的困惑會不時發生,令人無法預料。這些年輕人身上的困惑和迷茫,也反映是反映臺灣一代年輕人的的青春歲月。
再次,展現時代變化中的個體生命。電影并非單單來展現對個體生命的記憶與體驗,重要的是,把這些體驗放在時代變動的背景中來展現。《童年往事》以三代人的命運來突出時代的變化,從阿孝的祖母帶他尋找大陸的情節可知老人對大陸的情結以及反映出的歷史變遷,但由于世代的更替,這種情結在阿孝的心底已經淡化了。《童年往事》也暗示1958年的臺海空戰、陳儀之死等內容,作品“在世代更替、時運交移中,一層層凸顯出阿孝的成長與時代變遷的某種遇合”⑦。隨著上一輩人的謝世,年輕人逐漸成長,并融入臺灣的社會生活中。所以有學者認為侯孝賢創作的重要特點是“將個人式的表達與作品作負載的社會歷史意義高度契合”⑧。
侯孝賢這種對生命記憶的描繪影響到了賈樟柯的電影創作,賈樟柯在與侯孝賢訪談中提到“《風柜來的人》給我很大的啟發……就是個人生命的印記、經驗,把它講出來就有力量”,侯孝賢在訪談中也提到“創作基本上跟你早期接觸的東西有關,你的創作就從那里來”⑨。自《風柜來的人》以后的十年左右時間,侯孝賢關注的大多是生命的個體存在。侯孝賢說:“我的創作焦點是存在的個體,就是生命的本質,存在的個體打動我,所以我拍的都是一些邊緣人,一些小人物。”⑩重要的是,作品通過對普通人物、對小人的刻畫展現個體生命在時代變遷下的生活和記憶,也展現由不同生命個體所呈現出的時代特色。
二、自然法則與記錄色彩
侯孝賢的理想是“能拍出自然法則底下人們的活動”?,也就是采取客觀的態度和冷靜的觀察,拍出人物生活的日常進程,自然狀態下的生存情況,而非進行人為的編排,對人物的關照也不帶有個人的情緒。“商業三部曲”之后的作品就是以“自然法則”來觀察和表現人物的命運。正由于此,電影呈現出強烈的記錄色彩,呈現出強烈的真實性。
侯孝賢的自然法則觀受到沈從文的影響,朱天文給侯孝賢所看的《沈從文自傳》讓侯孝賢對電影有了重新的認識,侯孝賢提到《沈從文自傳》的影響:“看了后頓覺視野開闊,我感覺到作者的觀點,不是批判,不是悲傷,其實是一種更深沉的悲傷……那些人的生生死死,在他的文字里是很正常的事……所以我就想用沈從文那種‘冷眼看生死’,但這其中又包含了最大的寬容與深沉的悲傷,從這個客觀的角度來拍,我覺得我的個性比較傾向于此。”?《風柜來的人》首先受到這種影響,電影中的人物從鄉下到城市,電影采取遠觀的視角,觀察人物的變化。這種表現就是客觀呈現,不對人物進行評判。阿清等人少年好斗,但是在殺雞時卻無能為力,阿清母親沖動地朝他仍菜刀,傷到之后又去賠罪,等等,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缺點,都不是完人。但“侯在他們的缺點面前沒有優越感,也沒有針對這些人物及其所有言行提供任何道德判斷。他們是什么樣,就是什么樣”。?這是按照人物性格自然的形成法則來敘事,把原本的客觀狀態呈現出來。這種“自然法則”還更多地體現在后來的《童年往事》中,特別是對三個人物的去世,侯孝賢不帶自己的主觀情緒去展現,對感情保持一定的距離而呈現出客觀的靜觀視角。如父親的離世并沒有在劇情上進行鋪墊,而是發生在正常的生活進程中,表面上以“冷眼看生死”,沒有過多的情感宣泄,而背后卻透出蒼涼的況味。
對日常生活的記錄,對生存狀態的描繪構成了電影的記錄色彩,這在電影《戲夢人生》中有充分的表現。《戲夢人生》講述日本統治時期布袋戲大師李天祿的生存經歷,記錄李天祿一生所經歷的母親、祖父、祖母、父親、岳父以及小兒子的相繼離世,記錄繼母的殘忍,記錄他在艱難的時期的生存,也記錄他與麗珠的情感經歷,以及演出布袋戲的過程。所有這些都是對李天祿生活記錄的一部分,比如與麗珠的感情經過是電影中濃墨重彩的一部分,麗珠只是一個過客,經歷過便不再出現。甚至對日本人的呈現也是如此。把李天祿的經歷按照生活本身的面目來表現,呈現出最為自然的狀態。由此《戲夢人生》被認為是“一個藝術家的生命編年史,沒有宏大敘事,也沒有主題線索”。所表現的是“最鮮活豐富的記憶被傳統歷史記錄剔除的人們日常生活細節”。?這些日常生活的細節,無非是記錄李天祿的生活和家庭,并非重大事件,也未將李天祿作為一名英雄人物來塑造,通過故事敘述、李天祿自述和布袋戲的表演等內容構成了對日常生活進程的展開,這些元素共同構織李天祿的個人記憶、家庭記憶和時代記憶。
這種對自然法則的使用和記錄色彩《悲情城市》中也有表現,我們可以通過對具體場景的前后對比來分析這種安排。《悲情城市》即使是側面表現臺灣“二二八事件”,仍是通過林家一家人的興衰和四兄弟的狀況來表現,而具體的生活細節是表現這一事件的重要因素。林文雄作為老大,經營名為“小上海”餐館,老二作為醫生在戰爭中失蹤,老三文良從事黑社會活動而被陷害至瘋,老四文清作為聾啞人,卻因為與熱血知識分子的交往而成為“二二八事件”的受害者。電影在表現“二二八事件”的過程中,把主要的鏡頭放在林家的興衰上,而電影中大量篇幅的吃飯場景作為生活中的日常“瑣事”,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因素和社會因素,反映出的社會變遷值得深入探討?。林家祖孫三代兩次吃飯場景,第一次林文雄居中,兩邊分別是父親阿祿和侄子,突出文雄作為長子和一家頂梁柱的地位;電影最后的吃飯場景也是同樣的機位,只是中間的文雄換成了幾乎殘廢的文良,此時文雄已死,這個看似隨意安排的日常生活細節卻恰恰反映林家發生的變化。在表現知識分子兩個吃飯場景中,第一次是國民黨接收臺灣之后,寬榮等知識分子在酒桌上激情慷慨,對臺灣的未來充滿希望,甚至高唱《松花江上》歌曲來表達這種慷慨。而“二二八事件”發生后,知識分子在酒桌上討論時事,表達對當局的失望。這些對日常細節的冷靜記錄,恰是對時事的巧妙表達。
不按照人為的編排對故事進行構思,而是按照生活的本來面目展現日常細節,成為侯孝賢藝術電影的重要特色,“呈現一個世界,在那里最重要的不是專家和政客的東拉西扯,而是生活就是它本身,就是它存在的本來樣子”?,自《風柜來的人》以來的幾部電影在呈現方式上多是按照“自然法則”來記錄生活的本來樣子,記錄人的生存狀態。
三、淡化情節與詩化敘事
朱天文認為侯孝賢“‘基本上是個抒情詩人而不是說故事的人’。他的電影特質,也在此,是抒情的,而非敘事和戲劇”?。這一點點明侯孝賢電影以抒情為主的藝術特質。這與常見的主流商業電影敘事風格不同,甚至與侯孝賢的“商業三部曲”的敘事風格也具有很大的差異,侯孝賢的“新電影”敘事時淡化情節、弱化沖突,使抒情因素大大增加,表現為詩化敘事,這增加了侯孝賢電影敘事美學特征。
在侯孝賢的多部“新電影”中,都努力摒棄起承轉合的敘事模式,而追求內在的張力,這種張力是以人物的內在情感的張力為基礎的。侯孝賢在提到小津安二郎的作品時認這是表象與暗流的關系:“表面上很簡單,讓你感覺沒有很強的戲劇性,但是積累起來,底層便有個暗流,是驚濤駭浪的。”?這也是侯孝賢電影的突出特點。在多部電影中,我們找不到明顯的故事沖突的大段落和明顯的敘事線索,而是在日常的進展中讓人物的情感發生變化。《風柜來的人》對阿清等人的刻畫,多是在一些片段中呈現,打架、賭博、調戲女孩,以及到高雄尋找工作的迷茫和對小杏的暗戀,這些都不是故事沖突的“主軸”,而重點是在這個過程中阿清內在的成長變化。《童年往事》作為侯孝賢的自傳性作品,以回憶的情感流動來安排全片,沒有緊張的故事沖突,而是突出情感化的表現,特別在片頭,祖母一聲聲“阿哈咕”的呼喚和急切的尋找的身影,喚起一種記憶的傷感和對童年的眷戀,雖然沒有對故事沖突的敘事,但奠定了影片苦澀傷感的情感基調。《戀戀風塵》在了表現阿遠與阿云的愛情時,沒有明顯的矛盾沖突和解決過程,阿云與郵遞員結婚,對阿遠來說是突如其來的打擊,在表現這一內容時,一方面阿遠抱頭痛哭,另一方面就轉到阿公和阿遠在田地里談論天氣、談論番薯收成的畫面,表現了阿遠的逐漸成熟。其他的內容如阿公勸孩子吃飯、孩子偷吃味精、阿遠父親為其分期買的防水手表,等等,在整部片子中都較少呈現情節性和故事性,多是用畫面來表現生活的艱難。
這種對情節的有意弱化在《戲夢人生》中表現得尤為突出,這部電影在結構上把時間進行重組、把故事的進展和李天祿本人的講述融為一體,有如共時性的動態畫卷,把李天祿的生活的重要片段依次展開,鋪面而來的是一種由記錄和回顧帶來的詩意氣息,而并非若干個戲劇性強的情節。即使是在敘事性較強的《悲情城市》中,由于長鏡頭的使用帶來節奏的放慢,也使本來情節性較強的沖突得到弱化,而底層的“暗流”即情感的流動得以詩意地表現。侯孝賢的這種以弱化情節和強化情感的特色,在臺灣新電影運動中是較為突出的,被稱為“這種以‘情’為主的審美對象,在侯孝賢的電影中得到了一種現代意義的復活”?。
這種淡化沖突的詩化敘事方式一直影響到其后的創作,《刺客聶隱娘》是侯孝賢唯一一部“武俠片”,聶隱娘作為刺客,在師命與大義之間,選擇放棄刺殺表兄田季安。但與傳統的動作片不同,不強調外在的武打動作,而是以聶隱娘的內在的情感變化為中心,強調“俠義”精神。由于節奏放慢,為觀眾提供了參與的空間,去體會導演的美學風格。
與情節的淡化相對應,侯孝賢在多部影片中通過對風景的描繪、文字字幕的嵌入等來突出電影的詩化敘事。由于侯孝賢在《冬冬的假期》《風柜來的人》《童年往事》《戀戀風塵》等電影中要表現的是個體的成長,所以在具體手法上是以詩意的流動和情感的含蓄來架構故事,而不是直接表現故事,把較多的影像放在對田園風光和山水景物的表現上。《冬冬的假期》中,清澈的小河中、濃密高大的樹冠、一片片的水田、遠處的山巒、裊裊的炊煙構成了美麗的農村風光,也為冬冬的假期生活提供了一種快樂的背景,這也是突出鄉土情懷的一種抒情方式。
文字字幕有效的嵌入是《悲情城市》的突出特色,字幕成為鏡頭的有機組成部分。文清是聾啞人,他與別人的交流都采用筆談,這些交談都會以字幕的形式完整地展現。文清與寬美互生好感,向寬美介紹自己聾啞的原因時,黑底白字的字幕赫然顯示這樣的字跡:“八歲從樹上摔下/跌傷頭疼/大病一場/病愈不能走路/一段時間/自己不知已聾/是父親寫字告我/當年小孩子/也不知此事可悲/一樣好玩。”分行豎排的視覺造型,與現代詩一樣美觀。這樣的文字具有敘事功能,即介紹了文清耳聾的原因。但這種敘事功能是通過抒情性極強的詩歌文本來表現,使敘事得以詩意的展現。再如寬美的哥哥寬榮在“二二八事件”之后隱至山中,文清向寬美介紹時這個情節時,字幕如下:“寬榮已結婚/在山里/恕不能說出地方。他交代/不要告訴家人/當我已死/我人已屬于祖國/美麗的將來。”這里在情節上介紹了寬榮的去向,但以字幕形式的展示,又讓觀眾在“閱讀”中體會到寬榮的狀體和心境。侯孝賢將字幕當做有機的鏡頭進行展示,字幕成為與鏡頭平分秋色的畫面,詩歌的文本樣式與故事情節的完美融合,使得敘事本身帶有強烈是詩化抒情意味。這種意味正是侯孝賢通過對情節淡化來表現出的藝術氣質。
總體來講,淡化情節和詩化敘事方面,構成了侯孝賢“新電影”敘事的主要特色。“他的電影敘事比較疏于情節而側重詩意的提升,含有一種堅守人文精神的自覺性,在總體上形成一種獨家風骨:自我內省、切進現實……在大時代的動蕩中描繪出臺灣風俗民情的現代風貌”?。
表面上看,電影的商業化與藝術性好像非此即彼,藝術性強的作品由于“曲高和寡”不容易受到大眾的歡迎,而完全以商業化運作的作品也不會保持長久的生命力?。所以有學者感慨:“電影人最關心的,到底是個人在電影藝術上的成就和名譽,還是本國電影業的興衰、本土電影市場的繁榮和本民族電影文化的發展,這常常是一個兩難的選擇,也是最能考驗電影人對本土電影/民族電影是否具有強烈責任心和歷史使命感的一個重大選擇。”?但此處所論也是涉及到有關電影藝術和電影市場的問題,當然,一位導演能通過對電影藝術的追求來獲得可觀的電影市場,且做出體現出強烈責任心和使命感的作品,這將是莫大的鼓舞,而侯孝賢則堅持通過對藝術電影的追求來展現個人的生命思索和藝術責任感。
作為藝術電影,“文化的追求是電影創作的第一位需要,而無論3D還是黑白默片,關鍵是有沒有對于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努力……中國電影的精致不全是在技術的精致,而是在情感的精致、生活逼真性的精致上,舍此的大片和鴻篇巨制都難擺脫虛幻的命運”。?可以說,侯孝賢在早期的“商業三部曲”之后向藝術電影的轉向就確定了“新電影”為藝術電影而創作的方向,而非大眾電影,也并非為大眾電影市場而創作。按照朱天文的說法,是以“尋找精英觀眾為訴求”,“假如有一天他的片子不小心大賣了,對不起,那絕對是個意外”,是因為對藝術的追求,“電影壽命是可以因著對品質的要求而獲得延長”。?而侯孝賢的“新電影”創作在對個體生命的觀照和對時代因素的展現上、對日常生活的記錄特色上、在對淡化情節和詩化抒情的敘事風格上,都體現出對人的精神世界的探求,并且在對生命的記錄、對文化的追求和對使命感的展示上,都具有其獨特的藝術精神和文化品格,而這種精神與商業化電影不同,不是以票房來衡量的。
注釋:
①③⑤???[美]詹姆斯·烏登著,黃文杰譯:《無人是孤島:侯孝賢的電影世界》,復旦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頁、第248頁、第121頁、第118頁、第217頁、第219頁、第234頁。
②?孫慰川:《論侯孝賢的得與失——兼談電影的藝術性與觀賞性之關系》,《北京電影學院學報》2004年第4期。
④黃鐘軍:《侯孝賢“前新電影”時期作品中的城鄉二元議題研究》,《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3年第3期。
⑥饒曙光:《侯孝賢訪談》,《電影要從非電影中來:侯孝賢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237頁。
⑦?黃式憲:《侯孝賢作品的人文親和力及其文化品格——兼議臺灣“新電影”的崛起及其人文脈理》,《上海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3年第3期。
⑧李相:《電影作者侯孝賢——個人書寫與歷史記憶》,饒曙光主編:《電影要從非電影處來:侯孝賢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119頁。
⑨賈樟柯:《賈想1996—2008:賈樟柯電影手記》,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176頁。
⑩?卓伯棠主編:《侯孝賢電影講座》,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第94頁。
??朱天文:《〈悲情城市〉十三問》,饒曙光主編:《電影要從非電影處來:侯孝賢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235頁、第220頁、第221頁。
?張靚蓓:《〈悲情城市〉以前:與侯孝賢一席談》,《北京電影學院學報》1990年第2期。
?王冬梅:《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再出發》,《學術論壇》2011年第7期。
?朱天文:《最好的時光:侯孝賢電影記錄》,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版,第335頁。
?裴亞莉:《藝術抒情本體的電影化顯現——關于侯孝賢電影的幾個問題》,饒曙光主編:《電影要從非電影處來:侯孝賢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109頁。
?盧衍鵬:《傳媒改制、出版主導與文學導購》,《東岳論叢》2015年第6期。
?周星:《電影在地性與透視生活的真切感——關于侯孝賢電影的意義認知》,饒曙光主編:《電影要從非電影處來:侯孝賢電影研究》,中國電影出版社2013年版,第147頁。
*本文系山西師范大學科研啟動資金(項目編號:833342)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單位:山西師范大學戲劇與影視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