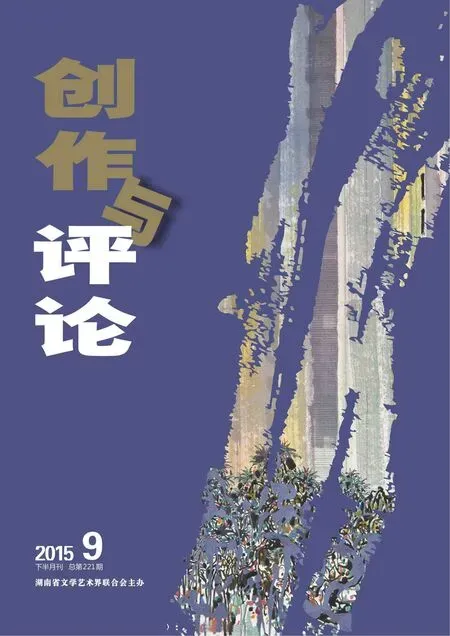現(xiàn)代人丟失了自己的精神之根?
○ 魯樞元
現(xiàn)代人丟失了自己的精神之根?
○ 魯樞元
國學(xué)大師牟宗三對(duì)于現(xiàn)代人的生命狀況可謂痛心疾首:“人類的生命發(fā)展到今日,實(shí)在是肢解了、僵化了,到了極端膠固枯燥的境地”“現(xiàn)代人沒有文化只有狡猾,沒有理性只有理智,陰險(xiǎn)狠愎的變態(tài)心理淹沒了一切”“時(shí)下中國人不成格局,心胸器量窄小,對(duì)人處處防范,學(xué)者也只看眼前、只重實(shí)利、冒充內(nèi)行、妄自尊大……”這可能會(huì)引起不少人的質(zhì)疑:你看活在當(dāng)下的人不是整天吃香喝辣、猛玩高樂,一個(gè)個(gè)白白胖胖,想減肥都減不下來,這樣的“生命狀況”難道還不好嗎?這或許就是現(xiàn)代社會(huì)被著力倡導(dǎo)的生活理想,但在傳統(tǒng)的中國文化人看來,這樣的生命活在世上無異行尸走肉!
那么什么是“生命”?什么是生命的“真義”?
牟宗三認(rèn)定中國的傳統(tǒng)哲學(xué)就是“生命哲學(xué)”,這里的生命固然也包涵了人的生物性生命,諸如人的“身體”;同時(shí)更包涵了人的文化生命,又叫“慧命”“天性”。這種“文化性的生命”,具有情感的、倫理的、道義的、智慧的價(jià)值與功能,與“身體”一樣,也是生來與俱、先天既有的。和顯示于外的生理性的生命相比,這是一種內(nèi)在的精神性的生命、精神的實(shí)體,一種“內(nèi)在自然”。這種文化性的、精神性的“慧命”或“天性”,是原本就存在于人的生物體內(nèi)的,被視為一個(gè)人的“根器”與“心源”,屬于一個(gè)人立身處世的“根源”。這有點(diǎn)像黑格爾的“絕對(duì)精神”,一部人類社會(huì)史就是人類的這一精神生命的演進(jìn)與呈現(xiàn)。
我想,這種“唯心主義”的學(xué)說很難為深受唯物主義哲學(xué)教育的人們所理解,但也許可以借助榮格的精神分析心理學(xué)得到某種程度的解釋。
榮格對(duì)于人類認(rèn)識(shí)史的進(jìn)程有著一種堅(jiān)定不移的看法。他認(rèn)為,歐洲自進(jìn)入現(xiàn)代工業(yè)社會(huì)以來,隨著人們向外部空間的拓展,隨著人們對(duì)于客觀世界的知識(shí)的激增,人對(duì)于自己心靈的觀照停滯了。人們?yōu)樽约撼晒Φ亟⒘艘粋€(gè)易于被意識(shí)和技術(shù)控制的世界,卻剝奪去人的全部心理潛能。人們?cè)谥橇Ψ矫媸斋@過剩,而在心靈方面則淪喪殆盡。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的爆發(fā),證實(shí)了榮格的預(yù)感。于是,榮格給自己樹立了一個(gè)終生為之奮斗的目標(biāo):尋回現(xiàn)代人類失落遺忘已久的心靈。
榮格相信,人類生活中存在一種“實(shí)體性”的“獨(dú)立性”的心靈,它就像是中國小說《紅樓夢(mèng)》中賈寶玉脖子上掛的那塊石頭一樣,是一個(gè)存在的實(shí)體。這種精神性的實(shí)體,就是他所說的一個(gè)種族的“集體無意識(shí)”。在榮格看來,“集體無意識(shí)”對(duì)于人類個(gè)體來說,是一種獨(dú)立的存在。它先于個(gè)體而存在,作為一種預(yù)定的“構(gòu)圖”與個(gè)體一道降生于人世。這種說法已經(jīng)十分接近中國儒家經(jīng)典中講的“天性”,亦即當(dāng)代新儒家講的“理性生命”“道德生命”“文化生命”“精神生命”。
這種“天性”,或曰“集體無意識(shí)”,應(yīng)該是有“種族性”的。種族不同,其內(nèi)涵也會(huì)存有差異。就我們中華民族而言,作為人之所以為人的“根器”與“心源”,是以“仁”為核心的“惻隱之心”、以“義”為核心的“羞惡之心”、以“禮”為核心的“辭讓之心”、以“智”為核心的“是非之心”。這些“文化的生命”“精神的生命”就相當(dāng)于人的內(nèi)在的自然,是原本存在于人的心靈之中的。按照牟宗三的說法:人之所以為人的“道德性主體”(Moral subjectivity)就是在這些“心性”的根基上豎立起來的。這樣的人,頂天立地,內(nèi)而透精神價(jià)值之源,外而通世事萬象之流,在此根基之上的生命活動(dòng)才是生命的理想境界!
現(xiàn)代人的生命活動(dòng)中為什么彌漫著如此濃烈的貪腐奢靡、暴戾無情、鮮廉寡恥、喪心病狂的氣息,或許就是因?yàn)橐呀?jīng)在不知不覺中捐棄了自己種族原本的“根器”與“心源”。這些精神性的實(shí)體,就是系在賈寶玉脖子上的“通靈寶玉”,丟棄了它,人是注定要發(fā)瘋發(fā)狂的。
(作者單位:蘇州大學(xué)文學(xu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