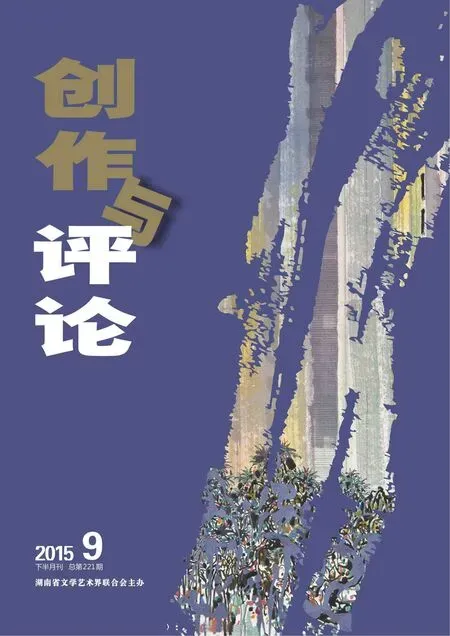“在場者”與“后來者”的對話
——重讀《創(chuàng)業(yè)史》與《生死疲勞》中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書寫
○ 劉欣玥
“在場者”與“后來者”的對話
——重讀《創(chuàng)業(yè)史》與《生死疲勞》中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書寫
○ 劉欣玥
“想象中國的方法”是王德威先生的提法,但是對于當(dāng)代作家來說,要講述中國的故事,僅僅有敘事層面的“想象”是不夠的。對于歷史的理解以及對于現(xiàn)實(shí)的考察,都是用文學(xué)表現(xiàn)中國所不必可少的儲備,對于表現(xiàn)宏闊歷史篇幅的長篇小說尤其如此。如何表達(dá)中國這一現(xiàn)代民族國家不斷更新的經(jīng)驗(yàn),與此同時(shí)公正地處理歷史,不僅僅關(guān)乎作家個人的眼光與能力,同時(shí)也意味著一個民族自我認(rèn)識和自我表述的智慧與自覺。近年來文壇涌現(xiàn)了不少反思共和國歷史的長篇小說,大多對共產(chǎn)黨領(lǐng)導(dǎo)的革命持諷刺、否定的姿態(tài),漸漸形成一種常規(guī)性的意識形態(tài),很難說沒有概念化和新的固化之嫌。這與1980年代以來“告別革命”的主流思潮有關(guān),在當(dāng)代文學(xué)的譜系里,建構(gòu)起與認(rèn)同革命、熱情歌頌社會主義的十七年文學(xué)截然不同的敘述范式,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和柳青的《創(chuàng)業(yè)史》正是分別處于兩個文學(xué)陣營之中的作品,農(nóng)村題材是他們共同關(guān)注的話題。
今天看來,《創(chuàng)業(yè)史》仍然是十七年農(nóng)村題材小說的典型之作,《生死疲勞》則大體未出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興起的新歷史小說的脈絡(luò),兩部作品乍看之下各自涇渭分明,似乎沒有什么新鮮的可比性,但若簡單地以“左”/“右”論之,或以一句標(biāo)簽化的“政治圖解”“宏大敘事”或“告別革命”“反歷史”打發(fā),難免掛一漏萬。在對比的視野里重讀《創(chuàng)業(yè)史》與《生死疲勞》,是因?yàn)閮刹孔髌飞婕傲艘粋€共同的對象: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①,這個對象可以放入共和國六十年的歷史中,進(jìn)行總體性的思考。“過去”與“當(dāng)下”兩個觀察視點(diǎn)互通有無,或許可以找到不乏價(jià)值的真正“對話”,有助于我們重新思考中國的農(nóng)村土地所有制以及討論中國農(nóng)村的命運(yùn)。
兩部作品的前后創(chuàng)作間隔了近50年,比較二者歷時(shí)性的差異,需放在一個共時(shí)性的框架中才能確立比較的合理性。因此本文擬以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作為入口,以“主人公形象”“敘事矩陣”“父子關(guān)系”“公有制與私有制之爭”等作為探討對象,最后將思考回歸到如何理解“歷史”本身上來。理解與觀照歷史,并且保持對現(xiàn)實(shí)的切實(shí)關(guān)懷,是“講述中國故事”不可缺失的文學(xué)品質(zhì),無論是十七年文學(xué),還是新歷史小說,都只是一種講述故事的范式,而唯有“跳出”某一意識形態(tài)控制和概念化的束縛,才能夠給予更加公正的對待歷史、書寫歷史。
一、從“英雄”到“反英雄”
《創(chuàng)業(yè)史》的故事發(fā)生在1953年到1954年,《生死疲勞》則跨越了半個世紀(jì)的當(dāng)代中國史,兩個小說文本書寫的歷史篇幅不同,在1950年代初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這一段是重合的,因此本文將以此為討論歷史的聚焦點(diǎn)。“‘歷史’與‘英雄’一直是兩個被捆綁在一起的概念”②,在這樣兩部書寫宏闊歷史的長篇小說中,尋找“英雄”是一種不自覺的閱讀期待,在合作化運(yùn)動中浮出歷史地表的兩位“英雄”的形象落差值得關(guān)注,作為敘事元素的小說主人公也確實(shí)可以提供比較空間。
蛤蟆灘年輕的黨員,互助組帶頭人梁生寶,是典型的十七年文學(xué)的正面人物。小說通過梁生寶建立互助小組、幫助貧農(nóng)解決活躍借貸困難、買稻種、辦新式育秧、率領(lǐng)小組成員進(jìn)終南山、辦燈塔社等一系列事件,塑造了一個目光遠(yuǎn)大,謙虛能干,吃苦耐勞的嶄新的中國農(nóng)民形象。最關(guān)鍵的是,梁生寶是共產(chǎn)黨員,堅(jiān)定地跟黨走,有著明確的階級斗爭意識和社會主義的政治理想,政治上的先進(jìn)性注定了梁生寶要成為蛤蟆灘合作化運(yùn)動的“英雄”。《創(chuàng)業(yè)史》一面世即廣受好評,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塑造了梁生寶這個“社會主義新人”形象,“(梁生寶)是十年來我們文學(xué)創(chuàng)作在正面人物塑造方面的重要收獲”③。雖然在六十年代文壇關(guān)于梁生寶和梁三老漢形象優(yōu)劣有過長時(shí)間的爭論,也曾有批評家指出梁生寶的塑造太過于圖解政治,缺少藝術(shù)上的飽滿性與真實(shí)性④。但是無論怎么說,梁生寶作為小說中的英雄人物、理想人物是確鑿無疑的,“他(柳青)筆下的梁生寶,不管帶不帶所謂的‘理念化’,都不可否認(rèn)是社會主義革命文學(xué)中最早出現(xiàn)的社會主義英雄人物的成功形象”⑤。梁生寶與劉雨生(《山鄉(xiāng)巨變》)、朱老忠(《紅旗譜》)、盧嘉川、江華(《青春之歌》)等處于同一個英雄人物序列中,他們都以前所未有的堅(jiān)定意志、神圣品格、樂觀精神,積極參與社會主義革命實(shí)踐,這也是十七年文學(xué)積極配合政治意識形態(tài)號召,多少有些“概念化”的產(chǎn)物。
梁生寶的“英雄”形象是在與反動階級的斗爭中樹立的。有學(xué)者提出可以按照格雷馬斯的敘事矩陣來剖析《創(chuàng)業(yè)史》的人物關(guān)系,而這一文本內(nèi)部結(jié)構(gòu)幾乎完全參照了毛澤東1955年所做的報(bào)告《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合作化問題》中對于貧下中農(nóng)、中農(nóng)和富農(nóng)入社的戰(zhàn)略性部署:
梁生寶,高增福,歡喜——公有化/正面人物
王佐民,楊副書記——幫手/正面人物
蛤蟆灘三大能人——反公有化/反面人物
梁三老漢——非公有化/中間人物⑥
梁生寶互助小組最終證明了合作化的優(yōu)越性,成功地建立起燈塔社,將代表了廣大貧農(nóng)猶豫不決心理的梁三老漢拉入走公有化道路的陣營中。社會主義公有化借助“英雄”之力證明了自身的優(yōu)越性與必然性,也在《創(chuàng)業(yè)史》歷史本質(zhì)主義的闡釋中獲得了權(quán)威。
《生死疲勞》中的藍(lán)臉,作為全中國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單干戶,如果出現(xiàn)在《創(chuàng)業(yè)史》中肯定是反動階級陣營里的一個“敵人”。如果同樣以格雷馬斯敘事矩陣分析《生死疲勞》中的人物關(guān)系,大概如下:
藍(lán)臉——反公有化/正面人物
陳縣長(后被打倒)——幫手/正面人物
洪泰岳,西門金龍——公有化/反面人物
藍(lán)解放——非公有化/中間人物
藍(lán)臉可謂蛤蟆灘三大能人的投胎轉(zhuǎn)世,但是在莫言的筆下,曾經(jīng)的“敵人”卻變成了“英雄”。一個通常認(rèn)識中的反面人物變成了正面人物,且被賦予了英雄的品質(zhì)、行為與地位,因此不同于傳統(tǒng)的英雄,筆者在這個意義上將藍(lán)臉命名為“反英雄”。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此處的“反英雄”和西方文論上的“反英雄”(antihero)以及新時(shí)期以來文學(xué)中出現(xiàn)的“非英雄化”現(xiàn)象都不同。⑦藍(lán)臉曾是地主西門鬧家的長工,貧農(nóng)的身份卻并沒有給他帶來絲毫毛澤東期待的“社會主義積極性”,相反,他堅(jiān)持單干到底,以“入社自由”原則為護(hù)身符,堅(jiān)決與合作化道路斗爭。與此同時(shí),作為共產(chǎn)黨員的村長洪泰岳和革命小將西門金龍?jiān)谕菩泻献骰瘯r(shí),卻被描繪成了蠻橫暴虐,強(qiáng)拉人入社的“左”傾問題嚴(yán)重的反面形象。“反英雄”藍(lán)臉的英雄氣概,在幾次拒絕入社直至妻離子散,寧死不屈,一人獨(dú)守著最后的土地這環(huán)環(huán)相扣的情節(jié)中展露無余,戲劇性的情節(jié)層面也有意突顯藍(lán)臉和他的土地的意義——合作化運(yùn)動最終失敗落幕,改革開放的浪潮中官商勾結(jié),將西門屯的土地開發(fā)成商業(yè)用地,許多人成了失地農(nóng)民,只有藍(lán)臉的一畝六分地屹立不倒,堅(jiān)守著幾千年農(nóng)村土地的本色:種糧食、埋尸骨。而所有曾經(jīng)迷失在歷史浪潮中的人,西門鬧和藍(lán)臉的子孫后代,都在故事的最后明白了藍(lán)臉和他的土地的珍貴價(jià)值。莫言有意與十七年文學(xué)“正史”式的話語系統(tǒng)唱反調(diào),用荒誕、戲謔的敘事聲音將《創(chuàng)業(yè)史》中旗幟高揚(yáng)的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處理為一出鬧劇,將最后一個堅(jiān)守土地私有制的農(nóng)民藍(lán)臉?biāo)茉斐伞胺从⑿邸薄摹坝⑿邸钡健胺从⑿邸保苑雌涞蓝兄摹暗讱狻眮碜杂谄洹昂髞碚摺钡臅r(shí)間差,“反英雄”的話語權(quán)是借助了更長的歷史視野而獲得的。但除此以外,選擇梁生寶或選擇藍(lán)臉作為“英雄”,也與兩人對土地所有制以及中國農(nóng)村命運(yùn)的不同認(rèn)識有關(guān)。
費(fèi)孝通在《鄉(xiāng)土中國》中曾參照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中提出的“阿波羅式”和“浮士德式”的文化模式區(qū)分鄉(xiāng)土社會和現(xiàn)代社會的精神。阿波羅式的精神是古典的,認(rèn)定宇宙的安排遵從一個完整的秩序,這個秩序超于人的創(chuàng)造,人只能接受和維持它;浮士德式的精神則屬于現(xiàn)代社會,將沖突看作存在的基礎(chǔ),生命的意義來自于不斷的對阻礙的克服,所謂前途,就是不斷的創(chuàng)造與變。⑧借鑒這兩種精神,來觀照柳青與莫言對農(nóng)村命運(yùn)的理解也未嘗不可。如果說“變”與“斗”是浮士德式的核心精神,那么“靜”與“守”則是阿波羅式的價(jià)值皈依,梁生寶與藍(lán)臉,顯然一個是浮士德式的英雄,一個是阿波羅式的英雄,兩個“英雄”是有各自的語境和對歷史的認(rèn)識的。
柳青所認(rèn)識的1950年代的中國農(nóng)村,是一個舊有的生產(chǎn)關(guān)系不能適應(yīng)新的社會需求的場域,舊有的土地私有制和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格局不能提高農(nóng)村的生產(chǎn)效率,更不能滿足國家工業(yè)化原始資本累積的巨大需求,因此必須走新的合作化道路,提高生產(chǎn)力。但是正如費(fèi)孝通所指出的,舊的方法格局有它的惰性,新方法不是現(xiàn)成的,需要有人發(fā)明和試驗(yàn),才能被接受,完成社會變遷的過程,“在新舊交替之時(shí),不免有一個惶惑,無所適從的時(shí)期,在這個時(shí)期,農(nóng)民心理上充滿著緊張、猶豫和不安”,此時(shí)“文化英雄”應(yīng)運(yùn)而生,“他提得出辦法有能力組織新的試驗(yàn),能獲得別人的信任”。⑨1953年的中國,第一個五年計(jì)劃剛剛啟動,黨中央的有明確的計(jì)劃,社會主義工業(yè)化不能離開農(nóng)業(yè)合作化的支持:“我們現(xiàn)在不但正在進(jìn)行關(guān)于社會制度方面的私有制到公有制的革命,而且正在進(jìn)行技術(shù)方面的由手工業(yè)生產(chǎn)到大規(guī)模現(xiàn)代化及其生產(chǎn)的革命。”⑩在這樣風(fēng)云激蕩的社會轉(zhuǎn)型關(guān)頭,新舊交替的農(nóng)村需要“浮士德式”的變革精神,梁生寶正是挑起了“文化英雄”的大梁,領(lǐng)導(dǎo)的蛤蟆灘合作化道路,雖然此處難以回避柳青對主流政治話語的附庸之嫌,其過分樂觀的理想化立場也掩蓋了許多現(xiàn)實(shí)中的矛盾。
反觀《生死疲勞》,西門屯五十年的歷史也是“變”與“斗”的歷史,土地革命、互助合作、大躍進(jìn)、文革、改革開放、家庭聯(lián)產(chǎn)承包責(zé)任制,具體而微著共和國農(nóng)村變遷的西門屯一樣也沒有錯過。但是藍(lán)臉和他一畝六分地自留地,實(shí)則與被諷刺手法過濾過的僵硬意識形態(tài)話語形成復(fù)調(diào),張揚(yáng)的是幾千年中國鄉(xiāng)土社會的主體意識,“從基層上看去,中國社會是鄉(xiāng)土性的”?,鄉(xiāng)土中國最大多數(shù)的人都是靠種地謀生的鄉(xiāng)下人,因此深知土地的可貴,將“土地”奉為數(shù)量上占最高地位的神明。正因?yàn)楦街谕恋厣希鲃有缘停r(nóng)民聚村而居,進(jìn)行封閉隔膜的小農(nóng)經(jīng)營,由血緣關(guān)系和傳統(tǒng)的社會習(xí)俗禮節(jié)維持鄉(xiāng)土文明,因此中國的鄉(xiāng)土社會格局大體屬于“阿波羅式”的模式。藍(lán)臉基本延續(xù)了農(nóng)民在鄉(xiāng)土社會中的生存方式,始終以土地為生命,在合作化的瘋狂浪潮中,他與殘廢了的西門驢在自留地上耕種的情景悲壯不已,與西門牛在月光下孤獨(dú)勞動的畫面被莫言描寫得神圣而莊嚴(yán),而隨著改革開放,建文化旅游村和現(xiàn)代享樂場所讓農(nóng)民失去了耕地,金錢與欲望在西門屯大行其道,也逐步賦予了藍(lán)臉的土地類似“最后一塊凈土”的崇高性,傳統(tǒng)意義上的“故土/故鄉(xiāng)”的價(jià)值亦被莫言無限放大。值得一提的是,小說采用的六道輪回的佛家想象、章回體的古典筆法,雖然流于表面化,但作為莫言的一種敘事策略,都暗合了莫言在重述土地故事時(shí)回歸傳統(tǒng)的立場。他基本完全否定了毛澤東時(shí)代的農(nóng)村社會主義革命,也無法認(rèn)同鄧小平時(shí)代的金錢資本邏輯,雖然他對中國農(nóng)村的問題缺乏深刻的、有誠意的思考,但其寫作的癥候性是值得關(guān)注的。莫言傾盡筆墨渲染最后一塊私有土地的榮耀,強(qiáng)調(diào)藍(lán)臉是“全中國唯一堅(jiān)持到底的單干戶”,這位反現(xiàn)代歷史—回歸傳統(tǒng)的“靜”與“守”的“英雄”,提供了“正史”敘述之外另一種講述農(nóng)村故事的方法。
二、指認(rèn)父親:公有制與私有制之間的“裂隙”
《創(chuàng)業(yè)史》與《生死疲勞》對于合作化運(yùn)動的認(rèn)識有著截然相反的立場,這與作者各自所處的歷史語境密切相關(guān),合作化運(yùn)動從根本上是將土地個人所有制轉(zhuǎn)換成集體所有制的社會主義革命,兩部小說的分歧由此而來,公/私土地所有制因此值得進(jìn)一步討論。梁生寶和藍(lán)臉這一正一反兩位“英雄”,其實(shí)還處在另一重相同的身份結(jié)構(gòu)中,就是父子關(guān)系。比較梁三老漢與梁生寶,西門鬧與藍(lán)臉的父子關(guān)系,可以發(fā)現(xiàn)許多有趣的異同,其中隱藏著各自對土地所有制的認(rèn)同。因此本節(jié)擬從兩對父子關(guān)系入手,嘗試結(jié)合當(dāng)代史探討他們對農(nóng)村土地所有制問題的思考。
首先,梁三老漢與梁生寶,西門鬧與藍(lán)臉都不是親生父子。貧苦的莊稼漢梁三中年喪妻,在饑荒年間“撿”來了渭北高原逃難出來的寶娃母子,寶娃從此隨繼父姓梁,長成了日后的梁生寶。藍(lán)臉也是被撿回來的,地主西門鬧救了快要凍死的藍(lán)臉一命,收留他并認(rèn)了干兒子,不同的是藍(lán)臉并沒有隨西門鬧姓,而是成了西門鬧家的長工。兩對父子都是繼父子/養(yǎng)父子,這種非親生的關(guān)系就割斷了農(nóng)村社會一以貫之的“血緣”紐帶。梁三老漢一直懷抱著創(chuàng)家立業(yè)的理想,土改后分得了田地,本以為終于可以父子聯(lián)手創(chuàng)立一番事業(yè),但梁生寶讓他的期望落空。梁生寶以一個地緣上的“外來者”身份,成為了蛤蟆灘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的帶頭人,他選擇的社會主義公有化道路,與繼父梁三老漢個人發(fā)家的“創(chuàng)業(yè)”理想有著不可調(diào)和的矛盾,這一父子矛盾貫穿《創(chuàng)業(yè)史》第一部的始終,成為一條重要的敘事線索。事實(shí)上,作為一個兒子,梁生寶一直對父親非常尊重孝順,但在私有/公有的原則性的問題上堅(jiān)決地忤逆了父親的意志;而藍(lán)臉作為西門鬧撿來的義子,不僅沒有血緣關(guān)系,也沒有繼承西門鬧的姓氏(相比于梁家父子“有名無實(shí)”,藍(lán)臉連“名”都沒有),只是做了西門鬧家的長工。西門鬧在解放前的土地革命中被槍殺。但就是這樣一個在血緣、名分、身份上都與西門鬧親疏有別的“義子”,卻始終保持了對“老掌柜的”的敬重,念念不忘,這一點(diǎn),從藍(lán)臉與西門鬧轉(zhuǎn)世的驢、馬、狗的靈犀相通即可見。藍(lán)臉繼承了西門鬧“不勞動者不得食”的信條,至死捍衛(wèi)自己的土地,靠自己的雙手吃飯。在所謂的“兩條道路”的選擇中,藍(lán)臉和西門鬧同在反社會主義的陣營里,他在私有土地上單干到底的選擇,可以說是大體上對“父親”意志的繼承。
其次,不難看出,在小說中,梁生寶和藍(lán)臉都是具有鮮明堅(jiān)定的意志和極強(qiáng)行動力的人,再大的困難和挑戰(zhàn)都沒有動搖他們各自走公有化/私有化道路的決心。這樣的意志力并非憑空產(chǎn)生,需要強(qiáng)大的信仰支撐,這就涉及到這兩對父子關(guān)系中相似的第二點(diǎn)。同為非親生的兒子,繼父/養(yǎng)父的影響并不能滿足梁生寶和藍(lán)臉的信仰需求,這樣他們就自覺或不自覺地產(chǎn)生了“精神尋父”的行為。想要對兩人純粹而堅(jiān)定的意志力作出更合理的解釋,就要找到他們內(nèi)心認(rèn)同、皈依的對象。在這樣一個層面上可以說,在繼父/養(yǎng)父之外,他們其實(shí)都找到了各自內(nèi)心認(rèn)定的“生父”。
梁生寶找到的“生父”是共產(chǎn)黨。柳青在《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中明確解釋了自己的創(chuàng)作意旨:“《創(chuàng)業(yè)史》這部小說要向作者回答的是:中國農(nóng)村為什么會發(fā)生社會主義革命和這次革命是怎樣進(jìn)行的”“簡單的一句話來說,我要把梁生寶描寫為黨的忠實(shí)兒子。我以為這是當(dāng)代英雄最基本、最有普遍性的性格特征。在這部小說里,是因?yàn)橛辛它h的正確領(lǐng)導(dǎo),不是因?yàn)橛袀€梁生寶,村里掀起了社會主義革命浪潮。……小說的字里行間徘徊著一個巨大的形象——黨”?。其實(shí)在小說的最開始,年輕的梁生寶也曾與梁三老漢一樣想要走個人創(chuàng)業(yè)之路,但是隨著共產(chǎn)黨力量滲入農(nóng)村,梁生寶經(jīng)歷了意識形態(tài)的覺醒,開始一步步向社會主義理想靠攏,這個時(shí)候就是他指認(rèn)“生父”的關(guān)鍵時(shí)刻。隨著梁生寶無條件地接受、信賴共產(chǎn)黨輸入的意識形態(tài),堅(jiān)定不移地響應(yīng)黨的合作化號召,他也就逐步在實(shí)踐中完成了疏離養(yǎng)父—指認(rèn)“生父”—借助對“生父”的認(rèn)同建立自身主體性的“成人儀式”。“忠實(shí)兒子”的形象,從他掛在嘴邊的那句口頭禪“有黨領(lǐng)導(dǎo),我慌啥了?”中得到最直觀的體現(xiàn)。正如有學(xué)者指出的,“梁三老漢與愈來愈自行其事的梁生寶的沖突,是已去勢的母親權(quán)威對新興父親權(quán)威的最無力抵抗,在大多數(shù)沖突場合,與梁生寶的堅(jiān)定、富于朝氣相反,梁三老漢總顯得怯懦(如第十七章里只能去獨(dú)自哭墳)。最后,梁三老漢心悅誠服地支持兒子,表明作為父親形象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已正式贏得合法權(quán)威地位”?。
梁生寶的“成人儀式”是由指認(rèn)“生父”而完成的,與養(yǎng)父梁三老漢血緣關(guān)系的缺失,正好提供了作為“外來者”的梁生寶一個向共產(chǎn)黨“效忠”的結(jié)構(gòu)性的空位之便。作者想要通過梁生寶的成長說明,作為解放后翻身做主的貧農(nóng),舊有的私人發(fā)家創(chuàng)業(yè)已經(jīng)不符合歷史潮流,而“聽共產(chǎn)黨的話,跟共產(chǎn)黨走”,做“黨的忠誠兒子”,就能贏得廣大群眾的信任,戰(zhàn)勝階級敵人,成長為推動歷史前進(jìn)的英雄人物。必須進(jìn)一步指出的是,梁生寶對黨的認(rèn)同和對梁三老漢的疏離,就是向公有化的合法權(quán)威的認(rèn)同與向私有化的不合法權(quán)威的疏離。土地公有制的合法性就這樣被建構(gòu)起來了。
作為一部持有非常徹底的反歷史、告別革命立場的作品,《生死疲勞》卻對兩種土地所有制之間的矛盾給出了另一種回答。區(qū)別于與梁生寶和養(yǎng)父出身相同而志向不同,藍(lán)臉雖然是地主西門鬧家的長工,與養(yǎng)父屬于不同的階級,但在小說中階級意識已被模糊,“長工”與“地主”混溶在一起,藍(lán)臉與西門鬧轉(zhuǎn)世投胎的牲畜親密合作,他們共同信仰的“生父”是超越了階級的“土地”本身。藍(lán)臉的一畝六分地是他用生命捍衛(wèi)而得以存留的,他是小說中對土地價(jià)值保持頭腦清醒的唯一一人,土地就是他的信仰本身——無疑,莫言不僅要把藍(lán)臉?biāo)茉斐伞叭袊詈笠粋€單干戶”,也要把他塑造成“全中國最后一個真正的農(nóng)民”。中國是一個農(nóng)業(yè)大國,幾千年來土地是農(nóng)民賴以生存的命脈和不可動搖的根基;而中國又是一個人口大國,土地資源的稀缺造成了中國特有的精耕細(xì)作的小農(nóng)經(jīng)濟(jì)模式,孕育了普遍的小農(nóng)思想,而小農(nóng)思想的核心就是珍視土地和“私”的精神。在費(fèi)孝通看來,中國的鄉(xiāng)村的基層結(jié)構(gòu)——無論是生產(chǎn),還是倫理道德——是一個“差序格局”,是以“己”為中心,再像水紋波浪一樣層層外推的,因此,“私”精神驅(qū)動的私有制心理由來已久,而私有制最重要的收編對象就是作為生產(chǎn)資料的土地。正是因?yàn)闇?zhǔn)確地抓住了農(nóng)民對“耕者有其田”的渴望,共產(chǎn)黨成功地在革命年代獲得了廣大農(nóng)民的擁戴,并在建國后通過土地改革一舉在農(nóng)村真正扎穩(wěn)了政權(quán)。其實(shí)藍(lán)臉、梁三老漢、富裕中農(nóng)郭世富、共產(chǎn)黨員郭振山在擁有土地后試圖走個人發(fā)家之路的思維古已有之:“絕大多數(shù)農(nóng)民都深深地依附于自己的土地,傳統(tǒng)的勞作習(xí)慣、宗教活動和社會價(jià)值觀強(qiáng)化了農(nóng)民對土地的依附。土地改革的絕大多數(shù)受益者都期望在自己土地上的勞動能給他們帶來相對富裕的生活。”?顯然,共產(chǎn)黨只把土地改革當(dāng)做社會主義建設(shè)的過渡手段,土地私有制是要被逐步消滅的,但是“長期以來對‘農(nóng)民的個人主義’十分敏感的黨的領(lǐng)導(dǎo)人意識到,土地改革強(qiáng)化了農(nóng)民對自己土地的依附性”?,這樣,五十年代中期,共產(chǎn)黨的意愿與農(nóng)民的意愿之間就產(chǎn)生了“裂隙”。這個裂隙后來為共產(chǎn)黨政權(quán)所不能容忍,一舉加快了原來較為穩(wěn)健的集體化進(jìn)度,這才有了后來的人民公社的神話及其破滅。兩部小說的對立正是在這“裂隙”之中孕育而出的,毛澤東“堅(jiān)信大多數(shù)農(nóng)民——其中百分之七十是貧農(nóng)和下中農(nóng)——將會自愿走社會主義道路,其余農(nóng)民在看到合作社的經(jīng)濟(jì)優(yōu)勢后,也會走上這條道路”?,這是《創(chuàng)業(yè)史》敘事邏輯,但是《生死疲勞》將曾經(jīng)在十七年中被壓抑、遮蔽的農(nóng)民“私”精神的一面放大到極致,展現(xiàn)出農(nóng)民中還有以土地而非共產(chǎn)黨為“生父”,對土地抱有絕對信仰的一支,他們并不像毛澤東言之鑿鑿的具有“極大的社會主義積極性”,在狂熱的烏托邦追求和個人崇拜的神話中,其實(shí)也隱藏著一群始終頭腦清醒,勤勉勞動,沒有“忘本”的人。
在指認(rèn)“生父”的過程里,莫言重述了合作化運(yùn)動中當(dāng)代農(nóng)村與當(dāng)代農(nóng)民,要處理的是曾經(jīng)被遮蔽了的歷史褶皺中的遺跡。社會主義公有制社會,在這里更像是一個被共產(chǎn)黨建構(gòu)出來的烏托邦式的“想象的共同體”,它的破產(chǎn)足以說明典型革命話語體系的虛偽和失敗。而在《生死疲勞》中被傾注了“認(rèn)祖歸宗”式的情感認(rèn)同的土地,就更見出了對“革命”的厭惡,以及對鄉(xiāng)土社會的懷念。農(nóng)民私有化的意愿,與千年鄉(xiāng)土中國的生態(tài)、社會格局和思想習(xí)性密切相關(guān),并非簡單的階級話語、“自發(fā)的資本主義腐朽勢力”可以概括,而且也沒有輕易被公有化浪潮吞沒。它是漫長的革命歲月底下的暗流,在改革開放后新的歷史語境中重見天日,也在新的歷史際遇中遭遇了新的土地私有和合作勞動的問題,但這已不是本文要處理的話題了。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農(nóng)業(yè)大國,中國的農(nóng)民,乃至中國人的精神都與土地密不可分。新中國成立以來,隨著工業(yè)化、城市化、現(xiàn)代化的推進(jìn),農(nóng)村的功能地位和權(quán)力格局被打破、重構(gòu),農(nóng)民經(jīng)歷了與土地關(guān)系的幾度起落。隨著1990年代以來的“三農(nóng)問題”得到普遍關(guān)注,農(nóng)村凋敝、小農(nóng)破產(chǎn)、失地農(nóng)民和城市貧民化的問題,無一不與土地所有制密切相關(guān)。農(nóng)民與土地的關(guān)系,私有制和合作化的關(guān)系,都是值得探討的重要課題。從《創(chuàng)業(yè)史》到《生死疲勞》,兩個不同的“生父”的話語更替,自公/私之間共產(chǎn)黨與農(nóng)民的意愿“裂隙”而起,可從中窺得共和國幾十年來農(nóng)村變遷的一角。兩部小說采用了兩種敘述范式,本文并不想要對兩種范式作出價(jià)值判斷,但是它們確實(shí)提供了截然不同的立場與視野,為我們思考中國的農(nóng)村土地問題、中國農(nóng)民的情感模式提供了不同的向度。
三、歷史的多重面孔
“創(chuàng)業(yè)”和“伸冤”分別是兩部小說的敘事動力,梁生寶所追求的“創(chuàng)業(yè)”,創(chuàng)的是農(nóng)村社會主義改造的“大業(yè)”,與梁三老漢、“蛤蟆灘三大能人”代表的個人“創(chuàng)業(yè)”之間的矛盾形成文本結(jié)構(gòu)內(nèi)部的張力,推動故事發(fā)展,最終以前者對后者的勝利(暫時(shí)勝利)告結(jié)。這與柳青作為歷史的“在場者”的身份密不可分,一方面,“在場者”的誠懇與真切毋庸置疑,另一方面又難以避免歷史目光的局限性。消滅地主階級是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在農(nóng)村取得的公認(rèn)的顯著成績:“土地改革運(yùn)動的偉大歷史成就恰恰就是1950年運(yùn)動開始時(shí)宣布的目標(biāo),即消滅作為一個社會階級的地主階級,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使用了比最初預(yù)期中更多的暴力和恐怖手段。”?但作為小說敘事者之一的地主西門鬧,是一個完全與普遍歷史想象相抵牾的地主——西門鬧一生勤勞,和農(nóng)民一樣堅(jiān)持勞動,而且以德服人,樂善好施,不符合我們常描述的地主階級游手好閑的“寄生蟲”形象,也與毛澤東時(shí)代要打倒的殘酷的封建剝削者相去甚遠(yuǎn)。西門鬧投胎轉(zhuǎn)世作驢、牛、豬、狗、猴直至大頭嬰兒藍(lán)千歲,就因?yàn)樗撵`魂在陰曹地府不斷“伸冤”所致,他要申的“冤”,是一個無辜的人,僅僅因?yàn)楸粍澐值摹暗刂鳌鄙矸荻粴⒅D赃x擇了完全與歷史對立的敘述立場,諷刺歷史與革命,基本承續(xù)了1980年代以來余英時(shí)否定“激進(jìn)的革命”,李澤厚和劉再復(fù)“告別革命”的主流意識形態(tài),但是就小說本身也有概念化的傾向,“缺乏對歷史的同情與理解,也缺乏與中國民眾的血肉聯(lián)系”是小說為人詬病之處。?但是無論怎么說,“創(chuàng)業(yè)”與“伸冤”確實(shí)呈現(xiàn)出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情感結(jié)構(gòu)和歷史面孔。
另外一個有趣的現(xiàn)象是,《創(chuàng)業(yè)史》中柳青的進(jìn)化論的史觀是將目光投向未來/共產(chǎn)主義社會,而莫言則給出了一個截然不同的立場,他認(rèn)為共和國五十年的建設(shè)是失敗的,似乎更加認(rèn)同過去/傳統(tǒng)鄉(xiāng)土社會的價(jià)值準(zhǔn)則。兩部小說在許多問題上的價(jià)值評判截然相反。在這樣的對讀中,柳青站在1960年代將目光投向“未來”,莫言站在新世紀(jì)卻將目光回溯到“過去”——他們的目光在歷史之維中相遇了,認(rèn)同的時(shí)代對象卻完成了一個“顛倒”,這個畫面感很強(qiáng)且略顯吊詭的情境,既能在我們理解農(nóng)村土地所有制、農(nóng)業(yè)合作化歷史乃至整個中國當(dāng)代史的過程中給予啟發(fā),也對如何理解“歷史”本身提供了一個有趣的入口。
理解歷史是我們?nèi)绾巍跋胂笾袊钡钠瘘c(diǎn),如何公正地對待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史,進(jìn)一步說,如何公正地對待共和國史,是當(dāng)代文學(xué)領(lǐng)域的重要課題。“重要的不是故事講述的年代,還是講述故事的年代”,無論是梁生寶這樣的農(nóng)民黨員,還是地主西門鬧,還是單干戶藍(lán)臉,都只是作者建構(gòu)出來的藝術(shù)符號,不能完全符合歷史的真實(shí)性。因此,說柳青的寫作太過于“理念化”也好,說莫言缺乏對歷史的理解和同情也罷,他們都是在使用文學(xué)超越了歷史本身的藝術(shù)性,嘗試揭示歷史地表下潛藏的種種可能性——是被呈現(xiàn)出的歷史本身的可能性,也是我們理解歷史的可能性。
正如特里·伊格爾頓所說,“理解”在某種意義上始終具有“回顧”的性質(zhì),而這也就是黑格爾所說的密涅瓦的貓頭鷹只在黃昏時(shí)起飛的含義。一個現(xiàn)象的來生(afterlife)乃是其意義的一部分,但這一部分卻是“在場者”很難看透的意義。“如果歷史是向前運(yùn)動的,關(guān)于他的知識就是向后運(yùn)動的,所以在寫我們自己的不久的過去之時(shí),我們總是不斷地在另一條路上遇到向我們走來的自己”?。其實(shí)講述歷史又何嘗不是一種這樣的行為呢?隨著時(shí)間的推移和“后來者”的出現(xiàn),講述歷史的話語權(quán)就要在“在場者”和“后來者”之間形成互補(bǔ)與對抗,“后來者”能夠提供解釋的多樣性和豐富性,但是孰優(yōu)孰劣并不完全以講述時(shí)間的先后為標(biāo)準(zhǔn)。此時(shí),理解歷史的人,就更需要具有不被任何一方局限的獨(dú)立與清醒。進(jìn)一步說,在我們習(xí)慣了批評十七年文學(xué)是一種被“舊”的、“左”的意識形態(tài)所控制的文學(xué)時(shí),或許也應(yīng)該警惕落入新時(shí)期以來“新”的、“右”的意識形態(tài)的控制和局限之中。歷史具有多重面孔,在回顧和展望之中常常更新自己觀察歷史的“眼鏡”,也是重讀《創(chuàng)業(yè)史》和《生死疲勞》帶來的一種啟示。
注釋:
①農(nóng)業(yè)合作化運(yùn)動又稱農(nóng)村集體化運(yùn)動。經(jīng)過了建國初期三年的恢復(fù),黨在1953年提出了過渡時(shí)期的總路線,將“一化三改造”——國家工業(yè)化和對農(nóng)業(yè)、手工業(yè)、資本主義工商業(yè)的社會主義改造制定為過渡時(shí)期的總路線和總?cè)蝿?wù),以重工業(yè)建設(shè)為中心的第一個五年計(jì)劃正式開始。與此同時(shí),在農(nóng)村,隨著土地改革運(yùn)動的完成,農(nóng)村合作化運(yùn)動在1953年步入正軌。所謂的農(nóng)村集體化,就是要逐步廢除土地私有制,向社會主義公有制逐步過渡,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根據(jù)黨的計(jì)劃,先后依次要經(jīng)過互助組、初級合作社和高級合作社三個階段。
②曹文軒:《二十世紀(jì)末中國文學(xué)現(xiàn)象研究》,作家出版社2003年版,第291頁。
③馮牧:《初讀<創(chuàng)業(yè)史>》,《文藝報(bào)》1960年第1期。
④嚴(yán)家炎:《談<創(chuàng)業(yè)史>中梁三老漢的形象》,《文學(xué)評論》1961年第3期;《關(guān)于梁生寶形象》,《文學(xué)評論》1963年第3期。
⑤閻綱:《致函<創(chuàng)業(yè)史>及農(nóng)村題材創(chuàng)作討論會》,轉(zhuǎn)引自嚴(yán)家炎主編:《二十世紀(jì)中國文學(xué)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68頁。
⑥此處參考王一川對《創(chuàng)業(yè)史》所做的格雷馬斯“符號矩陣”分析,見王一川:《卡里斯馬典型與文化之境(一)——近四十年中國藝術(shù)主潮的修辭學(xué)闡釋》,《文藝爭鳴》1991年第1期。
⑦“反英雄指的是現(xiàn)代小說或戲劇中其品行與嚴(yán)肅文學(xué)作品中傳統(tǒng)的主角或英雄形象相去甚遠(yuǎn)的主要角色。與偉大、高尚、威嚴(yán)或英勇的英雄形象相反,反英雄體現(xiàn)的是卑鄙、下流、消沉、無能或奸詐的人物品行。”(艾布拉姆斯:《文學(xué)術(shù)語與詞典》(第七版))而筆者此處使用的“反英雄”雖然也不同于傳統(tǒng)英雄形象,但在作品中依然是正面人物,仍具有一般意義上英雄的氣質(zhì)與品行。而新時(shí)期文學(xué)以來的“非英雄化”傾向,更多的側(cè)重于取消“英雄”的存在,恢復(fù)人物的平民化與日常性書寫,也不同于本文中的“反英雄”。
⑧⑨?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上海世紀(jì)出版社2007年版,第42頁、第72頁、第6頁。
⑩毛澤東:《關(guān)于農(nóng)業(yè)合作化問題》,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0頁。
?柳青:《提出幾個問題來討論》,謝冕、洪子誠主編:《中國當(dāng)代文學(xué)史料選(1948-1975)》,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1995年版,第597-598頁。
?王一川:《卡里斯馬典型與文化之鏡(一)——近四十年中國藝術(shù)主潮的修辭學(xué)闡釋》,《文藝爭鳴》1991年第1期。
????[美]莫里斯·邁斯納著,杜蒲譯:《毛澤東的中國及其后:中華人民共和國史》(第三版),中文大學(xué)出版社2005年版,第121頁、第124頁、第131頁、第92頁。
?李云雷:《如何講述中國的故事——關(guān)于近期三部長篇小說的批評》,《上海文學(xué)》2006年第11期。
?[英]特里·伊格爾頓著,伍曉明譯:《二十世紀(jì)西方文學(xué)理論》,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07年版,第219頁。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xué)中文系)
責(zé)任編輯 馬新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