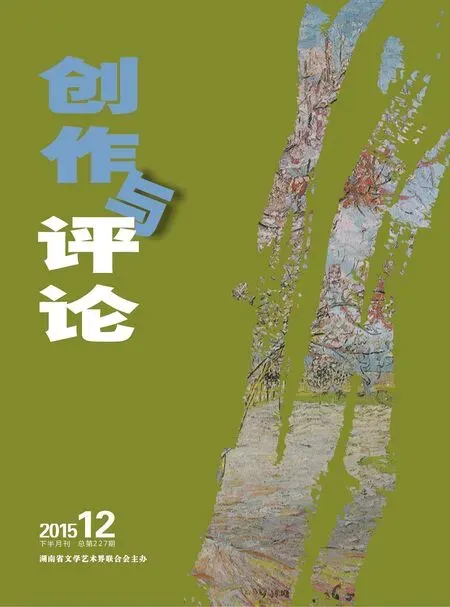《云南映象》:經驗的展示與消費
○閆楨楨
《云南映象》:經驗的展示與消費
○閆楨楨
作為現代性或者說全球化的后果,“地方性”的文化經驗越來越成為文化關切的焦點,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在中國的廣泛開展可謂是其佐證之一。“保護”一方面體現出對于地方性民俗文化的重視,另一方面也說明其生存空間日漸逼仄。地方性的民俗文化在現代社會中如何生存與傳播?基于“地方性”文化的“自我”如何在文化全球化時代的語境中進行呈現與展示?這種呈現與展示是否足以維護族群的文化特質?對于這些問題的思考敦促人們在眾多的文化現象中尋求啟發與答案,而《云南映象》及其引發的討論則為這樣的思考提供了一個可分析的實例。
2003年8月,楊麗萍的大型原生態舞蹈集《云南映象》在昆明會堂首次公演。此后,在長達十年的時間中,《云南映象》在全國乃至全球范圍內都有著不俗的票房成績。截至2013年底,《云南映象》已經在全國范圍內巡演將近4000場,在十余個國家和地區累計演出50余場①。無論在作品的影響范圍、知名度、演出場次或是票房收入等方面,都可被視為當代中國舞蹈藝術在演出市場與藝術創作方面“里程碑”式的作品。
《云南映象》的票房“神話”無疑為中國舞臺創作注入了一支有力的強心劑,而與此同時,該劇主創人員關于“原生態”的多方闡釋則引起了評論界與理論界的雙重關注。《云南映象》的創新集中體現在其對傳統民族民間舞蹈作品形式的突破,而其在國內國外市場獲得的高度認可,也讓我們重新審視作品中關于“中國形象”的呈現。更重要的是,當展示性的地方性經驗通過《云南映象》獲得消費價值的同時,也使得地方性經驗本身不得不面對一個懸而未決的未來。
一、“原生態”之爭
中國民族民間舞蹈在劇場舞臺上的創作實踐由來已久。這些在農業文明社會中與日常生活緊密相連的舞蹈形式,在新中國初建的特定歷史時期,肩負著整合社會大眾意識形態的重任被納入到社會的主流文化形式中。于是,本應自洽于日常生活的民俗舞蹈通過專業舞蹈家們的提煉、改編,以一種精致的、審美化的形式出現在劇場舞臺上。這種“化俗為雅”的藝術創作方式,在為中國民俗舞蹈提供舞臺化的生存空間的同時,也始終面臨著其文化屬性上的詰問,現代劇場對于舞蹈形式的要求與民間舞蹈自身相去甚遠,將民間舞蹈作為舞臺作品進行呈現,必然要進行“削足適履”般的再加工。
于是,《云南映象》所強調的作品的“原生態”屬性,自然被看作是對過往舞臺民間舞蹈創作方式的一種否定。在《云南映象》的主創來看,“‘原生態’是最自然、最接近人性的一種表現形態。農民們認為萬物有靈,人需要同天和地、萬物及神靈溝通,而舞蹈就是人與萬物溝通的惟一方式。這也是這部歌舞集中70%演員是農民的原因”。②《云南映象》的主創楊麗萍認為,這部“歌舞集”中所有的藝術形式都是經過長達15個月的時間,在云南各地進行采風后,直接選取的“原汁原味”的民俗形式,為了凸顯“原生態”對民俗本身的尊重,演員、服飾、道具、器樂都最大限度地保持了原貌。可見,《云南映象》對于“原生態”的解釋主要是依托兩點:演員背景和形式來源。
不過,也有學者提出:“‘原生態’文化具有比較嚴格的界定。即原生形態(基本不帶加工、包裝)、原生生態(未脫離其生成、發展的自然與人文環境)、自然或準自然傳衍,它是木之本,水之源——為民眾及藝術家所共享。《云南映象》顯然是藝術家創作的舞臺藝術品,凝聚了藝術家的個性化創造和相當程度的舞臺包裝,而非民間藝術的‘土坯’。以‘原生態舞蹈’為‘賣點’并不高明——并未提高其文化藝術價值……盲目地打出‘原生態’之旗號,既低估了《云南映象》的藝術創造力,更會混淆“文化源頭”的概念。”③
《云南映象》的“原生態”之爭所呈現出來的是鄉土民俗生態與城市文化傳播方式之間的天然悖論。這種悖論不僅屬《云南映象》,甚至也不僅屬民俗舞蹈。在當代中國城鎮化、全球化的匆匆步履中,一個前現代的鄉土中國正在悄然逝去。特定的民俗形式本就是生活經驗的產物,一旦生活經驗發生了變化,民俗形式也必然會產生相應的變化,我們自然可以使用“保護”的方法來保留這些鄉土民俗的形式,但是“博物館”式的展現卻無力承擔起對民俗的動態保護功能。這也是《云南映象》之“原生態”悖論所產生的根本原因,當這些充滿著生命經驗的民俗歌舞被移植到“劇場”這樣一個城市文化的代表性空間時,舞臺與觀眾之間天然存在空間與心理距離已經注定了《云南映象》中的民俗形式只能成為“展示”的對象。
二、“野性”中國
不論關于《云南映象》之“原生態”做法褒貶如何,市場對其的反應可謂是積極熱烈。
不妨從三個層面來對其票房魅力進行分析。
首先,對于國內觀眾來說,作為一種對“原生態”文化的展示,《云南映象》可以說是當代中國都市文化與少數民族部落文化之間的一次深層次的“互視”,盡管這種“互視”也許并不具備平等或對話式的內在心理機制,但是從其所引發的行為效果來說,塑造某種“別處的生活”從而滿足人們對“他者”生活的想象以及獵奇心態,無疑是《云南映象》在國內獲得良好票房的一個重要因素。《云南映象》中的歌舞,的確保留了民俗的樣式,但是卻脫離了民俗的功能。民俗歌舞中最為重要的參與感,以及由此產生的族群認同感在劇場空間里是無法產生的。而劇場獨特的空間使得“重在參與”的民俗活動被舞臺上的“秀”與舞臺下的“看”取而代之。觀看《云南映象》成為了一種“觀賞”其他民族生活方式的消費活動,而這種“觀賞”中隱隱透露出來的是一種“獵奇”的心態。更重要的是,不論觀看者與被觀看者是否承認,這種“獵奇”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種“都市文明”對“原始奇觀”的居高臨下式的心態。
其次,《云南映象》的成功與楊麗萍作為舞蹈家的廣泛知名度和個人號召力有著直接的關系。在現代社會分工日益精細,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的今天,楊麗萍似乎是一個“不走尋常路”的特例,她是中國第一個舉辦個人舞蹈晚會的舞蹈家,卻從未接受過任何專業舞蹈教育機構的培養。“小的時候我的奶奶告訴我,跳舞是為了和神對話;許多年之后,我明白了她的話。每當我在心靈的天地里伸開雙臂起舞時,我感覺到臂膀無限延伸、延伸,這時神會握住我的手,我能感覺到我的靈魂從我的身體里飄蕩開來,這種美妙的感覺使我的靈魂得到了最清靜的安撫。”④在這段自述的文字里,楊麗萍為自己的舞蹈之旅蒙上了一層神秘的信仰色彩,“跳舞是為了和神對話”,舞蹈不再是一種需要經過專業訓練和舞臺包裝的藝術行為,也沒有一絲與市場、商業、盈利相關的味道。舞蹈在楊麗萍的敘述中成為一種無關俗世生活的精神存在方式,被賦予了形而上的神學意味。同樣,在楊麗萍的筆下,云南呈現出來的是一種有別于現代城市的“他鄉”形象,這里的人以歌舞為伴,在他們的世界里奉行著天地、陰陽這些仿佛獨屬前現代的觀念。對于習慣了城市生活里精致而矯情的消費景象的人們來說,這種原始部落里的生活經驗攜帶著泥土、草葉和牲畜糞便的味道,與自然融為一體,閃爍著某種逃離消費主義的精神之旅的誘人光芒。
最后,《云南映象》之所以在海外演出市場獲得廣泛的認可,其主要原因也在于《云南映象》所呈現出的獨特的中國形象。長期以來,在國外的演出市場中,中國在舞臺劇目中常常以兩種形象出現:一種是以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等為代表的“西式中國”,另一種是京劇、武術等傳統藝術中的“古典中國”。前者將西方藝術形式與中國元素進行融合并置,讓觀眾在熟悉的藝術形式中發現新鮮的中國元素,而后者則是將中國傳統藝術形式與舞臺科技相結合,塑造一種“古典中國”的文化形象。而《云南映象》則另辟蹊徑,用民俗歌舞構建了一個“野性中國”的文化形象。與以往海外演出劇目中的“中國形象”有所不同,《云南映象》并沒有將“中國”作為自身的文化歸屬定位,而是突出了“云南”這樣一個具有明顯地域特色的文化背景。這種獨具地域特色的“中國”形象打破了以往海外演出市場中始終以“中華民族”為基調的國族形象,呈現出一種獨特的“野性”中國形象。《云南映象》對于“原生態”的擇選突出了其粗糲原始的神秘氣質,它既非京劇的細膩婉約之美,也與武術的陽剛氣質有別;不屬于細膩婉約的“雅士文化”,也不同于縱情不羈的“武俠文化”。《云南映象》中的“中國”是一個原始、神秘、充滿前現代氣息的想象之地,對于浸淫于當代工業文明中的海外觀眾來說,“野性”“神秘”的前現代形象,在情感上似乎比一個正在崛起的超級大國形象更易于接受,也更容易勾起人們對作品的好奇心。
《云南映象》機敏地把握到了當代都市生活與西方工業文明宰制下,人們對于那些充滿自然、神秘氣息的原始文化的想象,無論是作品形式還是主創人員的背景,都在努力營造一種與當代生活經驗迥然不同的文化氣質。換句話說,《云南映象》的票房“神話”既離不開主創團隊的藝術創意,也離不開特定文化語境所賦予其的歷史性契機。只有在全球化背景下,這種充滿原始生命力的特殊經驗才會成為一種可供消費的資源,才會生成獨具魅力的“中國形象”。
三、被展示的“經驗”
《云南映象》的成功可謂有目共睹,由“原生態”引起的思考也依舊方興未艾,然而對于《云南映象》及與之相似的文化現象而言,其帶來的話題遠遠超出了這些現象自身。
當我們走進一個民俗博物館,除了展柜里與生活相關的各色器具或是民俗服飾,最不可忽略的是對這些展出物品的文字解釋。一個殘破的器具,如果沒有特定的背景介紹,相信沒有任何人可以看出它的價值和意義。然而,在《云南映象》中,所展示的并非某種民俗形式或是與之相關的地方性知識,而是一種云南地區少數民族的生存經驗。對于觀眾而言,這些農民身份的演員和他們的舞蹈之所以令人動容,是因為觀眾們遭遇到了一種全新的經驗。這種經驗拒絕科學的或是理性的觀念,而是憑借身體的直覺和遠古的神話來組織生活。在這樣的經驗里,身體不再是受到來自各方權力規訓的對象,而是與自然和諧共振。《云南映象》中的舞蹈與其說是一種民俗形式,不妨說是一種生存狀態,人們也許并不向往山區部族里物質貧瘠的生活環境,卻無法拒絕舞臺上令人激動的身體狀態。
事實上,在世界各地,人們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文化在各色空間中被“展示”:博物館、民俗旅游村、文化遺址或是主題公園,所有的場所似乎都在展示著文化的某個側面。英國學者貝拉·迪克斯(Bella Dicks)認為:“展示將文化作為景觀和知識保留下來;既可以讓人們大飽眼福,也能增進知識。可能有人認為,文化展示的教育和保存功能僅僅用于掩蓋其‘真正’的作用——誘惑消費者。但大家不妨將這兩種功能看作齊頭并進的。將事物轉化為可被參觀、可被觀賞的將延續其生命,不僅可以為他者充當展示,也可以為自己用作文化/教育的資源。”⑤在她看來,對于文化,特別是對具有地域性特色的文化進行“展示”性的開發盡管會出現種種不盡人意的問題,但也并非一無可取。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對于地方性知識的“展示”也許可以成為其延續的一種方式,但是對于經驗的“展示”是否能夠成為經驗的延續呢?對于“經驗”來說,最為重要的應該是“主體”,這些來自于村落中的農民恰恰是因為攜帶著原初的生活經驗,才被楊麗萍選中來出演《云南映象》。“我堅持啟用那些村子里的土生土長的農民,只有這些樸實憨厚的、為了愛為了生命而起舞的人,他們在跳舞時的那種狂歡狀態,才最能表現這臺原生態歌舞的精神。”⑥楊麗萍意識到農民們跳舞的狂歡狀態正是“原生態”歌舞的魅力所在,卻沒有意識到這種狂歡狀態并非憑空而來。如果沒有夜里零下20度的生存環境,沒有辛苦勞作后的收成,沒有長期對生活的隱忍和承受,何來為了生命起舞的狂歡狀態?“原生態”歌舞中瞬間迸發的魅力正是農民們日常生活經驗的“饋贈”,這種狀態是隱忍下的瞬間釋放,是困苦中的短暫歡愉;而一旦這些日常生活經驗被舞臺的表演經驗所取代,這些農民們也就只能重復民俗歌舞的形式,而無法復制曾經屬于自己的生活經驗了。
在這里,《云南映象》中隱含著的關于經驗“展示”的悖論已經呼之欲出。一方面,民俗歌舞形式中所蘊含的地方性經驗在舞臺上構建了有別于城市生活經驗的“異文化奇觀”,這種展示在一定程度上激發了觀眾對這些瀕臨消逝的“原生態”歌舞的興趣,也令“原生態”歌舞煥發出強健的市場生命力,作為一種可消費的文化資源來說,也許能夠對民俗歌舞形式起到一定的“保護”作用。另一方面,對“經驗”的舞臺展示卻是以犧牲實際的地方性經驗來完成的,當原本的生活經驗被作為展示的文化資源時,流失與改變也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
更重要的是,這種對于“原生態”的展示在保護民俗生態的同時也在遮蔽著它們,當一種“原生態”的民俗資源在舞臺上獲得廣泛認同時,其原本的狀態也就越發淡出人們的視野。當“原生態”歌舞可以在舞臺上作為一種文化資源被消費時,真實的云南村落里的日常生活經驗也就不再具備吸引力。
當然,《云南映象》的悖論并不獨屬于它自身,在文化全球化的語境下,文化與生活方式的獨特性越來越獲得廣泛承認,而這種對“獨特性”的強調恰恰是全球化的產物。“如同羅伯遜進一步指出的,全球化使文化特殊主義成為可能,文化特殊主義也是全球化的產物。全球化培育了我們對具有文化差異的全球系統的意識,使我們所有人都與文化意義上的他者概念相協調。”⑦在全球化的文化邏輯下,那些被標示出的文化“飛地”承擔著文化多樣性的責任:“它們被給予保護(通過規劃和環境調節),并展示其真實性以及與其他地方的不同之處,而那些地方都已絕望地屈服于現代性。在此過程中,它們變得可被參觀,因為它們成了‘風景’,使參觀者能夠確信文化和環境的多樣性得以幸存。因此,現代性運用文化展示來填補自己制造的空缺。”⑧正是在此意義上,《云南映象》中的“原生態”歌舞及其蘊含的地方性經驗成為一種在消費主義的視野中被“發現”的價值,這種價值對于市場來說是真金白銀,而對于那些“被展示”的經驗來講,似乎還遠沒有到可以定論的時候。
注釋:
①參見王立元:《楊麗萍:跨越“映象”十年》,《中國文化報》2013年12月24日。
②宋辰:《云南映象:“原生態”文化轟動全球》,《中國經濟信息》2006年第12期。
③資華筠:《云南映象—靈脈血肉連著根》,《光明日報》2004年4月21日。
④⑥楊麗萍:《我與“云南映象”》,《中國民族》2004年第5期。
⑤⑦⑧貝拉·迪克斯著,馮悅譯:《被展示的文化:當代“可參觀性”的生產》,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14-15頁、第30頁、第30頁。
(作者單位:北京舞蹈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