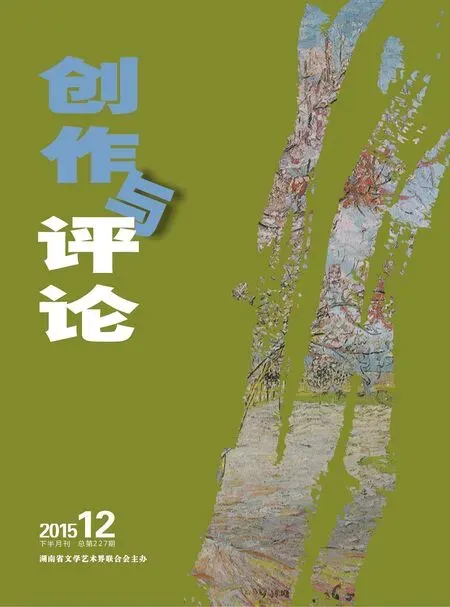“回歸傳統”后的“講故事”——從敘事視角解讀2000年以來莫言長篇小說
○康建偉
“回歸傳統”后的“講故事”——從敘事視角解讀2000年以來莫言長篇小說
○康建偉
“回歸傳統”構成了莫言2000年以來創作的主導趨向。2012年12月7日,莫言在瑞典學院發表演講《講故事的人》,主題便是“回歸傳統與講故事”。“問我師從哪一個,淄川爺爺蒲松齡。”“長大方知人即鬼,蒲公深意我能解。”①
中國敘事文學可以追溯到《尚書》,大盛于《左傳》,虛構性敘事文體,自六朝志怪經變文與唐人傳奇,到宋元之際分為兩支,一為文言小說,一為白話小說。前者以《閱微草堂筆記》和《聊齋志異》等清代文言小說為新的高峰,后者則以明代四大奇書和清代的《儒林外史》和《紅樓夢》為代表之作。④此譜系,莫言推崇《聊齋志異》,應視為對傳統敘事中較強調虛構志怪一脈的欣賞。季紅真具體剖析了莫言與中國敘事傳統的關系:“神話鑄造了莫言的思維方式,六朝志怪影響了他取材的向度,唐傳奇則激發了他奇詭的想象力。”⑤但是正如莫言自道:“這種回歸,不是一成不變的回歸,《檀香刑》和之后的小說,是繼承了中國古典小說傳統又借鑒了西方小說技術的混合文本。”⑥因此,莫言及其代表的中國敘事,已決非是傳統敘事文學的簡單移植,而是混合交融難分中西。在全球化語境下對于中國敘事的強調,也只能是對于傳統底蘊的承續。從這個意義上,以及民族文學與世界文學的角度來講,“回歸傳統”,也是另一種形式的“走向世界”。
“敘事就是講故事。”⑦在這一簡潔的表達中暗含了兩條發展路徑,或者強調“故事”這一所講之內容,或者強調“講”這一敘事行為。本文擬從敘事視角這一“講”的角度,對莫言在本世紀以來發表的《蛙》《檀香刑》《四十一炮》《生死疲勞》等四部長篇小說略加評析,以期理解“回歸傳統”/“走向世界”后“講故事”的莫言。
一、《檀香刑》:多聲部逐章換位移形換影
《檀香刑》是莫言大踏步撤退的標志性之作,經歷了絢爛斑駁的現代派手法,爭奇斗艷的感覺大爆炸,以及肆無忌憚的語言狂歡之后,莫言終于尋找到了自己的方法,植根于傳統土壤的民間敘事,以說書人的口吻腔調,敷演一幕幕大開大闔,大悲大喜的人間故事。這種“撤退”,既是回歸,更是游刃先鋒之后的再度出發,以退為進。
《檀香刑》以鳳頭、豬肚、豹尾組成三部分,同時鳳頭部與豹尾部各以眉娘浪語、趙甲狂言、小甲傻話、錢丁恨聲等四字主謂短語作為標題。就小說敘述視角而言,鳳頭部與豹尾部換章換人換視角,逐章換位,移形換影,自然推進故事進程。在豬肚部,則換為全知敘事,全景交待故事,敘事角度相當清晰。這樣,人稱轉換形成視角轉移,廟堂敘事、士紳敘事以及民間敘事,共同構成一個多聲部的敘事結構,形成一種復調結構,也正是在此意義上,陳思和認為:“復調型的民間敘事結構是莫言小說最基本的敘事形態。”⑧
《檀香刑》共描寫死刑六次:用“鐵門栓”處死太監小蟲子,腰斬國庫庫丁,趙甲舅舅被砍頭,趙甲五百刀凌遲刺殺袁世凱的錢雄飛,斬首“戊戌六君子”,給孫丙上檀香刑。前面五次施刑,敘述者都是趙甲,他以國家機器兼“技術專家”的第一人稱視角,將施刑過程中血淋淋的場面、自身心理、受刑者情狀以及看客的神情清晰地表現了出來。特別在對施刑過程的描寫中,莫言似乎也變成了一個施刑者,將對受刑者凌遲的每一刀同時也割向了讀者,挑戰著讀者閱讀的極限。讀者以一種既拒斥又期待、欲罷不能的心理等待著趙甲的每一刀。在檀香刑——這一趙甲的收山之作中,讀者更是期待莫言以他如椽巨筆再次肆虐我們的神經,然而在烘云托月的描寫之后,并未看到對趙甲濃墨重彩的描寫。作者筆鋒一轉,將敘事視角轉向趙小甲,以他的感覺整整一章筆盡曲折地描寫檀香刑。趙小甲一如莫言小說中的傻子系列,不諳世事,感覺遲鈍,但幻覺豐富,浮想聯翩。敘事視角的轉變,使得讀者在這里不再看到有如專家講座般的關于施刑技法解析與心理刻畫,而是如同趙小甲一般麻木地在趙甲指揮下按部就班地參與到施刑之中。趙甲似乎凌駕于生命之上,完全是主導著施刑過程的“父親”的代表。通過互為言說的方式,形成了一種多聲部的敘事。
二、《四十一炮》:回溯性敘事中的兒童視角
莫言小說中存在著一個獨特的敘事視角——兒童視角。轟動文壇的《透明的紅蘿卜》中奇異的色彩感與想象力,就是借助于始終一言不發的黑孩的視角。1986年發表的《紅高粱》則正式開始使用“我”這一第一人稱敘事,講述我爺爺與我奶奶的故事。而到了《四十一炮》中通過羅小通這個身體已是大人,而精神依舊孩子的視角來講述整個“我”對“肉”的欲望,以及屠宰村到肉聯廠的變遷。正如作者自道:“他是我的諸多‘兒童視角’小說中的兒童的一個首領,他用語言的濁流沖決了兒童和成人之間的堤壩,也使我的所有類型的小說,在這部小說之后,彼此貫通,成為一個整體。”⑨這個首領,不僅表現在這一敘事視角的延續與總結上,更多地表現在這一視角的突破上,羅小通按其年齡應該有二十多歲,身體業已成熟,但心理上依舊沉湎于記憶,沉湎于最為原初的欲望:肉與奶水。角心人物在道德上或智力上比較低下,就會出現仰角觀察:“這種仰角觀察自然破壞了被敘述世界的真實感:事件和人物在角心人物意識中被扭曲,被模糊化,被主觀化。”⑩當然這種沉湎不是弱智、癡呆,而是一種對于“肉”偏執的沉溺。
羅小通的回憶部分屬于回溯性敘事中的兒童視角。《四十一炮》的敘述者存在著一種悖反的情狀,一方面,這是一個二十余歲的青年在追憶自己少年往事。這位已經成年的羅小通具有一種耽迷幻覺的心理結構,具體表現在其對“肉”的沉迷與交流。另一方面,這個被追憶的少年時的羅小通比之同齡人有著明顯的成熟性、成年性,如其在肉聯廠車間主任崗位上“洗肉”程序的設計。這兩方面共同構成羅小通這個獨特的存在,同時也類似于回溯性敘事中的兒童視角:“回溯性敘事中再純粹的兒童視角也無法徹底摒棄成人經驗與判斷的滲入。回溯的姿態本身已經先在地預示了成年世界超越審視的存在。”?這樣,在這一文本里,心理偏執的成人,過度成熟的少年,再加上兩者之間的交集——追憶,共同形成了一個極富張力的文本,回溯性敘事中兒童視角的韻味也就生成于這樣一種時間跨度之中。
三、《生死疲勞》:流動視角的流速頻次
《生死疲勞》中西門鬧依次轉世為白蹄驢、西門牛、豬十六、狗小四、大馬猴以及藍千歲,因此,我們可以說這部小說的主要敘事者就是西門鬧(藍千歲)與藍解放,同時還有他們的朋友“莫言”。就這三個敘事者而言,大頭嬰兒藍千歲才是主導者。?
☆秋風陣陣,枝頭上的樹葉紛紛飄落。有的如蝴蝶,扇動著美麗的翅膀;有的如蜜蜂,轉著“8”字飛舞;有的如降落傘,緩緩地打著旋兒……一片片樹葉,無論是怎樣飛舞,都會緩緩落下,在地上鋪成一條金色的道路。
小說前面四章以藍千歲(即西門鬧、白蹄驢、西門牛、豬十六、狗小四、大馬猴)與藍解放聊天的方式展開,因此,這個“我”因語境的不同而指向了不同的講述者。第一部驢折騰(共11章)敘事視角就是白蹄驢(藍千歲);第二部“牛犟勁”(共9章)敘事視角變成了藍解放。第三部“豬撒歡”(共16章)敘事視角又轉向了豬十六(藍千歲)。以上三部基本以整部為一單元,依次更替敘事人稱。小說第四部“狗精神”(共17章),第37、39、41、43、45、47、49、51等奇數章敘事人稱為狗小四(藍千歲),而38、40、42、44、46、48、50等偶數章敘述人稱又轉向了藍解放,基本上是奇偶交替更換敘事視角交替講述故事,雖然敘事人交替,但奇偶交替這一規律非常明顯。第四部第52章和53章,表現為每一章內兩個敘事人交替出現,在小說形式上最明顯的標志是以破折號開頭,引出不同的敘事者。第五部“結局與開端”(5節)又引入了小說的另外一個敘事者——作家“莫言”,小說中“莫言”第一次出現是在第四章開頭,提到“莫言”出生,后又有編順口溜,接納私奔的藍解放、龐鳳凰,為他們找工作,尋住房等情節。同時小說屢次引述“莫言”的《太歲》《杏花爛漫》《撐桿跳月》《養豬記》等作品,“莫言”逐漸以配角的身份參與了部分情節,最后第五部分竟轉為主要敘事者,以第三人稱轉述的方式,接管了小說的敘事權,完成了關于結局的交待。
藍千歲、藍解放、“莫言”這三個敘事視角,屬于定點透視,也就是限知視角。三個敘事視角的頻繁轉換,又形成了不定點透視,即“流動視角”。《生死疲勞》第一、二、三部每部敘事人稱依次轉換,第四部前15章依次轉換,第52、53章,章內依次更替,最后第五部引入第三個敘事視角。這種敘事視角的頻繁轉換,便出現流動視角的流速問題,也就是視角轉換的頻率問題。隨著敘事視角轉換頻次的逐漸頻繁,敘事節奏逐漸加快、累積,到第四部,形成高潮,再回落到第五部,交待結局,從而形成了一種世事無常飄忽不定的敘事效果。
四、《蛙》:“展示”與“演述”的交叉跨界
《蛙》由五封書信、四部長篇敘事和一部話劇組成,四部長篇敘事則由四部書信帶出,可視為書信體小說。這樣在同一部小說里,就存在兩種文類形式,書信體小說與話劇劇本。
羅伯特·施格爾斯(Robert Scholes)和羅伯特·凱洛格(Robert Kellogg)在《敘事的本質》(Nature of Narrative)一書里把“敘述者”作為一個區分西方三大文類的重要工具。抒情詩有敘述人(teller)但沒有故事(tale),戲劇有場面和故事(scenes)而無敘事人(teller),只有敘事文學既有故事(tale),又有敘事人(teller)。在敘事文學中,又有“展示”(show)與“演述”(tell)的區別,前者沒有作者的聲音,后者有作者的聲音。按此觀點,《蛙》之書信體小說部分當屬既有故事,又有敘事人的敘事文學,其中故事是關于姑姑的故事,而敘事人則是劇作者蝌蚪。話劇部分只有場面和故事,而無敘事人,在小說部分的敘事人蝌蚪已不具敘事角色,成為話劇中的一個角色。書信體小說部分是敘事人蝌蚪凸顯的演述,而話劇劇本部分則將蝌蚪演述作用淡化,重在客觀展示。這樣,這部小說同時具有“展示”與“演述”,兼具敘事文學與戲劇的形式特點,體現出一種交叉跨界的敘事特色。
從敘事角度而言,《蛙》中敘事者是蝌蚪,這是一個一直以來想以姑姑的一生為素材的話劇作者,小說部分就是蝌蚪給杉谷義人講述的關于姑姑的故事。選擇這樣一位敘事者,有幾個原因。首先,符合作者回歸傳統的美學風格,通過書信體,完成了傳統說書體的現代轉換,劇作者便是說書人,而書信體,則有如說書人的話本。其次,在敘述語言上可實現線性敘事,不瘟不火,如話家常,緩緩道來,而不是快節奏的跳躍表達。再次,也與作品的結構布局緊密相關,因為這樣一位劇作者既便于完成具有文學性的長篇敘事,又能將話劇巧妙地置于小說末尾,而不至于過分突兀。同時,也可以在話劇劇本部分耍點花槍,正如作者所言“帶有某些靈幻色彩”。例如舞臺上一個身穿綠色小肚兜、頭皮光溜溜的孩子,率領著一群坐著輪椅、拄著雙拐、前肘上纏著繃帶的青蛙,嘎嘎咕咕叫個不停,奇幻詭異。又如第八幕劇作者設置了戲中戲電視戲劇片《高夢九》拍攝現場,陳眉叫怨,高夢九斷案,真真假假,如夢似幻。通過這些設置,形成了一種既能投入講述,又能出乎講述的特殊敘事口吻,呈現出一種幻覺現實主義的敘事風格。
2001年莫言宣布“大踏步地倒退”,引蒲松齡為隔代知己,向傳統致敬。2012年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稱其為“幻覺現實主義”,這十二年,雖然毀譽參半,但莫言以自己獨特的風格引領文壇已成不爭事實。本文對莫言2000年以后的四部代表作,從敘事視角層面做了簡要的解讀,也看作這一“莫言現象”的延續。作為一個本身極富個性,具有國際聲譽的作家,其作品內涵豐富,提供了多種解讀的可能性,在當下的時代語境中,作為一個“講故事的人”,莫言這一符號必然承擔更多的能指,承擔著向世界講述中國故事的責任,同時,我們通過莫言也可以體悟到中國故事的力量。
注釋:
①莫言:《師從》《庚寅冬日聽聊齋》,轉載自蘭傳斌:《莫言與蒲松齡和<聊齋志異>》,楊守森、賀立華主編:《莫言研究三十年(下)》,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26頁。
②莫言:《學習蒲松齡》,中國青年出版社2011年版,第2頁。
③郜元寶:《中國作家才能的濫用和誤用》,《文學報》2011年11月17日。
④⑦?浦安迪:《中國敘事學》,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頁、第4頁、第18頁。
⑤季紅真:《莫言小說與中國敘事傳統》,《文學評論》2014年第2期。
⑥莫言:《盛典——諾獎之行》,長江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80-81頁。
⑧陳思和:《莫言近年小說創作的民間敘事——莫言論之一》,《鐘山》2001年第5期,楊守森、賀立華主編:《莫言研究三十年》,山東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191頁。
⑨莫言:《四十一炮·后記》,上海文藝出版社2012年版,第402頁。
⑩趙毅衡:《苦惱的敘述者》,四川文藝出版社2013年版,第81頁。
?吳曉東、倪文尖、羅崗:《現代小說研究的詩學視域》,《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99年第1期。
?王德威:《狂言流言,巫言莫言——<生死疲勞>與<巫言>所引起的反思》,《江蘇大學學報》2009年第5期。
?楊義:《中國敘事學》,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33頁。
(作者單位: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