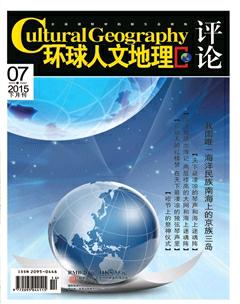淺析民族村寨旅游中“邊緣人”的地方感
摘要:在現今的民族村寨旅游中,經營旅游產業,提供旅游服務的人群多為旅游發展中衍生的“邊緣人”,他們主要是本地中老年經營者和外來經營者。這兩類人群的地方感具有較大差別,前者的地方感主要偏向地方依戀,后者更加偏向地方依賴。而外來者對當地社區帶來的巨大影響,對地方文化發展及當地居民地方感起到一定程度上的影響作用。本文將著眼于本地“邊緣人”和外來“邊緣人”的地方感差別進行分析比較,站在地方感的角度為民族村寨旅游提出建議。
關鍵詞:邊緣人;地方依戀;地方依賴
一、引言
“邊緣人”這一概念最早由德國心理學家K·勒提出,[1]泛指對兩個社會群體的參與都不完全,處于群體之間的人。在普通民族村寨旅游中,“邊緣人”指的是上了年紀或外來的樂意參與旅游業,能夠擔當地方文化、旅游中介人的群體,這一群體逐漸成了文化商人。對于當地“邊緣人”,他們對旅游的促進作用不屬于政府規定范圍,但他們用以接待游客的技能或設施又是當地原始居民不具備的,如能夠使用普通話交流。而隨著旅游在民族村寨中的不斷發展,必然會吸引外來經營者的進入,他們的進入基礎就是對當地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的認同,認同又是對當地文化解讀的基礎,所以在潛移默化中外來個體經營者也就轉變為了當地旅游的“邊緣人”。
“地方”不僅具有地理上的含義, 還有人文、社會心理的內涵。[2]“地方依戀”和“地方依賴”這兩個概念之間又有著細微的差別:Scannell 和 Gillord(2010)提出地方依戀的三維框架概念,第一個維度指的是作為行動者的人,其影響因素分別位于群體層面和個體層面,如文化、歷史,個體經歷等。第二個維度是心理過程,影響因素包括情感,認知和行為三大方面。第三個維度是依戀的對象,影響因素包括地方特征等。Stokols 和 Schumaker (1981)描述了地方依賴的兩個維度,第一個方面指地方具有滿足人們行為需要的資源,第二個方面指的是一個地方與其他地方在生活質量和環境方面相比較的結果。探究地方依賴的發生機制, Moore 和 Graefe(1994)提出了以下觀點, 認為人們之所以會對某些環境產生依賴性, 是因為這些地方具有獨特的能力來滿足人們需要的經歷。
二、研究區域概況
獨克宗古城是中國保存的最好、最大的藏民居群,而且是茶馬古道的樞紐。中甸即建塘,相傳與四川的理塘、巴塘一起,同為藏王三個兒子的封地。歷史上,中甸一直是云南藏區政治、軍事、經濟、文化重地。千百年來,這里是雪域藏鄉和滇域民族文化交流的窗口,漢藏友誼的橋梁,也是滇藏川“大三角”的紐帶。中甸從20世紀末期開始發展旅游業,良好的自然、人文資源使香格里拉在世界范圍內一躍成名,成為云南旅游的重要旅游目的地。
直到2014 年1 月11 日,獨克宗古城發生火災,燒毀242 棟房屋,過火面積占古城核心保護區面積的17.81%,導致古城歷史風貌嚴重破壞,部分文物建筑不同程度受損。
三、當地“邊緣人”的地方依戀
旅游業屬于第三產業,這意味著發展旅游業不需要高強度的體力勞動和知識水平要求,這一情況導致了當地的“邊緣人”多為中老年人,而富有體力和知識水平年輕人多選擇外出學習、工作。這就造成了民族村寨旅游中村寨的“空巢化”,即本地“邊緣人”多為中老年人,年輕人多選擇外出務工。如在對獨克宗古城的調研中就可以發現,當地的旅游經營者多是中老年人群。這一群體的地方感不同于外來經營者:首先,他們世世代代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對土地有著深深的依戀。他們是地方文化、歷史、宗教的參與者,對于第一維度的地方依戀是外來經營者無法擁有的;其次,獨克宗古城對于他們來說不僅僅只是一個旅游古鎮,更是他們的家,這里有他們的社會關系網絡、賴以生存的土地以及他們日日夜夜居住的家屋,可以說獨克宗古城是他們溫馨、穩定的記憶儲藏室;除此之外,古鎮中還充滿著寺廟、經幡等宗教物質載體,這些載體使他們的精神有所寄托,加深了對地方的依戀。
但是,在民族村寨商業化后,當地“邊緣人”的地方依戀也會隨著變化。[1]麥坎內爾(MacCannell,1984,p388)指出:“當一個民族開始出售自己……作為一種民族吸引力,這個民族就不會自然地發展。其民族成員開始把自己視為一種真正的生活方式的活代表。”在獨克宗古城的民族村寨旅游開始發展之后,當地經營者逐漸發現只要把傳統的生活方式呈現在游客面前就可以輕松盈利,結果所有當地經營者的盈利模式多轉變為了出售自己唯一的產品——祖先的生活方式。而呈現在游客面前的本應多姿多彩的民族都淪為就成一種“模型文化”,在獨克宗古城,無論走到哪里都可以看到“獨特”的藏式民居、藏式客棧、藏式餐館,多數建筑風貌趨于相似。也正因如此,當地的文化不再呈現一種自然發展的狀態,而是停滯在現今的發展階段,或是被外來文化反噬。原有的單純的地方文化認同摻雜了經濟利益之后成為了當地“邊緣人”的謀生工具,如家庭客棧對于自家的裝飾不再只是憑借著傳統的審美和自己的喜好,更要考慮游客體驗的需求。
另一方面,在獨克宗古城發展旅游的過程中,因發展需要,古城的建筑格局和公共空間格局也隨之變化。原來的空地如今已建成客棧或酒吧;原來的鄰居如今把房屋出租給外地人開店;原來的老建筑內部裝飾已充斥著現在元素等現象屢見不鮮。但空間格局的變化意味著人際網絡的變化,原有的單純鄰里關系,如今變成了傳統的鄰里關系逐漸被商業鄰里關系所取代,本地居民之間的交往比以前減少,而陌生人也在不斷增多。外來經營者多選擇與自己情況相似的經營者交往,很少把本地人列為交往的對象,以商業街道為單位的“新鄰居關系”正在形成。社會關系網絡的變化使得也使得當地人對地方情感認同發生弱化。
四、外來“邊緣人”的地方依賴
在2014年獨克宗古城遭遇火災后,重建過程中,相比起當地居民,再這樣的突發情況下,在各大媒體的報道中似乎外來經營者對重建家園表現得更加積極。他們的表現讓觀眾造成一種外來經營者對獨克宗古城的地方感更加強烈的映像,但追其根底,外來“邊緣人”的地方感有別于本地居民,更偏向地方依賴。如今選擇到古鎮開客棧、咖啡館、精品店的群體多為有一定經濟、文化基礎的年輕人。但為什么會有源源不斷的年輕人選擇到民族村寨創業、安家,筆者在訪問一位在古鎮開客棧的外地青年的過程中得到了答案,她的看法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她認為年輕人會不遠千里來到一個陌生的古鎮生活的原因如下:首先,到古鎮經營旅游業的年輕人多數都在大城市都擁有一份較體面的工作,文化水平較高,并有一定的積蓄,才會有經濟基礎和經營思路到古鎮開客棧;其次,這些年輕人雖然在城市有自己的社會交際圈,但現代都市的高速運轉和對經濟利益的追逐讓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不斷變大,不如到古鎮和志同道合的年輕人或淳樸的當地人交往,以尋求一份安寧、平和的生活;最后,到古鎮經營的年輕人還有一個特點,他們多遠離家鄉在外工作,他們已適應了與父母、家庭相隔千里的生活,正是這樣的情況讓這些年輕人既可以四海為家,也可以無處是家。
所以,這些外來“邊緣人”的地方感就可以解讀為一種地方依賴:一方面獨克宗古城的旅游業發展給與他們最基本的生計保障;另一方面,獨克宗古城也是這些年輕人精神上的避風港,與他們之前所處的大城市有著巨大的反差,古城的獨特環境能夠滿足這些年輕人逃避壓力、尋求安寧的愿望。
五、“邊緣人”之間的影響
外來“邊緣人”和本地“邊緣人”之間存在著相互影響作用,但外來的文化對本地文化的沖擊終究是遠遠大過本地文化對外來文化的影響,可以說這是一種在小范圍內形成的“文化霸權”。追溯歷史,在近代史中,由于長時間的閉關鎖國,使得外來文化相較于我國的本地文化更具有吸引力。同理,城鎮文化對民族村寨也具有較大的吸引力。而這些外來的“邊緣人”就成為了當地“邊緣人”的效仿對象,也正是外來者的示范讓當地人明白需要怎樣布置、裝飾自己的經營場所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所以他們在“祖先的生活方式”中加入了現代審美的因素,過上更加便捷、高效的現代城鎮生活。從此,民族文化失去它自由發展、興衰的環境而停滯不前或慢慢淡出人們的視野。其實,民族村寨旅游的發展過程也是當地居民實現城鎮化的過程。
另一方面,外來“邊緣人”實際上存在著相對當地居民較強的流動性,社會流動的增強,不斷降低居民地方感。一方面,外來經營者并不扎根于古鎮這片土地,并有著較高的知識水平和勞動技能,可以隨時離開古鎮并過上較好的生活;另一方面,民族村寨所能提供的生活水平和教育水平遠低于城市,外來經營者為家庭和子女的生活和教育問題考慮,多會選擇重新回到城市生活或讓子女回到城市生活。外來經營者流動性強這一情況使當地居民在村寨中的左領右舍都不再是熟悉的朋友,而是流動性較強甚至語言不通的外來經營者。這讓當地居民對民族村寨的情感認同有所降低。
六、總結及建議
民族村寨中本地的旅游邊緣人與外來的旅游邊緣人的地方感知是不盡相同的,當地邊緣人的地方感知更容易受到土地、宗教、人際關系及房屋(家)等因素的影響,從而形成地方依戀。而外來邊緣人的地方感知更容易受到生活方式和生計模式等方面因素的影響。但由于外來文化的強勢,對當地容易形成“文化霸權”,從而使當地文化處于非自然發展或停滯狀態。所以從民族村寨旅游發展的地方認同角度,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1)保護當地居民的老房屋(家)、宗教實體及城鎮布局,使當地居民對地方的依戀感和滿意度長期保持在較高水平。
(2)在民族村寨旅游開發中需注意適度開發,必要時可限制進入村寨人數,一方面提高了游客體驗度,另一方面使村寨的文化處于一個較為自然的環境中發展。
(3)注重社區參與和社區受益,適當控制外來旅游經營者的進入。讓本地居民能夠參與到旅游發展的規劃、策劃、經營、管理等活動中,保留當地文化的原真性。
(4)樹立當地居民的民族文化自信。可通過一定的政策、補貼鼓勵當地居民傳承民族文化、民族語言,重視民族文化的生存與發展,減少外來文化對本地文化的沖擊。
參考文獻:
[1]瓦倫·L史密斯. 東道主與游客——旅游人類學研究[M]. 昆明:云南大學出版社, 2002.
[2]姜遼,蘇勤. 周莊古鎮創造性破壞與地方身份轉化[J]. 地理學報,2013,08:1131-1142.
[3]莊春萍,張建新. 地方認同:環境心理學視角下的分析[J]. 心理科學進展,2011,09:1387-1396.
[4]郭文軒. 防止過度商業開發 加強文物消防管理——對獨克宗古城、報京侗寨火災的幾點思考[J]. 中國民族,2014,03:54-57.
作者簡介:趙俊嫻(1993—),女,白族,籍貫:云南昆明,單位:西南民族大學旅游與歷史文化學院,研究方向:旅游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