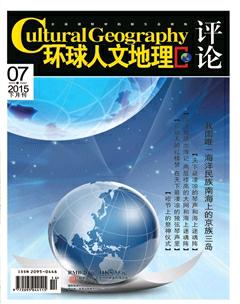淺談俄裔猶太人遷移哈爾濱的原因
摘要:猶太民族是一個歷經坎坷的古老的民族。基于宗教等原因,他們一直以來飽受排斥和迫害,遷徙也往往成為了猶太人迫于無奈的選擇。19世紀末大量的俄國猶太人隨著中東鐵路的修建來到我國的哈爾濱,并在此定居。而由此形成的哈爾濱猶太社區是世界猶太社區的重要組成部分。哈爾濱以其博大的胸懷接納了這些來自異國他鄉的猶太人,而猶太人的到來也為哈爾濱的城市現代化進程以及多元文化的形成做出了重要貢獻。
關鍵字:俄裔猶太人 遷徙 中東鐵路 哈爾濱
猶太人早在公元前幾個世紀就已經到俄國定居。這些猶太人散落到城市里組成了猶太社團。到了十五世紀以后由于宗教等原因,尤其在猶太教信徒派出現以后,沙皇政府對其不能容忍,猶太人在俄國的各種活動開始受到限制,境遇也每況愈下。而到了十九世紀末,沙皇政府對猶太人的態度,各項排猶政策以及國內反猶浪潮的出現更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隨著俄國勢力在遠東地區的擴張,大量的俄國猶太人以中東鐵路的修建為契機掀起了移居哈爾濱的熱潮,譜寫了兩個民族關系史的新篇章。本文旨在梳理這一時期俄國猶太人移居哈爾濱的原因,探討兩個民族交往的過程及其意義,以期中以兩國的關系在這個嶄新的時代能夠有進一步的發展。
一,俄國反猶排猶浪潮與猶太人的遷移。
俄國反猶的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宗教問題。東正教作為穩定沙皇政權的基礎不僅是全俄第一大宗教,甚至在東歐也有著相當的影響力。別林斯基就曾說過:“這個民族(俄羅斯)堅定地支持上帝的教會,祖先的信念,毫不動搖地盡忠于正教的沙皇。” 所以沙皇要不遺余力的維護東正教,要保證東正教在全國的影響力。于是作為異教信仰的猶太人自然成了沙皇的眼中釘。他們被強迫改宗,但固有的民族凝聚力使他們對自己的宗教有一種堅定不移的信仰。在多數猶太人看來,宗教信仰勝過他們的生命。另外,作為客居他國的民族,猶太人一直受到本地居民的歧視和政府的迫害。猶太人在柵欄區聚居,與主流民族相對隔絕。這也使他們的民族性得以保留。正是這種難以同化的民族性使猶太人是沙俄政府的同化政策難以對猶太人起作用。正如查姆 波曼特所言:“無論一個猶太人離開他的國度,他的民族,他的信仰有多遠。只要有人在清晨敲一下他的房門,哪怕只是為了猶太人的地獄,他也會即刻復原成一個猶太人。 這種難以同化的民族性使沙皇失去了耐心而最終選擇了打壓。
17至18世紀沙俄境內的猶太人不斷遭到壓制,迫害,甚至屠殺,大多數猶太人流離失所,19世紀更是到了一個巔峰。而這一時期一位典型的反猶沙皇就是尼古拉一世。作為虔誠的東正教徒,尼古拉一世對猶太人以一種天生的反感。在他統治期間,猶太人從他們長期居住的村莊中被驅逐,意第緒語和希伯來語書籍受到嚴格的檢查,猶太學校遭到干涉,猶太人的狀況日益惡化。到了亞歷山大二世,情況有所好轉。但在其統治后期,反猶政策有所加劇,甚至還出現了屠殺猶太人的現象。1981年3月1日亞歷山大二世被刺,在沙皇被刺的幾周時間里,俄國境內的猶太社區不斷受到有組織,有預謀的迫害。而新任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從即位之初就宣布:“你要知道,我必須承認,當猶太人受到虐打時,我是感到快樂的”。 由此可以看出這位新沙皇對待猶太人的態度。1882年至1887年亞歷山大三世出臺了一些列的政策。這些政策使大多數猶太人的處境變得無比糟糕,生活難以想象。雖然亞歷山大三世不如尼古拉一世那么無情,但是對于俄國猶太人而言。穩定與平等都是渴望不可及的,俄國的政策使猶太人陷于貧困,有40%的猶太人靠救濟度日。19世紀90年代,執政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為了削弱日俄戰爭給俄國帶來的不利影響,直接把矛頭轉向猶太人。1903—1908年,俄國的很多城市都發生了屠猶事件,猶太人又陷入了深淵。很多猶太人因為無法忍受,開始族群的向外遷徙,大部分人去了美國、加拿大,一部分人沿中東鐵路到達哈爾濱。
二,中東鐵路的修建與猶太人的遷移
19世紀俄國將眼光投到了遠東地區,意欲建立遠東地區的霸權。而中東鐵路的修建對沙俄的遠東政策就顯得尤為重要。一方面它將以最短的距離連接俄國的東西部,以緩解經濟矛盾和社會發展的不平衡,以此來加強沙皇政府對西伯利亞的控制。另一方面,中東鐵路可以幫助俄國打開通往太平洋的大門,提高俄國在中國東北地區的影響力。從中國方面來說,甲午戰爭的失敗,迫使清廷向沙俄靠攏。1896年李鴻章與沙俄財政大臣維特簽定了《中俄密約》,獲得了中東鐵路的筑路權,后又簽訂了一系列附加條款。 這些條款使哈爾濱許多地方覆蓋在俄國勢力之下,為猶太人的遷入創造了客觀條件。
《中俄密約》簽署后,俄國的阿穆爾省總督柯羅杰科夫認為善于經營的猶太人對中東鐵路的修筑有特殊的意義,于是多次向沙皇建議開放猶太禁區(滿洲里)。隨著禁區的開放,第一批猶太人得以從俄國來到中國東北。這批猶太人從遠東的幾個主要大城市如符拉迪沃斯托克、布拉戈維申斯克、哈巴羅夫斯克來到哈爾濱。 在首批到哈的猶太人中,有相當一部分是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大商人,他們享有許多優惠政策,哈爾濱的俄僑私人企業可以不受中國和俄國稅收管理,他們可以不繳稅并在不同程度上享有免稅特權。這些商人是構成哈爾濱猶太社區形成的關鍵因素。1898年隨著中東鐵路局從海參崴遷到了哈爾濱,一些猶太技術人員、工程師 筑路工人、服務人員以及他們的家屬也紛紛來到哈爾濱。這些人的到來不僅為初步形成的社區增添了新鮮的元素和活力,也為猶太商人提供了潛在的消費市場。1903年中東鐵路竣工,沙皇決定向路區派駐有大量猶太士兵參與的護路軍。大量的護路軍及其家屬來到路區并且還形成了士兵村。這些士兵村沿中東鐵路一線分布,大部分猶太士兵退役后就直接留在了哈爾濱。所以在日俄戰爭結束后哈爾濱的俄裔猶太人就已經達到3000多人。
在中東鐵路修建以及運營了的近半個世紀里,有大量的猶太人參與了中東鐵路的建設,這些人構成了早期的哈爾濱俄裔猶太社區,雖然他們的身份不同,職業不同。但是他們為哈爾濱的發展做出了相當的貢獻。也使從前的小漁村哈爾濱初具大城市的規模。
三 哈爾濱的文化包容性
哈爾濱作為一個有著多元文化的城市以其獨特的魅力和城市特點為猶太人的到來敞開了懷抱。首先哈爾濱在地理位置上靠近俄國,動蕩的地區形勢再加上 便利的交通吸引著大量的外國僑民。其中最多的應該就是俄國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領導人瞿秋白曾回憶到:“哈爾濱道里及秦家崗兩部分,完全是俄化的,街道都有俄國名字,中國人只叫第幾條街而已,俄國人在這里就像在自己的家一樣”。
隨著外來人口的涌入,大量的領事館,外國人社區,以及外國僑民會也在這里設立,1907年美國,俄國,日本和法國就率先在這里設立了領事館,而隨后德國,西班牙,丹麥,瑞典等北歐國家也相繼在這里設立了領事館。總計達到21處。領事館的設立使大量的僑民在哈爾濱地區受到了來自本國勢力的保護,同時也為大量的外僑移民哈爾濱大開方便之門。
而包容性的另一個特點就是對異域文化尤其是異國宗教包容性,作為一個新興的城市,這里不僅中國傳統的佛教,道教等宗教場所,而且還有天主教,東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等宗教場所。所以,在當時的哈爾濱可謂是寺院道觀煙霧繚繞,教堂鐘聲此起彼伏。由于在哈爾濱生活的外僑人口較多,而且民族又較為復雜,所以這些外僑的信仰的教派也較多,教堂隨之也多了起來。尤其是東正教教堂,遍布哈爾濱數量之多是其他城市罕見的。除東正教堂外,其他宗教機構的設立無論從規模還是數量上雖然無法跟東正教比但是正是由于它們的存在才顯出哈爾濱的宗教繁榮之城,才彰顯出哈爾濱的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優越的地理位置,四通八達的交通,豐富的物產資源,這些都是吸引猶太人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還是其宗教包容性。猶太民族是一個宗教民族,可以說猶太教是他們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沒有了猶太教也就沒有了猶太民族。而哈爾濱對猶太教從不排斥,基于這種情況,哈爾濱理所當然的成為了猶太教存在和發展的樂土,也是猶太人生存和生活的樂土。
結論
中猶兩個民族有著悠久的歷史又飽經滄桑的民族,長期以來猶太民族過著流散的生活,寄居他國,受盡凌辱和歧視。早期兩個民族的交往可以追溯到宋代,當時大量的猶太人來到帝都開封,開啟了兩個民族交往的先河。到了近現代以來,尤其是19世紀末20世紀初期,哈爾濱在連接兩個民族的經濟與文化交流的過程中承擔了重要的角色。
構成這種聯系的動因我覺得在很大程度上是較為被動的,猶太人的身份,文化,宗教信仰,以及歐洲傳統的反猶心理注定他們無法像其他公民一樣穩定的生活。不斷地排猶政策和層出不窮的暴力反猶浪潮是造成他們離開的根本動因。中東鐵路的修建以及俄國對中國東北勢力的延伸開啟了猶太人移居哈爾濱的道路。而哈爾濱本身的文化的多元性和包容性也是哈爾濱俄裔猶太社區形成的關鍵因素。
作者簡介:矯淙旭(1990—),男,漢族,河南許昌人,在讀研究生,河南大學歷史文化學院,研究方向:猶太—中東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