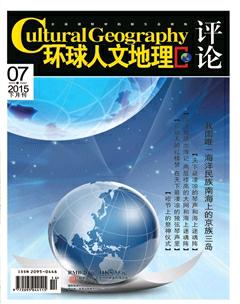探究民族主義對國家安全的影響
[摘要]: 民族主義與有軍國主義、對外擴張等復雜歷史經歷的日本相互結合,形成了以日本文明為核心的日本民族主義,其在近年來以安倍晉三等右翼勢力的上臺執政而不斷通過修憲、領土爭端、防務松綁等政治對外事件而產生擴散性效益。國家安全領域及其相應決策為對內、外政治的外延,日本政治的右翼傾向必然推動日本自身國家安全及其戰略的轉型、異化,形成了亞太地區的不穩定因素;民族主義經日本政治環境的特殊塑造,正以較極端的方式對自身及周邊國家的安全態勢產生重要影響。
[關鍵詞]:民族主義 國家安全 右翼傾向 影響
一. 民族主義在日本的發展歷程
日本經歷了一戰、二戰的勝利、失敗,戰后被“管理”、占領、改革、連續經濟繁榮與蕭條的跌宕起伏過程,一直以自身特殊環境、文明、思想、政治模式等領域的充分結合繼承至今,并自上個世紀90年代凸顯為以“京都學派”的“日本文化論” ,迸發出日本民眾的自信力、傲慢感、優越感。部分日本學者甚至將日本稱為保守主義、大國主義的完美結合品,“應當被當作另一個歐洲來看待”2,其受部分封建思想、右翼及軍國主義遺留思潮及所謂“自由主義”歷史觀影響,逐漸形成了具有較強變異性、扭曲度的“新民族主義”,不僅成立了多個右翼政治組織,同時影響并鼓動政府實施對外擴張、恢復軍事大國及歷史教科書修改等右傾公共決策,引起了亞洲乃至世界范圍內多國的質疑與不滿。
二. 日本新民族主義與右翼傾向現狀闡述
自2012年安倍晉三再度當選日本首相以來,日本便打著“國家主義”、“民族主義”、“恢復正常國家”的旗號,多次圖企侵犯周邊國家領海、領空主權,并通過修改憲法、對外派駐軍隊、建造隱蔽進攻性軍艦、戰機為行動表象,嘗試改變二戰后維持世界秩序的雅爾塔體系,并謀求成為集經濟、軍事、政治為一體的大國。其中,日本將一貫繼承的民族主義思潮,結合安倍晉三為首的右翼日本政客勢力、民族心理變異等元素,迅速地在政壇將反對者打壓、弱化,并力圖推進其憲法修改,將同中、韓等國的外交關系通過爭議領土矛盾尖銳化而擺脫聯合國及二戰后秩序對其的束縛。有學者認為,日本新興的民族主義為其右翼傾向的本質基礎,其誕生原因主要來自于遠東審判的公正缺陷、對戰爭反思不力、恥感文化教育和變異性自尊心的結合3;單一的民族、集群的團結意識加上對所謂“惡”的非惡性認識,造就了日本的右翼主義為形式,民族主義為根源性動力的內容。
三.日本民族主義對國家安全的影響力分析
1.形成對日本民族整體性“歷史失憶”局勢,極端性思維結合集團、恥感思想,形成對社會民族主義的擴散性、深度性滲透,使其激發對侵略、軍國主義的訴求,忽略其軍事化、極端化與法西斯化所帶來的地區性、世界性災難與嚴重社會后果。日本在20世紀30年代東方會議后,全國上下在法西斯少壯派的鼓吹、宣傳及洗腦性行動下,全面開動其工業化、現代化、軍事化國家機器,并以民族主義、自豪感為主觀精神動力,促進日本全民族對軍國主義和法西斯侵略的支持,以至于在將日本拖入戰爭泥潭與深淵的戰爭面前,日本集體產生了一種至高無上的“惡”的榮耀感,從極度瘋狂的軍事進攻中找到屬于自身的民族自信力與認同感;即便是經歷了戰敗、二戰后改革、民主化以及相應的經濟崛起,深藏于日本民族內心中對安全的渴求與民族主義對安全的沖擊力,形成了日本社會、民眾、個體的高度矛盾感,并將自身的信仰與行為依賴于他人反應,以強者為榮,即使存在錯誤也極力否認,否則便是恥辱;刻意對歷史的掩蓋與選擇性以往,必然為相應的右翼與軍國主義擴散提供了時空機遇。
2.右翼擴散與軍國主義的復活,使民族主義呈現多元化形態,在多維度上逐步滲透并弱化社會、公共部門及國家安全部門的理性、科學的戰略決策,使其成為了缺乏對未來的預見性、思考力、全面性的短期性、狹隘性戰略與頂層設計,促使民族主義膨脹,并間接引發國家經濟、軍事、政治、外交安全等的非穩態場力的綜合性作用。日本意圖控制亞太,建立對外軍國的野心與現實的交錯性部分扭曲了民眾心理,并使之泛化、傳達至高層,結合其政壇內部家族與派系勢力的殘留性與頑固性,使日本民族主義逐步在頂層規劃時演變為以右翼為主導的政治派別;在民眾群體內則潛伏著民族主義經民主化改革后政府與決策機構的特殊結構,它以著眼短期性效益為主,使領導者因利益的沖突、矛盾與協商而更迭頻繁,增加了民族主義同媒體平臺結合下輿論對公共政策、國家安全戰略的把控與推行的份額,逐步使日本的社會各階層團體、以至上層廣泛性介入民族主義,與之互動,形成對外戰略、軍事防務與政治輸出的進攻性、極端性狀態。
3.民族主義為核心的日本思潮、安全決策,使日本將自身防務、國家安全需求置于被周邊鄰國、世界性大國的共同性質疑、否定與反對狀態中,形成了對日本國家安全戰略的進一步“包圍”與“隔離”狀態,使日本面臨來自包括和平崛起的中國在內的多國的反向戰略壓力與威懾,造成其對外軍事、防務野心擴張的反彈效應,使日本與自身的合理訴求背道而馳。無論是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還是美化侵略,高調“紀念戰爭”,日本在憲法修改、研制服役進攻性艦船戰機、推行正常國家戰略、謀求聯合國安理會席位等對外政治大動作中,均被解讀為復活軍國主義與對外侵略的再開始;因日本民族主義及其存在的泛化、深度化環境,使日本自上而下對侵略歷史反思存在非誠懇與非嚴謹性,且始終保持其對外侵略與擴張的非穩定性心理與國家因素,必然使得受其侵害與經受其威脅的國家對其無法放松戒備,特別是在相對敏感的防務、軍事領域,日本依舊保持高新裝備的研發產業與技術、人力儲備,對中、韓、朝等受其侵略之害的亞洲國家始終為實質性威脅,故使得原本可正常化的中日關系因釣魚島、東海爭端等矛盾而逐步冷卻。
參考文獻:
[1]嚴岳. 裂變的太陽旗——日本政客的行為與校正. 世界軍事,2014,(3):4—9.
[2]宋汝余. 變異的日本新民族主義[J]. 世界軍事,2014,(5):16—19.
[3]林東. 安倍們何以如此癲狂[J]. 世界軍事,2014,(23):10—14.
[4]王鼎杰. 帷幕后的日本國家戰略[J]. 世界軍事,2013,(3):10—14.
作者簡介:
李江(1990—),男,江蘇省南京人,現就讀于南京理工大學公共事務學院行政管理專業,碩士研究生一年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