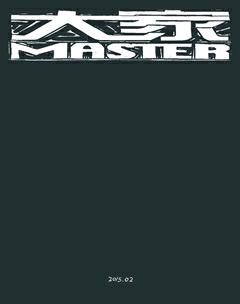張雷小說,一種人間的奇跡
雷杰龍
張雷走了。從2009年初夏,他的小說被詩人雷平陽發現,在當年《滇池》雜志第5期驚艷亮相,至2015年1月28日在47歲上因病盛年西去,張雷在“文壇”上“活動”的時間,滿打滿算,不到6年。6年里,他的小說,也只在云南的幾家刊物《滇池》《大家》《邊疆文學》上出現,在所謂更大的江湖上,并沒弄出什么像樣的聲響。作為一位小說家,張雷生前寂寞,身后也似乎注定寂寞。而這,并不影響一些人,即使只是很少一些人對他深切懷念,即使其中許多人,除了他的小說,與他素不相識。如我的一位寫小說的朋友,就在微信中說,她可以不讀許多大師的小說,但如果見到張雷的小說,她一定讀,并且要讀五遍才會罷休,即使無緣謀面,但她依舊堅信,張雷是一位有宿慧的小說高人。
張雷到底是不是小說高人?我無權斷定。或許,這樣的問題要留給未來書寫的文學史。而真正的文學史,是殘酷淘汰的時間法則,對張雷這樣沒弄出什么聲響的小說家,大約也會不屑一顧。再或許,對張雷這樣的人,討論他的小說能否進入文學史,本身就是一種羞辱。因為他的人生遭際,他早知命不久長。他把生命余下的時間,大半獻給小說。小說對他來說,不僅是一種唯一能夠消遣時光的游戲,而且他還想在這樣的游戲中盡力探索他自己生命的真相,尤其是,他的靈魂的真相。而他的靈魂,是內向的,幾乎和時代無關。而一切的文學史,卻又大多是時代的文學史。因此,談論他的小說和任何文學史的關系,骨子里是一個庸俗的話題。而張雷的靈魂,尤其是飄蕩在他的小說里的靈魂,絕無庸俗之氣。他小說里的靈魂,只有孤獨之氣,一種純凈、優雅、玄妙、熱烈而寂靜悲愴的孤獨之氣。
借助小說的虛構性特質,張雷在他的小說里找到了許多他自己的靈魂的替身,這些替身或者生活在古代的咸陽、汴京、長安,以及青藏高原的雪山之巔,或者生活在現代的某個小城、某個鄉村,但他們無一例外都在進行命運的猜謎和冒險,或者得到救贖,或者永無解脫。他用替身、用靈魂在敘事,在進行小說的煉金術游戲。他在這種孤獨而決絕的游戲中洗凈了肉身的悲苦和俗氣,而他的靈魂,則在這種游戲中一次次練習巧妙、空靈、優雅而唯美的飛升。誰也不知道,他練習好了沒有,在他真實離去的輪回游戲中,他的靈魂飛升了沒有。但他的練習本身——他練習留下的副產品,或者說遺蛻物——那些他留在人間世的小說,卻讓我們這些熱愛小說的人,再次獲得了熱愛小說的理由。因為他的出色練習,讓我們再次感受到小說藝術即使不能奢談什么救贖,但它依舊是一種人間的奇妙之物,一種可資證明靈魂存在的奇跡!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