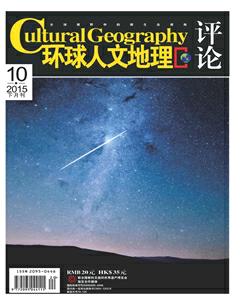先秦時期晉南歷史地理沿革初探
摘要:山西境內,自龍山時代起,大致以霍山為界將其劃分為中原系統古文化與北方古文化。翼城大河口在臨汾市東南,位于晉南,古屬中原地區,是中原文化區的一部分。得天獨厚的地理環境,造就了此地繁榮的社會文明,這里是中華文明的重要發祥地,是中原農耕文明和北方草原文明交匯融合的天然通道和軍事重地,在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史上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
關鍵詞:晉南;大河口:青銅器;文化區
2014年7月29日,由首都博物館、山西博物院、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共同主辦的“呦呦鹿鳴——燕國公主眼里的霸國”展在北京首都博物館舉行。精美的青銅器,無論鑄造工藝還是數量、種類都具有極高的研究價值,并對探索西周時期晉南地區的諸侯國提供了新的資料。值得注意的是,大河口墓地出土的星銅器與宗周、成周地區王都器物具有很大的一致性。以下我們以霸國的歷史淵源為引,從青銅器角度略作討論,其中難免有所紕漏,還望方家指正。
大河口墓地,古屬故翼城,位于翼城縣東南十五里。翼城縣,古屬平陽府,禹貢冀州地,即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府東連上黨,西略黃河,南通汴、洛,北阻晉陽,宰孔所云:“景霍以為城,汾、河、涑、澮以為淵”,而子犯所謂“表裹河山”者也。此地河流密布,環境優越,土壤肥沃,交通便利,多面環山,易守難攻,自古以來多為兵家必爭之地。戰國時魏有其地,秦商鞅言于孝公曰:“秦之與魏,譬若人有腹心之疾,非魏并秦,秦即并魏。何者?魏居嶺阨之西,都安邑,而獨善山東之利。利則西侵秦,病則東收地。魏必東徙,然后秦據河山之固,東郷以制諸侯矣。”后有杜畿云:“平陽披山帶河,天下要地。”是也。
自新石器時代以來,晉南地區出現了大片的考古學文化遺存,代表了不同時期文化發展類型。以汾河為源,大量的文化遺存集于此地,先后有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以及作為“先夏文化”的陶寺類型。晉南地區的史前文化,與中原其它地區一樣,是中華文明的重要源頭之一,與上個世紀九十年代蘇秉琦先生提出的“滿天星斗說”相互印證。
二里頭時期,夏縣的東下馮類型作為二里頭文化的重要類型,出土了大量的遺物,成為研究夏文化的對象。從考古學文化因素分析,東下馮類型雖與二里頭類型同為二里頭文化,但兩者之間卻存在差異。陶器中以鬲、甗多而鼎少,未見觚、鬹等較具特色;窯洞式的房屋和墓葬也區別于其他類型。此外,東下馮壕址出土有銅鏃、刀、鑿和銅容器的殘塊、銅渣以及石范等,證明東下馮類型不僅使用銅器,而且具有自己的青銅冶鑄工業。
早商時期,商王朝統治中心在豫西的鄭洛一帶,豫西與晉南隔黃河毗鄰,交通往來并非難事。從考古發現看,當時已有多處渡口:洹曲古城、平陸前莊以及茅津渡等,尤其以在前莊遺址以西40公里處茅津渡最為重要,一直是晉豫交通的重要渡口。多處渡口的發現表明,至少在早商時期,晉南地區與商王朝之間已有密切的文化交流。從文化因素分析,晉南地區的文化因素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商文化的統治中心。陶器中,大口尊、小口甕、平口甕等器物雖為當地而有,但均經過改造,其變化規律同于二里崗類型者,并且東下馮類型已經以商文化的典型器物—商式鬲為主要炊器;銅器上,這一時期,晉南地區的青銅器目前僅發現于垣曲南關、平陸前莊,兩地青銅器墓在銅器形制上與組合形式上與同時期的鄭州地區的商墓近同,表明商前期晉南地區與當時商中心政治區域的密切聯系。當然,中商時期,商文化的二里岡類型與東下馮類型并不能完全的對等,東下馮類型中未見傳統早商文化墓葬中所見的腰坑。但總的來說,這一時期晉南地區的青銅文化開始受到商王朝的影響。
中商時期,二里岡類型演變為白家莊類型,并成為中商一期遺址最豐富的一處,或仍為商文化的核心文化。從中商二期開始,由琉璃閣類型演變而來的曹演莊類型一度成為商文化的核心,并一直延續到中商三期,因此豫北、冀南便成為當時重要文化中心。商王朝統治中心的轉移,使得新的通道被開辟出來,兩地雖有太行山阻隔,但有漳河河谷相連,使得兩地往來頻繁,今河北武安南是太行八陘之一滏口陘,便是當時主要的交通孔道。伴隨交流通道的轉移,兩地之間文化交流的區域也會相應的發生變化,在考古學上的表現便是考古遺址的分布狀況。這一時期晉西南考古發現較少,但在晉東南長治、屯留,長子、潞城一帶以及晉中汾陽地區,卻有著較豐富的中商文化遺存,考古學上成為小神類型。
從文化因素分析,小神類型既有東下馮類型的特點也有曹演莊類型的特點,應是兩者結合的產物。小神遺址除了商鬲和陶豆,與商王朝同類器物接近。但也具有自身特點,鬲體的最寬處大都在腹部的中間,三足內收,足跟不明顯。豆表現出復雜形制。其中一種喇叭形假腹豆似不見其他類型。
文物尤其是大批銅器在晉東南的集中出土,反映了當時這一地區在商王朝歷史中的重要地位。出青銅器的地域主要有三塊:其一在晉東南,今長子、屯留、武鄉一帶,該地隔太行與安陽相望,應是商人勢力首先到達之地,其地處于濁漳、清漳二水流域,二水向東匯成漳河流經安陽北。二是山西西部中段,呂梁山脈以西,黃河東岸的保德、石樓、永和、吉縣一線;與這些地區出土青銅器風格相同,可歸屬同一類型的遺址已跨過黃河,分布在今陜西東北地區。三是太原南北的晉中盆地汾水流域之靈石、洪洞一帶,以及太原北的忻縣,夾在一、二兩個區域之間,因而在青銅文化上成為兩種青銅文化交會的中介區域。
根據對殷墟卜辭所反映的商后期政治地理的研究可知,當時商人勢力已西越太行到達晉東南、晉南,在這些地區可能有商人所建之重要城邑。
自殷商以來,這里就是古農業發達區,根據甲骨文記載,商人在晉南地區分布了四個農業帶:
運城盆地——甫(合集9779)、郇(合集9774)、臿(合集9791)、冓(合集9774);
晉中南古沁水流域——轡(合集9776)、纟羊 方(合集6)、口(合集9774) ;
晉東南古漳河流域——亙(合集6943)、長(合集9791)、示(合集9816);
晉西南臨汾盆地——唐錄(合集8015)、缶(合集1027)、呂(合集811)、口(合集583)、蓐(合集583)
晉南地區作為古農業區,應經成為商王朝的糧倉,一直以來受到商王朝的重視。
此外,卜辭資料也反映出在晉地多有頻頻與商人兵戎相見的所謂方國勢力在活動,這也必然會造成與殷墟青銅文化的接觸和交融。這種歷史背景正是晉地多商器的原因。
晚商時期,商王朝的統治中心經盤庚遷殷,轉移到今河南安陽地區。殷商時期是整個商文化的高峰期,以殷墟為中心,燦爛的青銅文化對周邊文化產生了極大地影響,有的地區的文化甚至被同化直至消失。小神文化在這一時期不見,應是被同化的結果,而且晉南地區也再未出現其它地方文化類型。鑒于商文化的繁盛,晉南的商文化遺存有較多分布,主要有靈石旌介村、浮山橋北、臨汾龐杜和屯留上村、潞城。從今天的考古發現來看,已發現的晉南商文化遺存,其文化因素與殷墟文化具有高度的一致性。
此外,汾河以西,晉陜之間黃河兩岸的高原地區,以山西石樓、永和、柳林,陜西綏德、清澗、延長等地為中心,集中出土了一批晚商時期的青銅器。這批器物與殷文化、北方草原文化具有密切的關系,應是兩者結合的產物。它的出現證明了至少在商代晚期,北方草原文化與中原文化已有了交流和影響。其交通路線是商都安陽越太行至屯留,向西走到達汾河中游地區,再向北行抵晉陜高原。
晉中盆地出土商代青銅器的最重要地點在晉中市西南的靈石縣旌介村,1976年發現M3后,又于1985年發掘了M1、M2,三座墓共隨葬青銅器六十九件,包括容器十八件,兵器四十六件。從出土器物看,三座墓出土的青銅器年代相近,大致在殷墟三期。值得注意的是,三墓出土的大多數容器上有族氏銘文 ,而 氏與商王族關系密切,所以此三墓代表的青銅文化似仍屬殷墟文化系統,為其一分支,是商后期偏晚商人勢力繼續西進之表征。除此外,1982年洪洞上村村民挖地基時發現一組商代銅器,有鬲一、爵一、戈二。三器基本上應屬二里崗——殷商銅器系統。
綜上所述,至少在早商時期,晉南地區已受其它地區尤其是商王朝統治中心文化的影響。山西地區青銅文化發展應是來源于東部商文化的核心地區,由漳河、滏河西進入晉中地區(商代晚期以靈石旌介村商墓為代表),然一分為二分別向晉南和晉北發展。
參考文獻:
1、「清」顧祖禹:《讀史方輿紀要》,中華書局,2005年3月。
2、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國考古學·夏商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12月。
3、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大河口墓地聯合考古隊:《山西翼城縣大河口西周墓地》,考古,2011年第7期。
4、中國青銅器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青銅器全集》,文物出版社,1997年9月。
5、史念海:《戰國至唐初太行山東經濟地區的發展》,《河山集》,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63年。
6、宋鎮豪主編,孫亞冰、林歡著:《商代史·卷十》《商代地理與方國》,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10年。
作者簡介:
劉樹滿(1988—),男,漢族,山東臨沂人,單位:陜西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專業:考古與青銅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