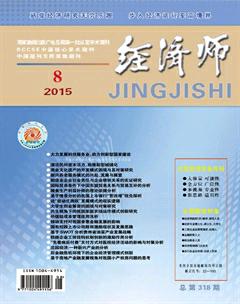論“能動式跳躍”發(fā)展模式的現(xiàn)實(shí)邏輯
摘 要: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出的“全面深化改革”不同于按部就班的“漸進(jìn)性改革”,是一種在總結(jié)過去經(jīng)驗(yàn)教訓(xùn)、理清現(xiàn)實(shí)發(fā)展思路以及對未來科學(xué)自信的前提下實(shí)施的一種“能動式跳躍”。文章梳理了改革開放至今的發(fā)展歷程,在制度的視角下探討了國家在新時期下如何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績效的提升。在此基礎(chǔ)上闡釋了“能動式跳躍”發(fā)展模式的內(nèi)涵、能動式跳躍的支撐以及如何實(shí)現(xiàn)能動式跳躍發(fā)展。
關(guān)鍵詞:國家治理 制度 能動式跳躍 經(jīng)濟(jì)績效
中圖分類號:F015 ?文獻(xiàn)標(biāo)識碼:A
文章編號:1004-4914(2015)08-030-02
一、引言:漸進(jìn)式發(fā)展還是能動式跳躍
自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改革開放至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全面深化改革,中國用了35年時間基本實(shí)現(xiàn)了由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向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的轉(zhuǎn)型。建國后,我國按照前蘇聯(lián)模式進(jìn)行社會主義改造,完成了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后照搬前蘇聯(lián)經(jīng)驗(yàn)搞建設(shè),加強(qiáng)中央集權(quán),大力發(fā)展重工業(yè),搞“一大二公”的公有制,20世紀(jì)70年代末開始探索引進(jìn)國外技術(shù)和設(shè)備。雖然政府層面進(jìn)行了大量探索,但由于公有制觀念的束縛,國家對于民間的各種嘗試歷來都是明令禁止的。直到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實(shí)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后,在生存問題的倒逼下政府才逐步放松了對民間探索的限制。隨著小崗村農(nóng)民創(chuàng)造的“承包制”在城市國有企業(yè)和工商業(yè)中逐步推廣深化,舉國一體的計(jì)劃經(jīng)濟(jì)體制才逐漸開始松動。
對內(nèi)改革的同時,中國也開始嘗試逐步對外開放。但是在20世紀(jì)80年代,對外開放的行業(yè)僅局限于出口行業(yè),中國境內(nèi)外國直接投資總量還非常少。黨的十四大正式提出要搞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后,中國才開始逐步放開國內(nèi)市場,向外資開放。隨著經(jīng)濟(jì)特區(qū)的試點(diǎn)成功,中國逐步擴(kuò)大了試點(diǎn)區(qū)域,嘗試性地對外開放產(chǎn)生的報(bào)酬遞增效應(yīng),使國家開始探索更大范圍、更大規(guī)模的改革開放,并最終放棄了封閉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思路,實(shí)現(xiàn)了與世界經(jīng)濟(jì)的接軌。
十八屆三中全會強(qiáng)調(diào)要適應(yīng)黨和國家發(fā)展的新要求,將全面深化改革提升到戰(zhàn)略高度。提出以改革為主線,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舉措,一般性措施不寫,重復(fù)性措施不寫,純屬發(fā)展性舉措不寫,突出重要領(lǐng)域和關(guān)鍵環(huán)節(jié)。由此可知,當(dāng)下中國政府追求的不再是循序漸進(jìn)式的改善,也不是不切實(shí)際的大躍進(jìn),而是一種必須靠突破和跳躍發(fā)展才能實(shí)現(xiàn)的可以量化兌現(xiàn)的決定性成果。這是一種在理論指導(dǎo)下,通過發(fā)揮改革主體能動性,充分激發(fā)市場活力,從關(guān)鍵問題入手尋求突破的一種國家治理方式,筆者稱之為“能動式跳躍”發(fā)展模式。
二、能動式跳躍發(fā)展模式的內(nèi)涵
本文是在新制度主義的視角下探討中國經(jīng)濟(jì)績效如何實(shí)現(xiàn)跳躍式發(fā)展,而國家經(jīng)濟(jì)績效的改善最終都要落到國家治理的有效性上,因此只有清楚國家治理的含義才能夠正確理解能動式跳躍發(fā)展模式的內(nèi)涵。毋庸置疑,國家治理與國家相伴而生。新制度主義認(rèn)為,離開產(chǎn)權(quán),人們很難對國家做出有效分析。產(chǎn)權(quán)是一種排他性權(quán)利,其界定和實(shí)施必須依賴強(qiáng)制力,國家作為在暴力方面具有比較優(yōu)勢的組織,在產(chǎn)權(quán)界定和實(shí)施方面處于壟斷地位。不妨給定一個理想化的模型:假設(shè)存在一個新成立的國家,復(fù)雜的政府機(jī)構(gòu)和組織尚未設(shè)立,規(guī)章制度也有待健全,百業(yè)待興。原則上,政府可以抓住機(jī)會建立國家機(jī)構(gòu)提供管理和服務(wù)并獲取稅收;軍隊(duì)可以抓住機(jī)會建設(shè)國防以提供安全;市場主體可以抓住機(jī)會生產(chǎn)商品和服務(wù)并交易以獲取利潤。由此可知,“國家治理”最初所提供的僅僅一個“充滿機(jī)會的池子”,而組織的存在則是為了捕獲這些機(jī)會。公共選擇理論認(rèn)為,人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經(jīng)濟(jì)人。在諾思看來,政府與私人無異,也是經(jīng)濟(jì)人,同樣會去捕獲盡可能多的機(jī)會以實(shí)現(xiàn)自身利益最大化。這里的機(jī)會就是產(chǎn)權(quán),即個人支配其自身勞動、物品和勞務(wù)的權(quán)利。政府捕獲的“機(jī)會”成為政府的產(chǎn)權(quán);市場捕獲的“機(jī)會”就成為市場的產(chǎn)權(quán)。個人和組織只有通過捕獲“機(jī)會”才能實(shí)現(xiàn)一定的價值,獲得自身的利益。但是,在市場廣泛存在信息不對稱、不確定性和機(jī)會主義的條件下,如果沒有一定的規(guī)則來限制個人和組織的捕獲行為,必然會產(chǎn)生混亂和無序。為了對抗和防止人們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過程中出現(xiàn)的無序和混亂,制度便應(yīng)運(yùn)而生。因此諾思認(rèn)為:“制度是為約束在謀求財(cái)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個人行為而制定的一組規(guī)章、程序和倫理道德行為準(zhǔn)則。”進(jìn)而言之,國家治理體系就是一個制度體系。
諾思認(rèn)為,以產(chǎn)權(quán)的界定和實(shí)施為基礎(chǔ)的制度安排直接影響一國的經(jīng)濟(jì)績效。全面深化改革依賴于一系列新的改革方案的出臺與實(shí)施,而任何改革方案本質(zhì)上又都是全新的制度安排,因此,改革的全面深化本質(zhì)上是新制度的全面化和深化。“全面”就要求在橫向上實(shí)現(xiàn)各個行業(yè)、各個領(lǐng)域的制度化,只有這樣才能保證一切生產(chǎn)要素的活力被充分激發(fā);“深化”就要求在縱向上系統(tǒng)而徹底的進(jìn)行改革,不能僅僅滿足于利益微調(diào),而要大刀闊斧地破除一些阻礙改革深化的藩籬和障礙。十八屆三中全會所提改革路線圖其實(shí)是國家全行業(yè)、全方位的一種制度設(shè)計(jì)藍(lán)圖。只有保證有效的制度安排并以國家強(qiáng)制力保證制度的有效實(shí)施,才能夠?qū)崿F(xiàn)經(jīng)濟(jì)績效的質(zhì)的提升,這也是本文所提“能動式跳躍”發(fā)展模式的內(nèi)涵所在。
三、如何實(shí)現(xiàn)能動式跳躍
(一)提高制度供給質(zhì)量構(gòu)建全面的制度體系
制度供給就是制度的生產(chǎn)。制度通過各種正式與非正式的規(guī)則規(guī)定了人們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可以怎么做,不可以怎么做。有效的制度供給能夠通過一定的獎懲機(jī)制影響行為人的偏好和選擇,使人們按照一定的規(guī)則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諾思認(rèn)為:產(chǎn)權(quán)的界定和實(shí)施所構(gòu)成的制度框架對一個國家的經(jīng)濟(jì)績效具有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因?yàn)楫a(chǎn)權(quán)內(nèi)含著對行為人的激勵結(jié)構(gòu)。個人和組織由于“經(jīng)濟(jì)人”的天性會首先關(guān)注產(chǎn)權(quán)內(nèi)的利益,對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務(wù)總是傾向于“搭便車”,從而造成資源的價值耗散,也就是所謂的外部性。只有國家或政府建立制度體系,清楚界定各種產(chǎn)權(quán),才能夠?qū)⑼獠啃詢?nèi)在化,實(shí)現(xiàn)資源價值的最大化。
構(gòu)建全面的制度體系,首先要針對專門的市場需求及時提供制度供給。當(dāng)前,我國正處于跳躍發(fā)展的關(guān)鍵時期,一旦制度供給跟不上經(jīng)濟(jì)社會發(fā)展的需要,勢必影響市場主體的判斷和預(yù)期。企業(yè)和資本對市場信息尤其是官方政策變動極為敏感,要想在瞬息萬變的市場中激發(fā)市場主體的參與熱情,政府必須提供完全的確定性。這就要求政府不僅要有宏觀的制度框架,還要盡可能提供細(xì)化的制度設(shè)計(jì)。中央政府負(fù)責(zé)能夠?qū)彆r度勢,在宏觀上為市場提供指導(dǎo)性的政策原則,地方政府則需要依據(jù)地方實(shí)際和中央的政策框架及時出臺政策細(xì)則,全方位構(gòu)建統(tǒng)一而有層次的市場經(jīng)濟(jì)制度體系。其次,構(gòu)建全面的制度體系必須考慮各種制度的協(xié)調(diào)配合。全面深化改革是一項(xiàng)以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為主線,其他配套改革相互協(xié)調(diào)的系統(tǒng)工程。改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看做是利益的重新分配,而利益主要包含人力和財(cái)政等因素,因此改革的全面深化必然要牽扯到財(cái)稅體制改革和戶籍制度的改革。財(cái)稅體制關(guān)乎中央和地方的利益配置,改革的根本原則應(yīng)當(dāng)是權(quán)、責(zé)、利一致,即誰承擔(dān)的事務(wù)多、責(zé)任重,誰分擔(dān)的利益就高。關(guān)鍵在于明確中央和地方的事權(quán),在此基礎(chǔ)上深化財(cái)稅改革,形成穩(wěn)定、透明、公平的財(cái)稅體系,才能夠更好地發(fā)揮中央和地方兩個積極性。
構(gòu)建完善的制度體系要極力避免制度安排的碎片化。所謂制度安排的碎片化是指由于宏觀制度框架模糊以及政策實(shí)施不力,地方政府或其他部門按照自身利益隨意出臺政策,造成的制度分化現(xiàn)象。由于中央各部委、地方政府本身存在利益固化現(xiàn)象,使得他們不可能從自身出發(fā)尋求制度改革和突破;不同的部門與系統(tǒng)也不可能主動突破對方的“制度屏障”改變現(xiàn)狀,甚至可能出現(xiàn)部門與部門之間利益結(jié)盟共同抵制改革。只有超越地方利益和部門利益的中央政府能夠突破各種利益壁壘,依靠強(qiáng)力推行改革。為避免制度安排出現(xiàn)碎片化,必須在中央政府的強(qiáng)力領(lǐng)導(dǎo)下,樹立全國一盤棋的改革思路,督促地方政府、各部門根據(jù)中央政策精神細(xì)化制度安排。
(二)完善市場法律體系保障制度有效實(shí)施
制度不會直接轉(zhuǎn)化為經(jīng)濟(jì)績效,制度體系也不會自動運(yùn)行,如果沒有國家的強(qiáng)制力保證制度的實(shí)施,任何制度都只能是一紙空文。契約和信用是市場經(jīng)濟(jì)運(yùn)行的基石,而契約的實(shí)施又依賴于各種法律法規(guī)的有效執(zhí)行。因此,規(guī)則和契約產(chǎn)生以后,還必須建立相應(yīng)的監(jiān)督和執(zhí)行制度。缺乏監(jiān)督,會出現(xiàn)各種各樣的尋租行為;缺乏執(zhí)行,則會喪失制度的威信,使制度形同虛設(shè)。為此,一方面應(yīng)構(gòu)建檢察、審判以及調(diào)解等仲裁機(jī)構(gòu)的制度體系,完善市場經(jīng)濟(jì)法律體系,確保司法機(jī)關(guān)能夠依法獨(dú)立行使職權(quán);另一方面應(yīng)加強(qiáng)對司法機(jī)關(guān)的監(jiān)督,防止隨意侵犯市場行為人的合法權(quán)益,保證司法公信力和制度的穩(wěn)定性、權(quán)威性。
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離不開科技創(chuàng)新,科技創(chuàng)新一方面需要制度激勵,另一方面則需要加強(qiáng)對知識產(chǎn)權(quán)的保護(hù)。政府應(yīng)不斷完善有關(guān)知識產(chǎn)權(quán)、專利權(quán)和商標(biāo)權(quán)的法律法規(guī),在成熟的時候設(shè)立知識產(chǎn)權(quán)法院,以確保知識產(chǎn)權(quán)得到保護(hù)。因?yàn)檫@些法律實(shí)施不僅僅是保護(hù)個人的創(chuàng)新成果,更為重要的是能夠?qū)θ鐣膭?chuàng)新提供一種長效的激勵機(jī)制。一個人發(fā)明了一種機(jī)器,國家給予一次性獎勵,這是對發(fā)明者本人偶然的一種刺激,如果國家將類似的獎勵形成制度,并對相關(guān)的產(chǎn)權(quán)加以法律保護(hù),那就會對全社會成員產(chǎn)生可以預(yù)期的長效刺激,進(jìn)而激勵所有人在各行各業(yè)努力創(chuàng)新。對于市場中發(fā)生的侵權(quán)案件應(yīng)快速依法審理,及時向社會公布結(jié)果,不斷提高人們的產(chǎn)權(quán)意識,為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創(chuàng)造良好的法治環(huán)境。
(三)發(fā)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打造“強(qiáng)化市場型政府”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堅(jiān)持和完善基本經(jīng)濟(jì)制度,加快完善現(xiàn)代市場體系、宏觀調(diào)控體系、開放性經(jīng)濟(jì)體系。”與過去相比,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由“基礎(chǔ)性”變?yōu)椤皼Q定性”,同時宏觀調(diào)控被置于同市場體系并列的位置,這種變化絕不是政策和觀念的微調(diào),而是一種認(rèn)識的飛躍和觀念的扭轉(zhuǎn)。當(dāng)然,中央的意思并非是宏觀調(diào)控不重要,而是要嘗試“以市場配置為主,國家調(diào)控為輔”的跳躍發(fā)展。改革開放雖然成就了中國的市場經(jīng)濟(jì),但我國的市場經(jīng)濟(jì)本質(zhì)上仍是在國家“宏觀調(diào)控”主導(dǎo)下的市場經(jīng)濟(jì),政府對市場的過多干預(yù)是其區(qū)別于西方市場經(jīng)濟(jì)的主要特色。這種干預(yù)一方面造成了政府的經(jīng)濟(jì)職能擴(kuò)張,國有企業(yè)效率下降以及嚴(yán)重的資源配置失衡;另一方面產(chǎn)生了大量的行業(yè)壟斷、尋租和腐敗現(xiàn)象,使相當(dāng)一部分社會資源被用于非生產(chǎn)性用途,造成了極大的資源浪費(fèi)。由此導(dǎo)致的市場主體地位不公平降低了中小企業(yè)和資本的參與積極性,從而降低了勞動、技術(shù)資本等要素轉(zhuǎn)變?yōu)樯唐泛头?wù)的效率。
中國要繼續(xù)實(shí)現(xiàn)經(jīng)濟(jì)績效的提升必須著力進(jìn)行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為市場潛力的充分爆發(fā)提供合適的制度環(huán)境。首先,必須合理界定政府與市場的產(chǎn)權(quán),只有界定好這兩個最大的產(chǎn)權(quán),才能徹底劃清兩者之間的界限。當(dāng)然,政府不是市場的對立面,沒有政府強(qiáng)制力保證各項(xiàng)政策的有效執(zhí)行,市場體系不可能順暢運(yùn)行;市場不提供稅收,政府也無法維持運(yùn)作。要割斷政府對市場的不當(dāng)干預(yù)。市場能有效提供的產(chǎn)品和服務(wù),政府就不提供;市場能有效運(yùn)作的行業(yè),政府就不“插手”。只有在合理劃分政府和市場各自“大產(chǎn)權(quán)”的基礎(chǔ)上,對政府內(nèi)部各個部門的“小產(chǎn)權(quán)”(職能)進(jìn)行界定,才能防止出現(xiàn)“八個部門管不好一頭豬”的怪象。對市場主體、生產(chǎn)要素的“小產(chǎn)權(quán)”進(jìn)行界定并提供保護(hù),才能讓一切勞動、知識、技術(shù)、管理、資本更高效的轉(zhuǎn)化為商品和服務(wù)。其次,必須要增強(qiáng)政府的可信承諾,這不僅要求政府管住自己不向市場伸手,更重要的是政府必須提供有效地制度實(shí)施,建立起政府與市場參與者之間的可信承諾,使市場主體對自身利益具有安全感,對政府的行為具有可預(yù)測性。
四、挑戰(zhàn)和展望
在引進(jìn)市場經(jīng)濟(jì)理念和模式的同時,不可避免地會有政治、社會領(lǐng)域的“雜質(zhì)”隨經(jīng)濟(jì)一起涌入,而且市場經(jīng)濟(jì)的共性和全球化決定了資本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在發(fā)展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也可能在我國出現(xiàn)。此外,經(jīng)濟(jì)的飛速發(fā)展使我們形成了某種固化的路徑依賴,與此相伴產(chǎn)生了大量的附著的既得利益者形成了潛在的改革阻力。這些都是接下來的發(fā)展所必須要面對的挑戰(zhàn)。
歷次的經(jīng)濟(jì)危機(jī)顯示出西方國家在駕馭市場能力方面的局限性。令人欣慰的是,中國成功構(gòu)建起了相對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jì)體制,而且這種體制在國內(nèi)已經(jīng)定型為一種可控的、可操作的發(fā)展模式,在國際上也實(shí)現(xiàn)了與全球化的成功對接。這使得中國政府在繼續(xù)引導(dǎo)國內(nèi)發(fā)展和參與國際競爭中能夠做到“心中有數(shù)”。雖然改革會有風(fēng)險(xiǎn),但只要堅(jiān)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走封閉僵化的老路,不走改旗易幟的邪路”,就可以最大限度避免出現(xiàn)大的波動和失誤。
參考文獻(xiàn):
[1] 習(xí)近平.關(guān)于《中共中央關(guān)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要問題》的說明[N].人民日報(bào),2013.11.16(01)
[2] 習(xí)近平.改革是由問題倒逼而產(chǎn)生[N].新京報(bào),2013.11.14
[3] 張維為.中國成功緣于拒絕市場和民主原教旨主義[EB/OL].觀察者網(wǎng).2014.05.08
[4] 塞繆爾·P·亨廷頓.變化社會中的政治秩序[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5] 諾思.經(jīng)濟(jì)史上的結(jié)構(gòu)與變革[M].北京:商務(wù)印書館,2009
[6] 諾思.制度、制度變遷與經(jīng)濟(jì)績效[M].上海:格致出版社,2008
[7] 楊光斌.政治變遷中的國家與制度[M].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
[8] 金觀濤,劉青峰.開放中的變遷[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
[9] 俞可平.治理與善治[M].北京:社會科學(xué)文獻(xiàn)出版社,2000
(作者單位:山西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簡介:劉云周,山西大學(xué)政治與公共管理學(xué)院2013級行政管理專業(yè)碩士研究生,研究方向?yàn)楣舱摺#?/p>
(責(zé)編:賈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