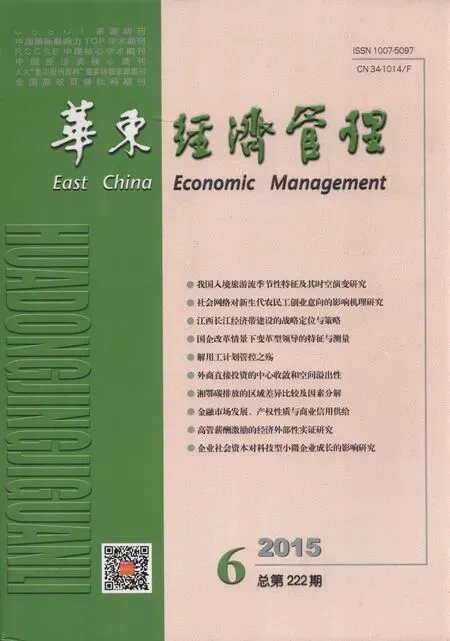辱虐管理對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的影響:情緒耗竭的中介作用
朱曉妹,連 曦,郝龍飛,丁通達,2
(1.華東交通大學 經濟管理學院,江西 南昌330013;2.北京中世能信息咨詢有限公司,北京100022)
一、引言
近年來,破壞性領導行為開始受到研究者的廣泛關注。作為破壞性管理行為的典型代表之一,辱虐管理是現實組織管理中一種較為常見且普遍的現象。根據一項來自美國的調查結果顯示,在工作過程中遭受過侵犯的員工不少于2 億,遭受過威脅的員工接近6億,而遭遇過性騷擾的員工達到了16億之多[1]。我國具有集體主義、高權距、高不確定性回避的國家文化,受傳統文化的影響,辱虐管理行為在領導者的日常行為表現上也十分明顯。傳統的家長式管理方式,“打是疼,罵是愛”的教育理念根深蒂固,上級與下屬之間存在著“上尊下卑”的等級關系,這些很自然地成了產生辱虐管理的根基所在。然而,辱罵、輕視、侮辱以及貶低等破壞性管理行為,會給員工的內心造成傷害,并容易引發家庭矛盾和糾紛,降低員工的工作滿意度、組織承諾、留職傾向以及工作績效,提高員工的缺勤率和離職率,甚至引發員工出現針對組織和個人的報復性行為[2]。Penney&Spector(2005)的研究結果也指出,當員工遭受到敷衍不禮貌的行為對待,或者是受到侵犯,使員工的自尊受到傷害,會引發員工表現出指向組織和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3]。反生產工作行為具有自發性和敵對性,會給組織帶來諸如生產力下降、財務浪費或受損、保險費用、法律費用、聲譽受損以及由于員工道德水平降低而引起的損失等。由此可見,探索辱虐管理與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的關系以及情緒耗竭的中間影響作用,對于組織提高領導素質和管理水平,改善員工關系,促進員工心理健康有著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根據公平理論的觀點,一旦員工遭受到組織或領導不公平或不對等的對待之后,其出現消極工作態度、反生產工作行為和工作行為懈怠等情形的傾向就會明顯提升,他們希望以此來使內心的平衡得到恢復[4]。那么,辱虐管理是通過什么機制來影響員工的反生產工作行為呢?不少研究結果顯示,上級的辱虐管理通常會與下屬的郁悶、倦怠、焦慮、工作緊張和低自尊等顯著相關[5]。這些負面的情緒體驗會逐漸導致員工心理難以承受,員工情緒出現耗竭和崩潰,極易引發反生產工作行為的出現,如消極怠工、破壞設備與工具、偷竊等。辱虐管理不僅會使工作中“溢出”由此所引發的負面效應,還會使得員工把工作中受的“氣”傳遞到家人身上,甚至會激化成家庭暴力。因此,研究辱虐管理與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的內在情緒反應機制,有助于進一步深化辱虐管理的理論研究,也有助于組織管理者不斷改進領導方式,關注員工心理健康,提高組織和員工福祉。
二、文獻綜述和假設的提出
(一)辱虐管理
Tepper 在2000年率先提出了辱虐管理的概念,并將概念界定為,“下級感知到的上級領導表現的具有持久連續性、不包括身體接觸性質侵犯在內、言語或非言語的敵意行為”[6]。其行為具體表現為辱罵或羞辱下屬、責怪下屬員工以擺脫他/她自己的尷尬、常提起下屬過去犯過的錯誤和遭遇的失敗、對下屬漠不關心、怒視、輕視和貶低下屬、批評下屬的想法或意見很愚蠢、在眾人面前侮辱下屬等。國內外研究表明,辱虐管理會對員工的態度、行為、心理以及績效等帶來非常消極的影響[7],進而削弱組織效能。辱虐管理通常與員工工作滿意感、組織承諾和組織公民行為[8]、建言行為[9-10]等積極的態度和行為負相關;并與員工的消極行為(如抵抗行為、攻擊行為及偏差行為等)相聯系。
(二)辱虐管理與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
員工對于組織和領導者如何對待他們的問題十分關注。當得到了公平、公正的待遇時,他們會認為自己是有價值的,且受到了應有的尊重,其工作的保障程度也是比較高的[11]。公平啟發式理論指出,如果員工對公平與否產生了自己的判斷,就會通過這種判斷來決定行動的方式。例如,當員工感覺到管理者是公平的,他們就會表現出良好的反應,并且對物質回報沒有特殊要求。此外,根據社會交換理論中的公平互惠原則,當員工得到管理者或同事給予的尊重時,他們會以更高水平的組織公民行為和組織承諾來回報對方[12];相反,當員工得不到管理者的尊重時,他們則會表現出強烈的消極反應,降低工作績效[2]。實施辱虐管理行為的人會利用其權力對員工進行壓迫,并使員工受到粗暴的對待[13],如恐嚇、威脅或嘲笑員工,在公開場合批評、嘲笑或羞辱員工等[14],員工會認為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對待,為了恢復這種公平感,便會實施報復行為[2]。研究也證實了這點,感知到領導者辱虐管理行為的員工更可能會對其決策加以抵制[6],減少有益的工作行為[15],并產生指向主管及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14]。
大量研究結果發現,員工會通過從事對組織和其他員工有害的行為來應對辱虐管理。反生產工作行為就是員工遭受到上級辱虐管理后所采取的報復行動之一[14]。反生產工作行為一般包括指向組織的和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Thau等(2009)的研究表明,辱虐管理會正向影響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7],但是,對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的影響并不顯著。國內學者的研究結果也顯示辱虐管理同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所呈現的正相關關系[16-17]。基于上述分析,本研究提出假設1。
假設H1:辱虐管理會對員工的反生產工作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假設H1a:辱虐管理會正向影響指向組織的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且影響顯著;
假設H1b:辱虐管理會正向影響指向人際的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且影響顯著。
(三)情緒耗竭的中介作用
作為心理過勞或心理性緊張的一種典型癥狀表現,情緒耗竭是員工面臨高工作要求時的一種應激性反應。上級對下屬的羞辱、辱罵和貶低等行為會給員工的心理帶來消極影響,巨大的心理壓力很容易讓員工對工作產生負面的抵觸情緒,這種不良情緒長期積累會讓員工感到情緒低沉、筋疲力盡以及自我否定。Einarsen 等(2007)研究發現,與辱虐管理聯系最為密切的下屬心理反應通常都呈現消極、負面的特性,其中最為典型的心理感受是:惱怒、挫折感和自尊下降[18]。Tepper(2000)研究表明,辱虐管理會顯著正向影響情緒耗竭[6]。Harvey等(2007)分析指出,辱虐管理與員工的情緒耗竭正相關[19]。我國學者劉軍、吳隆增和林雨(2009)在一項針對電子制造企業的調查研究中得出,主管的辱虐行為表現會正向影響下屬的情緒耗竭,且影響顯著[20]。
實證分析證實,在組織中員工所經歷的情緒體驗會給他們的心理和生理健康、對待組織和工作的態度以及工作相關的行為和結果等造成顯著影響[21]。當員工出現情緒耗竭時,往往會感到身心疲憊,缺乏目標和斗志,對組織中的人和事漠不關心等。這些消極的、負向的情緒無法得到很好的宣泄時,員工很難集中精力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當中去,容易導致員工的工作態度敷衍、工作績效降低、組織承諾和留職傾向下降。而且,這種因為工作壓力而滋生出的負面不良情緒可能會導致一些攻擊行為,比如故意不服從上級要求、不配合同事工作、破壞組織聲譽、浪費或違規使用組織財產、損害組織利益等。Spector和Fox(2005)也指出,工作壓力容易導致員工產生負面情緒反應,并表現出攻擊行為[22]。其他學者也提出情緒對反生產工作行為有直接影響[23]。結合上述分析內容,本研究提出假設2。
假設H2:情緒耗竭對辱虐管理與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的關系有顯著的中介效應。
假設H2a:情緒耗竭對辱虐管理與員工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的關系有顯著的中介效應;
假設H2b:情緒耗竭對辱虐管理與員工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的關系有顯著的中介效應。
三、研究樣本和研究方法
(一)研究樣本
本研究于2012年7-8月在南昌、杭州、溫州和紹興4 個城市5 家企業開展了問卷調查。總共發放問卷300 份,實際回收259 份,剔除空白過多等無效問卷后,總共得到有效問卷229 份,有效回收率為76.3%。在被試中,男性占41.9%,女性占58.1%;20 歲以下的占2.2%,20~29 歲的占82.1%,30~39 歲的占11.8%;大學專科及以下占62.4%,大學本科占32.3%,碩士及以上占5.3%;國有企業員工占38.9%,民營企業員工占61.1%。
(二)變量測量
(1)辱虐管理。本研究采用的是運用最廣泛的Tepper(2000)編制的量表[6]。量表共有15 個題項構成,例如,我的主管會侵犯我的隱私;我的主管會因為其他事情而遷怒于我;我的主管會在別人面前說我壞話;我的主管會提起我過去犯過的錯誤和遭遇的失敗;我的主管對我粗魯無禮等。該量表屬于李克特5 點量表,其中1 表示從不;2 表示很少;3 表示一般;4 表示較多;5 表示經常。該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31,具有較好的信度。
(2)反生產工作行為。測量反生產工作行為選取的是Aquino、Lewis 和Bradfield(1999)編制的量表[24]。該量表共由14個題項構成。其中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CWB-O)有8個題目,例如,為了逃避工作而做不必要的休息;沒有經過允許的情況下早退;有意不理會上級的指示等。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CWB-P)有6 個題目,例如,拒絕和同事說話;對同事有侮辱性的言論或動作;在他人面前嘲弄同事等。該量表屬于李克特5 點量表,其中1 表示從不,2 表示很少,3 表示一般,4表示較多,5 表示經常。反生產工作行為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939,具有較高的信度。
(3)情緒耗竭。本研究采用的是Maslach &Jackson(1981)編制的量表[25]。該量表由9個題項構成,例如,我對我的工作實在承受不住了;我的工作讓我有挫折感;我的工作讓我感到精力耗竭等。該量表屬于李克特5 點量表,其中1 表示從不,2 表示很少,3 表示一般,4 表示較多,5 表示經常。情緒耗竭量表的Cronbach’sα系數為0.887,信度較高。
(4)控制變量。實證分析結果顯示,性別、年齡、工作單位、受教育程度、工作時間等對員工的反生產工作行為有著顯著的影響[26]。因此,本研究選擇性別、年齡、工作單位性質和受教育程度4 項作為控制變量。
(三)共同方法偏差檢驗
本研究采用Harman 單因素檢驗法、主成分分析法對所有觀察變量進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未旋轉的因子分析結果顯示共析出了8個因子,8個因子的方差變異解釋量共為66.4%,其中第一個因子的方差變異解釋量為18.5%,其他7個因子的方差變異解釋量均位于2.8%~16.9%的區間。根據共同方法偏差檢驗的要求,如果探索性因子分析結果中只有一個因子或者某個因子能夠解釋大部分的方差變異,就說明存在著共同方法偏差,且程度極高。由此可見,本研究分析結果雖無法完全排除共同方法偏差,但是問題并不嚴重。
四、分析結果
(一)相關分析
研究變量的相關分析結果如表1 所示。從表1的數據分析結果來看,員工評價的辱虐管理和反生產工作行為水平并不太高。但是,在Tepper(2000)針對美國樣本的研究中,辱虐管理的均值為1.54,標準差SD為0.74[6],另一項研究的均值也在1.5 左右[15]。因此,本研究中的數據是可靠的,可以接受的。并且,辱虐管理、反生產工作行為和情緒耗竭之間的相關系數在0.214~0.370 之間,為下一步回歸分析提供了良好基礎。

表1 研究變量均值、標準差和相關系數
(二)辱虐管理對反生產工作行為影響的回歸分析
回歸分析結果如表2 所示,以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工作單位性質為控制變量,以辱虐管理為自變量,反生產工作行為為因變量進行回歸分析,回歸系數為0.381(p<0.001),表明辱虐管理對反生產工作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研究假設H1得到了驗證;若以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為因變量,回歸系數為0.350(p<0.001),表明辱虐管理對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驗證了研究假設H1a;若以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為因變量,方程的回歸系數為0.371(p<0.001),表明辱虐管理對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上述結論驗證了研究所提出的假設H1b。

表2 辱虐管理對反生產工作行為影響的回歸分析
(三)情緒耗竭的中介作用檢驗
根據Baron 和Kenny(1986)提供的方法[27],中介效應要滿足以下三個條件:①自變量對中介變量必須存在顯著影響;②自變量對因變量必須存在顯著影響;③當自變量和中介變量同時代入回歸方程解釋因變量時,中介變量的效應顯著而自變量的效應消失(完全中介作用)或者減弱(部分中介作用)。
情緒耗竭在辱虐管理與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如表3所示。方程1中,自變量為辱虐管理,因變量為情緒耗竭,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水平很高,其中β=0.284,p<0.001,說明辱虐管理會顯著正向影響情緒耗竭,符合中介效應判斷條件(1);方程2 中,自變量為辱虐管理,因變量為反生產工作行為(CWB),回歸方程的顯著性水平也很高,其中β=0.381,p<0.001,判別中介作用的前提條件(2)得以滿足;方程3 中,自變量辱虐管理和中介變量情緒耗竭同時進入回歸方程,以反生產工作行為(CWB)作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相對于方程2,回歸方程3的顯著性水平仍然很高,但辱虐管理的β絕對值由原來的0.381降至0.319,符合判斷中介效應的條件(3),情緒耗竭起部分中介作用,假設H2得到了驗證。同理,方程4 中,以辱虐管理為自變量,以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作為因變量的回歸方程達到了高顯著性水平,其中β=0.350,p<0.001,滿足對中介作用進行判別的條件(2);方程5同時以辱虐管理和情緒耗竭作為自變量進入回歸方程,以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作為因變量,回歸方程也達到了較高的顯著性水平,相對于自變量只有辱虐管理的方程4,方程5 中β絕對值由原來的0.350 降至0.286,符合判斷中介效應的條件(3),情緒耗竭在辱虐管理和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驗證了假設H2a。同理,方程6 中,自變量為辱虐管理,因變量為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回歸方程的顯著型水平較高,其中β=0.371,p<0.001,滿足了判斷中介作用的條件(2)。方程7中,辱虐管理和情緒耗竭同時進入回歸方程,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作為因變量,回歸方程也達到了顯著的水平,相對于自變量只有辱虐管理的方程6,方程7 中β絕對值由原來的0.371降至0.319,根據判斷中介作用的條件(3),情緒耗竭在辱虐管理和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起部分中介作用,驗證了假設H2b。

表3 情緒耗竭在辱虐管理與反生產工作行為之間的中介效應檢驗
五、討論與建議
綜上,在中國文化背景下,辱虐管理不僅存在于組織當中,而且會導致員工的反生產工作行為,這與西方的研究結果相一致[7,28]。社會交換理論的觀點是,當個體受到傷害且被感知時更可能會有消極負面的行為表現。由于領導有影響員工晉升、工作崗位安排和薪酬收入分配等重要決策的權力,所以,遭受到上級辱虐對待的、處于弱勢地位的員工通常并不愿意和上級發生正面的沖突。因為員工直接反抗上級的辱虐對待很可能會導致雙方矛盾進一步激發,并招致上級進一步的辱虐對待或打擊報復,更有甚者,會丟掉工作。因此,受到了辱虐對待的員工一般不會直接對抗實施辱虐管理行為的領導,而是以組織和同事等作為對象實施反生產工作行為的替代性報復[6],以此來使這種受損的公平感得到平復。員工遲到、早退、裝病、浪費組織財產等這些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會直接降低組織的出勤率和生產效率;而辱罵、歧視、嘲笑同事,拒絕幫助同事以及與同事合作,會形成不良的工作氛圍和環境,降低員工工作滿意度以及工作效率。此外,研究結果還表明,辱虐管理會通過情緒耗竭這一中介變量對反生產工作行為、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發揮影響作用。當受到上級的侮辱、辱罵、嘲笑、蔑視、遷怒時,員工自尊心受損,心理壓力增大,精神緊張,容易導致情緒耗竭[6],而負面情緒可以預測反生產工作行為[23]。因此,辱虐管理一方面會直接導致員工的反生產工作行為,另一方面會通過情緒耗竭對員工反生產工作行為發生作用。
鑒于辱虐管理會使員工的心靈受傷、情志抑郁、精神緊張,引發員工產生情緒耗竭,從而導致員工出現反生產工作行為,所以,組織應采取有效措施來消除辱虐管理的消極影響,以避免給組織帶來生產效率、管理效率損失以及財產損失。首先,組織要重視辱虐管理可能給組織帶來的危害,通過完善組織規章制度、重視管理人員的選拔和培訓、關注領導者身心健康等途徑來減少辱虐管理行為的發生。其次,管理者應該提升個人素質,加強個人修養,約束和控制個人消極情緒和不良行為,提高溝通技巧和水平,極力避免對員工實施辱虐管理,努力為員工營造一個善意和諧的工作環境。第三,組織應積極建立員工申訴制度、提供申訴渠道,從制度上約束管理者辱虐行為的發生,并為受到辱虐對待的員工提供心理援助和輔導,以減少辱虐管理帶來的負面效應。第四,組織應監控員工遲到、早退、消極怠工等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特別是群發的指向組織的反生產工作行為,以避免給組織帶來嚴重的損失。第五,管理者應努力創造良好的工作氛圍,加強對員工的心理輔導和疏導,鼓勵員工開展合作與交流,有效降低指向人際的反生產工作行為。
六、研究不足
囿于研究條件的限制,本研究還存在一些不足之處。首先,研究以國外比較成熟的量表作為量表來源,雖然其信效度都較好,但可能會存在跨文化差異問題。未來可以開發適合中國文化情境下的辱虐管理和反生產工作行為量表。其次,由于條件所限,本研究中只選取了南昌、杭州、溫州和紹興四個城市的5 家企業作為樣本來源,涉及的行業以及范圍都略顯局限。今后的研究中可以擴大樣本的范圍。最后,本研究中的數據來源于員工自我評價的結果,相同的數據來源容易導致共同方法偏差。因此,在今后的研究中,可以采用主管員工配對數據以減少共同偏差帶來的誤差。
[1]Lau V C S,Au W T,Ho J M C. A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Review of Antecedents of Counterproductive Behavior in Organizations[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03,18(1):73-99.
[2]Tepper B J. Abusive Supervision in Work Organizations:Review,Synthesis,and Research Agenda[J]. Journal of Management,2007,33(3):261-289.
[3]Penney L M,Spector P E. Job stress,incivility,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CWB):the moderating role of negative affectivity[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2005,26(7):777-796.
[4]Restubog S L D,Bordia P,Bordia S. The Interactive Effects of Procedural Justice and Equity Sensitivity in Predicting Responses to Psychological Contract Breach:An Interactionist Perspective[J]. Journal of Business and Psychology,2009(2):165-179.
[5]Hoobler J M,Brass D J.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family undermining as displaced aggression[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6,91(5):1125-1133.
[6]Tepper B J. 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2):178-190.
[7]Thau S,Bennett R J,Mitchell M S,et al. How management style moderat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workplace deviance:An uncertainty management theory perspective[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9,108(1):79-92.
[8]Aryee S,Sun L-Y,Chen Z X G,et al.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Contextual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Emotional Exhaustion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Work Unit Structure[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2008,4(3):393-411.
[9]嚴丹. 上級辱虐管理對員工建言行為的影響——來自制造型企業的證據[J]. 管理科學,2012,25(2):41-50.
[10]吳維庫,王未,劉軍,等. 辱虐管理,心理安全感知與員工建言[J]. 管理學報,2012,9(1):57-63.
[11]Tyler T R,Blader S L. The group engagement model:Procedural justice,social identity,and cooperative behavior[J].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03,7(4):349-361.
[12]Masterson S S,Lewis K,Goldman B M,et al. Integrating Justice and Social Exchange:The Differing Effects of Fair Procedures and Treatment on Work Relationships[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4):738-748.
[13]Ashforth B E. Petty Tyranny in Organizations:A Preliminary Examination of Antecedents and Consequences[J].Canadian Journal of Administrative Sciences / Revue Canadienne des Sciences de l′Administration,1997,14(2):126-140.
[14]Mitchell M S,Ambrose M L. Abusive supervision and workplace deviance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negative reciprocity beliefs[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2007,92(4):1159-1168.
[15]Harris K J,Kacmar K M,Zivnuska S. An investigation of abusive supervision as a predictor of performance and the meaning of work as a moderator of the relationship[J].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7,18(3):252-263.
[16]高日光,孫健敏. 破壞性領導對員工工作場所越軌行為的影響[J]. 理論探討,2009(5):156-158.
[17]顏愛民,高瑩. 辱虐管理對員工職場偏差行為的影響:組織認同的中介作用[J].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學報,2010(6):55-61.
[18]Einarsen S,Aasland M S,Skogstad A. Destructive leadership behaviour:A definition and conceptual model[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7,18(3):207-216.
[19]Harvey P,Stoner J,Hochwarter W,et al. Coping with abusive supervision:The neutralizing effects of ingratiation and positive affect on negative employee outcomes[J]. The Leadership Quarterly,2007,18(3):264-280.
[20]劉軍,吳隆增,林雨. 應對辱虐管理:下屬逢迎與政治技能的作用機制研究[J]. 南開管理評論,2009(2):52-58.
[21]Schat A C H,Frone M R. Exposure to psychological aggression at work and job performance:The mediating role of job attitudes and personal health[J]. Work & Stress,2011,25(1):23-40.
[22]Spector P E,Fox S. The stressor-emotion model of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C]//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Investigations of actors and targets,Washington D C: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2005:151-174.
[23]Mount M,Ilies R,Johnson E. Relationship of personality traits and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s:the mediating effects of job satisfaction[J]. Personnel Psychology,2006,59(3):591-622.
[24]Aquino K,Lewis M U,Bradfield M. Justice constructs,negative affectivity,and employee deviance:A proposed model and empirical[J]. Journal of Organizational Behavior,1999,20(7):1073-1091.
[25]Maslach C,Jackson S E. The measurement of experienced burnout[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Behavior,1981(2):99-113.
[26]Peng H. Counterproductive Work Behavior Among Chinese Knowledge Worke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election and Assessment,2012,20(2):119-38.
[27]Baron R M,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Conceptual,strategic,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1986,51(6):1173-1182.
[28]Tepper B J,Carr J C,Breaux D M,et al. Abusive supervision,intentions to quit,and employees’workplace deviance:A power/dependence analysis[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2009,109(2):156-1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