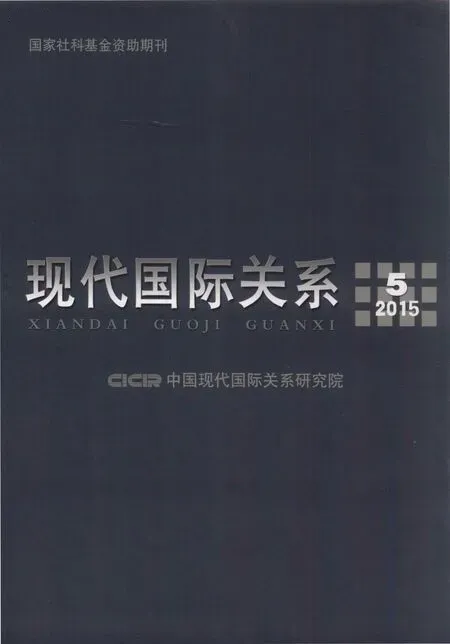審視亞投行的三個“坐標”
張運成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
亞投行是近年來中國創建或提議的、具有地區或全球層面意義的四家新機構之一。其他三家機構包括金磚國家發起的新發展銀行、應急儲備安排以及擬議中的上合組織開發銀行。其中,亞投行的時代特征、代表性、潛在影響力和之于中國的重大意義尤為突出。半年來,亞投行籌建工作緊鑼密鼓展開,亞投行漸漸熱起來,這與其中的中國因素密切相關,與中國發展帶給世界的機遇密切相關。亞投行的基本定位也逐步清晰,這是一個由中國倡議、發展中國家主導、發達和發展中經濟體平等參與的多邊開發金融機構。從本質上講,亞投行是中國提供的全球公共產品,是中國在其中擁有重大影響力的國際組織,是中國與世界關系深度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和里程碑,可從三大“坐標”的角度予以審視、解讀。
一是“歷史的坐標”。亞投行這一世界級的戰略構想,正確把脈了世界與中國發展大勢,將中國國勢、國家形象帶上歷史新高度。1874年,時任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鴻章上奏《籌議海防折》,分析了中國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嚴峻形勢:“一國生事,諸國構煽,實為數千年未有之變局。”1895年,李與日本簽訂了《馬關條約》,變局終致敗局。120年后的今天,中國倡議亞投行,落地有聲,應者云集,開拓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歷史的新舊坐標發生根本轉變。這一回,變局帶來的是好局、勝局。
亞投行如此受追捧或許令人始料未及,卻不難理解,這是中國與世界關系歷史性變化的必然結果。如果將中國比作一個“坐標原點”,中國歷史及其現代化進程為“橫坐標”,中國的國際觀為“縱坐標”,那么中國在每一個時間段上如何看世界,就形成了中國與世界的對應“關系”。中國領跑世界達數千年之久,但現代化進程緩慢,中國對外部世界的認識、與世界的關系長期以來處于“坐標”的低位。到了近代,中國十分明顯地落后于世界發展進程。1776年,英國的亞當·斯密就認識到了這種情況,他在《國富論》中寫道:“中國似乎長期處于靜止狀態”。垂垂老矣的大國!此后的百多年間,世界大體上就是這么看中國的。反過來,中國對世界的認識只是到了近代才發生突變,出現了一批“睜眼看世界”的人。中國人看世界看懂了一個道理:落后就要挨打。不夸張地說,這是新中國全力投入現代化建設的最強大的精神動力。
今天,中國又到了另一個要“睜眼看世界”的時段,但情況已與上次全然不同,全球化時代中國與世界聯系日益深刻、廣泛。一方面,外部世界繼續深刻地影響著中國;另一方面,中國也正以其獨特的發展模式影響國際體系轉型的軌跡和方式,越來越深入地參與塑造國際規范和國際貿易、金融、安全、氣候變化等領域國際制度的構建。中國人看世界又看出了另一個道理:秉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理念,與世界各國共同打造利益共同體、責任共同體和命運共同體,共同促進人類文明進步事業,這正是中國倡議亞投行的根本宗旨與理念所在。
二是“大國的坐標”。亞投行從構想到落實行動,充分體現了中國作為大國的責任與擔當,中國運籌國際事務表現出了更大成熟度,融入、影響全球化進程邁入新階段。改革開放30多年來,中國經濟騰飛,作為發展中的大國在發展理念和路徑上積累了許多經驗;而自身經驗的分享將有助其他發展中經濟體的增長與繁榮,亞投行專注于基礎設施建設,正是源于中國的成功發展經驗。
大國應有大國作為。中國是大國,無論是過去的重重困難,還是今天的實力增長,內心始終是大國心態,不是馬仔心態,這是一種氣勢,一種格局,更是一種道義的自信,沒有這種氣勢、格局和道義,成不了大國。短短半年時間,亞投行受到了域內外的廣泛追捧,轟動效應或許有所放大,但中國體會到了真正大國所具有的號召力、引導力:七國集團中分別有德國、法國、英國和意大利4國加入;二十國集團中有14個成員國加入;經合組織成員國(OECD)中21國加入;金磚五國全部加入;上海合作組織六個成員國全部加入。全球經濟總量排名前十的國家中,除美、日外全部加入。值得一提的是,所有與中國有南海爭端的國家都申請加入亞投行,其間的成功運作顯示中國政治成熟度提高,并在亞洲事務的參與度上邁出重要一步。
根據2014年簽署的籌建亞投行備忘錄,亞投行總部將設在北京。在股權分配上,亞投行將以GDP為基礎,其中亞洲成員的股權占比可能達70% ~75%,亞洲以外國家則分配剩余的25% ~30%股權。這意味著中國成為亞投行第一大股東幾成定局。作為第一大股東的地位不是特權,中國不會以老大自居,而是平等待人;將遵守國際通行準則,盡量以達成一致的方式決策。
大國行事需擇天下英才而用之。亞投行的籌建,聘用或咨詢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等機構的專家。目的就是要體現亞投行的專業、公開、透明和民主原則。以IMF為例,它現有1500位具有博士學位的經濟學者,1000位輔助人員;經濟學者中的800人負責具體國家的經濟研究,另外700人按功能劃分,專責財政200人,專責研究200人,專責金融市場200人,專責統計100人。IMF進行經濟預測時一半使用模型,同時參考800位國別經濟學者通過分析得出的預測結果,并將二者加總。亞投行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投行”,而是中國第一次以主導者身份與歐洲老牌工業強國建立關聯利益的投資銀行,兼具投資利益、全球金融治理、大國責任等多重功能,有無足夠的人才擔當重任是其成功的關鍵所在。這方面,IMF的運作模式可為參照、標準。
三是“秩序的坐標”。中國通過亞投行展現了參與塑造國際金融秩序的意愿與能力,開始了從被動的全球化參與者向主動引領者的轉變,這對中國及整個世界經濟秩序的變化都有重要意義。
英國《金融時報》指出,亞投行或許會成為撬動二戰后美國一家獨大的國際金融治理結構的杠桿。美國前財長、哈佛大學教授薩默斯指出,亞投行的建立標志著美國失去了其“全球經濟體系擔保人”的地位。顯然,西方習慣于把中國的一舉一動都解讀為對美國主導地位的挑戰。當下,中國還處在自己的發展階段和正常節奏上。從經濟全球化的角度看,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經濟成就的幾十年,實際也是適應美國主導現存國際經濟秩序的幾十年。中美在現存秩序內合作共贏的基礎實、條件好、機會多,兩者絕非零和博弈關系。對中國而言,不存在積極打破甚至瓦解這個體系的迫切性。
然而也毋庸諱言,中國正在現有秩序中推動新秩序的建立,同時做好“另起爐灶”的準備,畢竟歷史發展“獎勵”改革、創新甚至適度的冒險,會給走在前面的國家巨大回報。新舊秩序變革、交替之際,尋找、抓住機遇最關鍵。這次亞投行成立的時機很好,拿捏到位。因為亞投行的成立不僅是金融經濟問題,還涉及到國際政治博弈。現有國際經濟體系中,一方面美國領導力減弱,歐洲陷入衰退甚至變成了債務國,可謂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發達國家又不能納賢和讓步,如奧巴馬就曾不止一次地宣稱,美國“決不做老二”。這兩個方面發生矛盾,自然促使其他國家“另立山頭”。西方國家之間以及內部向來不是鐵板一塊。中國適時提出亞投行倡議,在國際上、學術界、智庫中以及政治上都能站得住腳。開弓沒有回頭箭,未來站穩腳跟后,可考慮將相關機制用好、用足,如適時、適機倡議召開“亞投行首腦峰會”等,打造出新型且具特色的全球治理平臺,做大影響力。
亞投行旨在建立一個真正的多國協商共治的全球性政策銀行,特別為全球金融改革、合作賦予新意與實質內容,既需腳踏實地穩步推進,也要尋找突破口。作為多邊開發金融機構,亞投行應堅持發展中國家主導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融資平臺的特色。與其他決策領域相比,基礎設施政策受意識形態和特別利益集團的影響要更小。當前,亞洲的可持續性發展仍然受到基礎設施投資方面巨大缺口的制約,而亞洲國家從現有國際開發機構中獲得的基建貸款很少。這方面,亞投行要利用自身的資本優勢拿出自己的具體方案。
新手當走新路。從全球治理體系上看,亞投行應視作是聯合國機制、國際金融治理體制的有益補充和完善。從其工作重點看,亞投行是對現有國際金融機構的直接、有益補充,并將激勵多邊開發機構完善制度設計和實現互利共贏。作為新手,亞投行應加強與現有多邊開發機構合作,積極營造互補而非競爭關系,實現互利共贏。IMF、世行和亞行等機構負責人都已表示出與亞投行加強合作的意愿。可以預見,亞投行未來在籌備、啟動基礎設施項目時會面臨融資安排、投資回報率,以及風險管控等多重挑戰,與其他國際機構在提供技術支持和聯合提供項目融資、治理結構、運營標準、投融資機制創新等方面有巨大的合作空間。
盛名之下,一些國家對亞投行的冷嘲熱諷、質疑反對聲音也會始終存在。中國復興崛起要走的路還很長,周雖舊邦,其命維新。環視全球,中國融入世界的因素、阻力更為復雜,在贏得國際尊敬的同時,也在看到更多的摩擦、猜疑甚至挑釁。當前,亞投行正式成立前還有大量工作要做。良好的開端是成功的一半,中國需要認真做好后續工作,加大協調力度,繼續調動各方合作意愿共謀發展。只有持之以恒,幸運的天平才會繼續向亞投行傾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