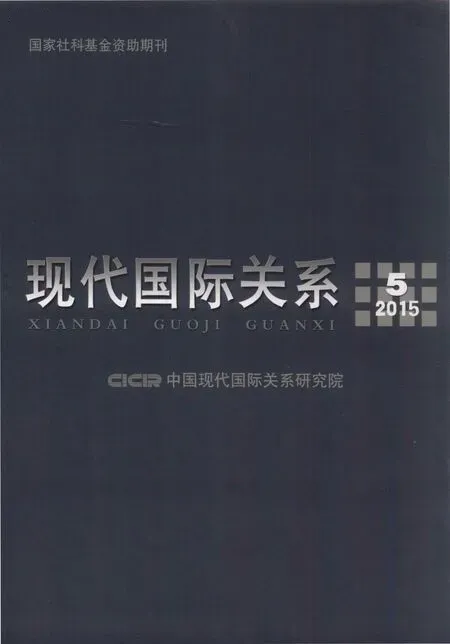做實亞投行應先解決的三個問題
魏 亮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籌建令人矚目,4個月內召開四次談判代表會議,57個國家成為該行創始成員國。根據該行網站披露,按照規劃,亞投行有望于2015年6月底完成章程談判,待各國批準后,或將于年底前運營。迄今為止,無論是從推進速度還是參與國家數量看,亞投行的籌建,或者說做大亞投行,都是一次值得稱道的多國集體行動。單憑這一點,就要優于發軔之時的世界銀行(28國)、美洲開發銀行(20國)、亞洲開發銀行(31國)、歐洲投資銀行(6國)。然而,亞投行是一項長久的事業,要讓57個(未來可能更多)國家的集體行動存續,使之做實、做出特色,或將是個微妙的長期命題。恰因為此,亞投行在正式運營之前先理清思路便至關重要。就當下而言,為了使亞投行走穩走遠,至少要解決好三個問題。
首先,要踐行以義為先的指導思想。多邊開發機構幫助欠發達國家發展,是造福人類的大義。亞投行作為推動亞洲基礎設施發展的開發性金融機構,必須首先明確真正幫助發展的指導思想。這既將指導亞投行未來該做什么,不做什么,又是亞投行存在的根本。
綜觀世界范圍內的多邊開發機構,在真正幫助發展中國家發展方面似乎總不能盡得要領。其根源在于“義”的指導思想出了問題。它們總是將提供發展支持與給這些國家開“發展藥方”兩者捆綁起來。具體到基建等投融資領域,則表現為單純的用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等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和方法來衡量投資價值,很少考慮發展中國家的具體情況和特點。多邊開發機構總試圖用西方的發展“模子”來塑造發展中國家,勢必飽受指責,自身愿景難以落實。同時發展中國家不少真正有益于發展的好項目也得不到投資,“零和博弈”頻發。
對亞投行而言,“義”必須不落新自由主義窠臼,要形成一整套兼容國際經驗與亞洲實際,推動施援者和受援者利益融合,幫助亞洲發展中經濟體實現基礎設施的完善、升級、連通,進而帶動亞洲地區整體向前進的理念和愿景。具體而言,就是要形成亞洲發展中國家易學、可用、習慣、高效的基礎設施發展套路,使亞投行的資金真正用在利于這些國家發展的刀刃上,使貸款在基礎設施項目上活起來,使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融資的幫助延伸下去,幫助建立一套投資、運營、資金循環的機制,使亞投行的成功同時成為亞洲的成功。離開這一點,亞投行就會失去靈魂、“泯于眾人”,吸引力也將大打折扣。
目前,亞投行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分處五大洲,既有域內國家(37國)又有域外國家(20國),有重要的出資國家,也有亟待發展基礎設施的國家。各方對亞投行的期待不同、理念各異,這屬自然。要使各國齊努力,做好溝通很重要。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的發展過程及特點比較了解;中國又是與世行等多邊開發機構及相關發達國家開展發展合作最成功的國家之一,對開發合作的一般原則比較熟悉。這兩者的結合,可以使中國30多年發展的總體經驗和具體項目心得成為亞投行運作指導思想的若干范本。同時,中國將是亞投行最大出資國,也將有義務做好不同發展理念的溝通者、不同發展話語體系的翻譯者、各成員國利益的協調者、集體行動的核心引領者,推動亞投行運營相關各方在利益共享的基礎上踐行以義為先。
其次,要提高專業性,謀定經營戰略。亞洲基礎設施建設市場廣闊。據亞洲開發銀行估計,2010~2020年間,亞洲發展中國家要維持現有增長水平,在基礎設施領域達到世界平均水平將至少需要8萬億美元投資。這既是亞投行發展的機遇,也是其挑戰。根據亞投行初步設想,該行法定資本將達1000億美元,初步認繳資本為500億美元左右。單就資金需求與供給的懸殊程度而言,可供亞投行籌劃、實施的投融資項目可觀。然而另一方面,若亞投行不能進一步準確定位細分市場,把好鋼用在刀刃上,一則將面臨廣種薄收的風險,二則龐大體量或將擠出亞洲基建投資的其他參與者,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自有資本,以及來自亞洲區域內外的私人資本,最終對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不利。因此,在正式運營前找準細分市場,確定何以盈利和以何盈利是亞投行做實的關鍵。
總體把握,亞投行找準盈利的細分市場宜做好三個方面工作。一是在亞洲整個區域,首先聚焦國家間基礎設施建設互聯互通項目,解決市場失靈難題。長期以來,亞洲國家之間的基礎設施聯通建設是短板,既是制約各國發展的瓶頸,也是區域經濟合作水平不高的原因之一。這既是“修路博弈”、利潤劣勢導致的市場失靈,也是新自由主義經濟發展理論無法解決的發展空白。亞投行似可由此入手,帶動亞洲基礎設施網絡化,降低國際經濟交往的交易成本,提升亞洲國家集群發展的規模效益。
二是在國家層面,亞投行投融資項目宜把基礎設施建設水平與一國所處的具體發展階段和經濟結構結合起來,使所投資的基建項目真正有利于降低這些國家經濟發展和結構轉型升級的交易成本。這需要亞投行以具體問題為導向,做足市場調研,摸清項目所在地最優企業規模、生產規模、市場范圍、交易復雜程度及其風險種類,立足現狀,做適合當地長遠發展的項目,照顧到當地對這些基礎設施的運營和維護能力。同時,亞投行也宜在項目選擇上有所取舍,盡可能避免對私人投資的擠出效應。既不急功近利,與私人投資爭奪難度低、回報高的基建項目融資;也需照顧銀行自身盈利要求,長遠運籌難度大、盈利預期過低項目,做亞洲基礎設施建設的中堅力量。
三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政府參與力度大、市場化程度不高,這既是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普遍特點,也是其他多邊開發機構在新自由主義思想和華盛頓共識指導下搞市場原教旨主義發展援助所不能逾越的普遍障礙。然而,在發展中國家特有的發展階段上,政府推動發展的作用不可忽視,甚至是優勢之一。因此,亞投行要超越既有多邊開發機構,勢必要重構適合亞洲區域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融資評估分析體系和風險防范框架,將政府的角色和作用納入視野,既要消化吸收國際通行的評估規則和套路,又要融入發展中國家特色。要實現這一點,需要做通亞投行內部各成員國和項目所在國兩方面的工作。
最后,要發展并處理好與現有多邊開發機構關系。在絕大多數領域,亞投行若能做大做強,也是站在這些機構肩膀上的結果。鑒此,亞投行宜秉持開放的態度與其他多邊開發機構構建良性競合關系。
一是辯證看待其他多邊開發機構訴求,汲取其歷史經驗。例如,過去幾十年西方各國政府在多邊機構的談判內容被要求長期保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外部關系董事托馬斯·道森曾謔稱,其職業生涯的前25年一直為協助各國部長們隱瞞事實真相而奔波。而現在各方卻要求亞投行立刻實現高標準、透明化,并將其作為開展合作的前提。這一方面可視為既有多邊機構要撤掉亞投行的發展之梯,另一方面,政策不透明導致不少項目遇阻也確是這些機構長期以來吞下的苦果,以及與亞投行開展合作的障礙。
二是積極與既有多邊機構開展合作,擴大后發優勢。目前亞投行仍處在籌建階段,必然缺乏運營、管理經驗。即使未來開始正式運作,要形成亞投行獨特的經營套路和打法也需要長期積累。現有多邊開發機構長期運營,積累了廣泛而深入的經營網絡、人脈關系、項目資源。在那些全球通行的基礎性規則上,亞投行完全可以秉持拿來主義的開放態度,通過運營管理協調、溝通、交流,甚至在具體項目上開展合作,以積累相關經驗。這既利于亞投行發揮后發優勢實現跨越式成長,也使之有更多精力和空間形成自身特色。
三是理性對待良性競爭。在5月初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亞行行長中尾武彥即表示亞行80%的項目與基建投資相關,未來增資也將大力發展基建項目。由此可見,亞投行作為多邊開發領域的后來者,盡管極具特色和專業性,也將難免與既有機構競爭。這一方面需要亞投行理性對待競爭,并由此激發出創新動力。另一方面,既有全球性多邊開發機構行為準則仍主要以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劃線,短期還難以改變。這也需要亞投行在不斷發展的過程中摸索經驗,并參與到全球多邊開發機構新行為準則的制定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