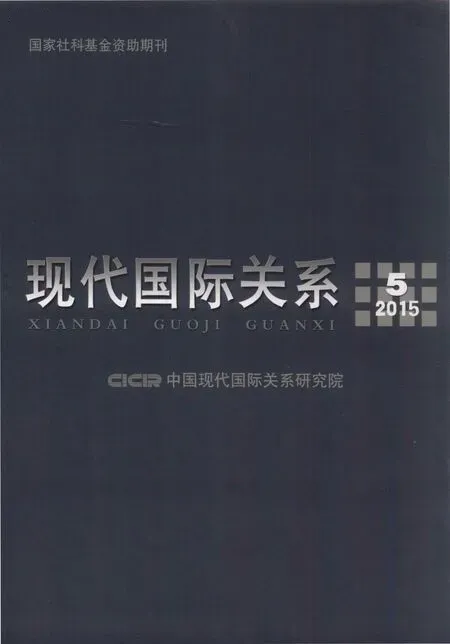歐洲加入亞投行的原因和影響探析
徐剛 司文 陳璐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世界經濟研究所助理研究員)
在亞投行的20個域外意向創始成員國中,歐洲國家占了絕對多數①俄羅斯身份特殊,本文暫定其將以亞洲身份加入亞投行。。自2015年3月12日英國公開表達加入意向后,歐洲多國一改之前的猶豫觀望,到4月15日累計有德、法、意、荷、盧等17國成為意向創始成員國,近半歐盟國家加入其中。從加入時點看,如此多國家選擇在截止日期(3月31日)前“沖刺加入”看似有集體狂熱之嫌,但實際并非草率之舉,而是經深思熟慮后做出的戰略決策,反映出歐洲對世界秩序、現實利益和治理規則等重大問題的思考與判斷。
首先,歐洲選擇“擁抱”亞投行,是基于其對未來世界經濟秩序演變趨勢的戰略判斷,反映出其試圖維持并鞏固自身地位和影響的努力。在本輪金融危機推動下,當前世界經濟格局正快速分化重組,發達世界中美、歐、日“三足鼎立”正演變為美“一枝獨秀”;而在中、印等新興大國帶領下,世界經濟版圖“東升西降”的勢頭仍在繼續,全球化正進入由新興大國驅動的新階段,并未因近年來新興經濟體群體性下滑而受挫。歐洲是當今世界多邊主義秩序的重要倡議者和塑造者,面對愈加明顯的世界經濟多極化趨勢和所謂的“經濟權力東移”,歡迎大于排斥,愿意承擔起改革和塑造未來世界秩序的責任。
對歐洲而言,其自身也面臨重要關口。過去幾十年歐洲一體化取得長足進展,形成了一個在經濟實力上足以匹敵超級大國的歐洲聯盟。借助七國集團(G7)、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治理機制和組織,歐洲事實上實現了與美國“共治”世界經濟的局面。但金融危機以來,“美歐共治”模式的根基發生動搖。一方面是歐洲一體化面臨不進則退、前功盡棄的重大風險。受困于歐債危機和自身結構性問題,歐洲經濟的“病夫”形象凸顯,歐盟內部成員國沖突不斷,歐元區解體風險若隱若現,對世界經濟的影響力日漸式微。為擺脫困境、避免被邊緣化,內生動力不足的歐洲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注重借助外力,尤其是借重中國崛起。另一方面,歐洲對當前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經濟治理體系的信心正在動搖。美國在危機中“自掃門前雪”、“落井下石”的做法令不少歐洲國家深感失望。美不但少有援手,而且美信用評級機構和智庫學者對歐洲國家信用和歐元前景的持續唱衰成為歐債危機遷延不絕的重要誘因。作為戰后國際經濟、金融秩序的制定者之一,歐洲對美國不斷逼迫其讓渡在國際經濟、金融體系中的代表權給新興經濟體,而美自身卻始終保留在世界銀行和IMF中的一票否決權的做法深感不滿。美歐聯手啟動的意在爭奪國際經貿規則制定主導權的“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關系協定”(TTIP)也囿于雙方在投資爭端解決機制、食品安全等方面根深蒂固的分歧,在歐洲民眾高漲的抗議聲中陷入停滯。歐洲正逐漸認識到,當前國際經濟秩序已難以完全代表歐洲利益,歐洲必須加速構建美國之外的其他支點來支撐自身的影響力,擁有極大經濟潛力和活力的亞洲無疑是最佳選擇。近年來歐洲力推的全球自貿區戰略中,亞洲國家往往成為其布局重點。面對亞投行提供的與亞洲國家深度合作的機會,歐洲各國的熱情回應自然在情理之中。
其次,這也是歐洲基于現實經濟利益的理性決定。經歷金融危機和債務危機雙重打擊后,歐洲經濟復蘇之路荊棘遍布、風險交織。2013年歐元區經濟增速雖實現觸底反彈,但至今仍萎靡不振,在主要發達經濟體中位居末席。通縮、需求疲軟、企業減產、失業率高企形成惡性循環,超寬松貨幣政策也未能救歐洲經濟于水火,結構性改革更是步履維艱。尋找新經濟增長點、刺激投資和需求已成多數歐洲國家當前的首要目標。
在此背景下,亞投行的出現應時應景,符合歐洲國家多方面經濟訴求。其一,提高資本收益,拉動投資需求。藏富于民的歐洲并不缺乏資金,但因經濟環境低迷,投資回報率不高,私人資本活力未充分顯現。而亞洲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需求龐大,且優質項目多,可以提供良好的投資回報。其二,開拓出口市場,鞏固產業優勢。歐洲多國在基建相關產業方面優勢明顯,如德、法、意等國機械設備制造業發達,瑞典、挪威、芬蘭等國信息通訊、環保產業研發擁有世界一流水平。加入亞投行將為歐洲眾多擁有技術優勢的企業打開機會窗口,提供與亞洲內部同行競爭的機會,避免缺席此輪亞洲基建大潮,喪失商業利益和產業優勢地位。其三,拓展金融業務,鞏固金融地位。英國、瑞士、盧森堡、荷蘭等國金融實力雄厚,金融服務業在本國GDP中占很大比重。隨亞投行融資需求擴大,其可憑創始成員國身份在爭取債券發行等金融業務上占得先機。而亞投行也被看作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平臺。倫敦、法蘭克福、巴黎、盧森堡、瑞士已開始離岸人民幣清算中心爭奪戰,期望借助人民幣國際化帶來的機會增量進一步拓展金融版圖。英國財政大臣奧斯本還希望借此增進中國對倫敦金融城的投資,鞏固倫敦金融中心地位。其四,謀求更廣闊的經濟合作空間。亞投行是中國“一帶一路”戰略的重要工具,而“一帶一路”的投資范圍和領域更為廣闊,蘊含投資機會更多。加入亞投行無疑可為今后參與其他“一帶一路”項目贏得更多機會。亞洲是世界經濟最具活力的地區,加入亞投行有利于歐洲國家深化歐亞經貿聯系,分享亞洲發展紅利,推動復蘇進程。
誠然,政治與經濟上的“有利可圖”使得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的腳步“根本停不下來”,但同時英、法、德等歐洲大國的加入對亞投行來說亦是“有利可圖”。最為直觀的影響便是歐洲國家加入亞投行所形成的巨大示范效應。自英國敲開亞投行大門后,一時間加入申請者蜂擁而至,短短半個多月時間內激增30個,極大提高了亞投行的代表性、多元化程度以及全球號召力。4月28日,57個意向創始成員國代表在最終名單確定后首次齊聚北京,共同商討亞投行組織架構與章程,亞投行籌建將正式進入實質性博弈階段,歐洲或在其中發揮重要影響。
這一階段,歐洲之于亞投行可謂是“有予有取”。“予”的方面在于,歐洲的加盟,不但可以為亞投行帶來一筆可觀的資金支持,而且還將帶來一系列的人才、智力和經驗支持。亞投行雖使中國第一次在真正意義上成為一個多邊國際機構的領導者,但中國仍顯年輕且經驗不足,這方面歐洲無疑更具發言權。在治理機制上,歐洲歷來倡導“多邊主義”,對多邊合作與治理有著創造性的發散思維,擁有豐富的協調與談判經驗。對于如何治理國際機構,以及在多國間有效協調與溝通,歐洲可以為亞投行提供寶貴的經驗支持。在項目運營上,歐洲對復雜投資項目的管理制度、符合國際標準的決策方式、項目投資回報預估等方面的經驗對亞投行的業務開展來說也值得借鑒。
“取”的方面在于,歐洲或將對在亞投行的話語權提出更大訴求,為亞投行的運營打造“歐洲化”的標準,從而事實上爭奪對亞投行事務的主導權。按照原有規劃,亞投行中域內國家占據投票權75%的份額,域外國家只能占到25%。因此,即便中國已公開表示一票否決權對亞投行來說是偽命題,但作為發起國、同時經濟體量又最大,中國獲得實質性否決權的可能很大。但大量歐洲國家,特別是歐洲主要經濟體的加入或將改變這一情況,要求提高域外國家所占份額的呼聲已經出現,這可能將從根本沖擊到中國對亞投行的實際掌控能力。在亞投行的運營和規則制定上,歐洲的豐富經驗雖有助于推進談判,但也為歐洲在亞投行中塞入更多“私貨”提供了優勢,“喧賓奪主”的風險不容忽視。倫敦市長首席經濟顧問李籟思的一段話或可表示歐洲的普遍訴求和雄心壯志:“世界經濟的發展有四個主要驅動因素,包括軟實力、地緣政治硬實力、經濟和金融的驅動力以及政策制定機構的驅動力。英國須確保在亞投行這個新的政策制定機構占據有利地位,如同當年在IMF和世界銀行占據有利地位一樣。”可以預計,在亞投行的運營規章和項目規則談判中,歐洲各國必將不遺余力地貫徹落實其高水平的環保、社會、透明度等相關標準,塑造亞投行發展方向,力圖獲取對亞投行事務的主導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