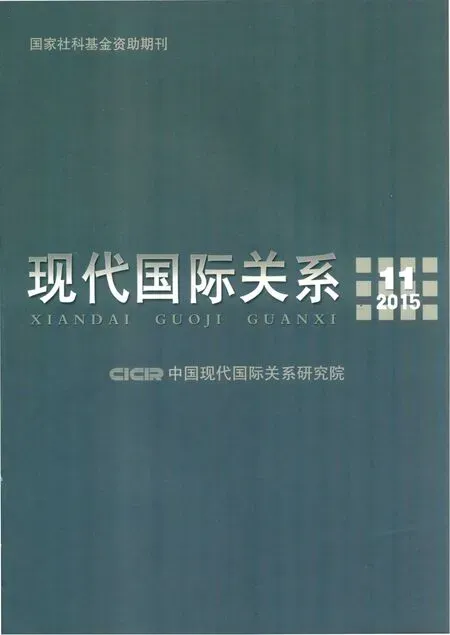“習近平訪美與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研討會綜述
劉博文
為深入探討習近平主席訪美的戰略意義,展望未來中美關系的戰略走向,2015年10月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研究中心主辦、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和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協辦、題為“習近平訪美與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的研討會在中國人民大學召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外交學院、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等單位的十余位專家學者展開討論。現將本次研討會的主要觀點綜述如下。
一、關于習近平主席訪美的成果和意義。第一,雙方進行戰略溝通與戰略意圖的再確認。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達巍認為,習近平主席此次訪美的最重要成果是增信釋疑,在近年來的外交戰略調整之后,與美國在三個方面形成了再確認:其一是確認了中美關系的重要性,重申中美關系仍然是中國外交的優先方向;其二是確認了中國對現行國際體系的態度,表示中國會支持現行體系,不會另起爐灶;其三是美國確認了將繼續接納中國的崛起,也接納中國改革和擴大這個體系的做法。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副所長倪峰認為,此次訪問的最重要收獲應該是一個“形而上”的成果,即在中美關系處在關鍵和敏感時期的大背景下,兩國最高領導人共同向世界展示了中美兩個大國要管控分歧、擴大合作、相向而行的強烈信號。北京大學中美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執行副主任王棟指出,在此次高訪中,雙方強調了戰略溝通的重要性,美方表示歡迎強大、繁榮、穩定、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中方則表示尊重美國在亞太地區的傳統影響和現實利益,歡迎美國在地區事務中發揮積極的建設性作用,體現了雙方在戰略意圖高度的相互保證。
第二,網絡安全領域。國務院參事、中國人民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時殷弘指出,根據中國的原則性建議,中美兩國造就了一個非常簡單、非常籠統但是前所未有的關于網絡問題的協議,在非常對立但非常重要的網絡安全領域造就了有限的突破,成為兩國政府進一步就此進行對話和談判的起點,意義極為重要。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現代國際關系》主編王文峰認為,雖然網絡安全方面的成果門檻較低,但這種操作層面的危機管控機制非常重要,對于雙方未來更進一步戰略互信的建立、更進一步危機管控的形成意義重大。王棟指出,中美雙方在網絡安全領域的成果體現在許多實際具體的措施上,包括建立高級專家小組、推動共同制定網絡空間行為準則、建立打擊網絡犯罪的高級別聯合對話機制、承諾均不從事或支持網絡竊取知識產權等。
第三,公共外交方面。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副院長王莉麗認為,習近平主席在西雅圖的訪問行程充分體現了在公共外交方面的考慮和設計,從對波音公司、微軟公司的企業外交,到對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的利益集團外交,再到習近平訪問林肯中學、彭麗媛與米歇爾為大熊貓命名等文化外交,充分展現了中國多元化、多領域、全方位的對美公共外交。
第四,經濟金融、氣候變化、地區安全等其他領域。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董裕平指出,在此次高訪發布的49項成果清單當中,廣義來講一半以上涉及經濟金融,體現了經濟領域作為中美關系“壓艙石”的重要作用。時殷弘指出,中國所做出的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重要承諾也將有利于中國國內發展模式的轉變和生態的較好發展。王棟認為,中國領導人此次關于中美兩國在南海問題上有諸多共同利益的表述,為緩解中美兩國間的緊張和對抗態勢創造了條件。
二、關于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關于習近平訪美之后的中美關系走向,諸多與會學者給出了自己的判斷和預測。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王文認為,冷戰后中美關系主戰場的博弈可以劃分為三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1991-2001年,中美之間的博弈基本圍繞中國國內議題;第二個時期是2001-2012年,博弈的主戰場集中在中國周邊;第三個時期是2013年之后,中美之間的博弈呈現全球化趨勢,此次訪問對網絡、氣候等問題的關注進一步顯示了中美博弈的全球性特征。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金燦榮認為,由于中美關系中的老問題很難得到根本性解決,所以永遠不宜對中美關系做過高的期待,中美之間的矛盾與問題只能用高超的外交技巧和對話機制加以控制,短期內兩國間的矛盾可能會增多,而如果中國能在未來保持強大穩固的態勢,美國則很可能面臨真正痛苦的戰略抉擇。王文峰指出,真正的戰略穩定應是一種雙方對戰略關系的基本狀態和態勢感到基本滿意的平衡狀態,由于中美實力對比仍然呈現比較明顯的變化態勢,兩國距離戰略穩定的狀態仍比較遙遠,未來兩國經濟各自發展的態勢以及兩國實力對比對雙方的戰略認識會有非常重要的影響。倪峰提出,中美關系的未來走向可以從中美兩國政府對此次訪問認知的三個溫差中窺見端倪:第一個溫差在于兩國政府所設定目標的差異,中國政府將構建中美新型大國關系作為一個更為宏大長遠的目標,美國政府則更多立足于通過此次訪問建立更加穩定的工作關系;第二個溫差在于兩國政府側重點的差異,中國政府更多的希望通過擴大合作的形式來穩定中美關系,美國政府則更多的希望通過此次訪問解決中美之間具體的問題;第三個溫差在于對待此次訪問的態度,中國方面是將官員、學者、媒體各種力量調動起來的高度關注,而美國的奧巴馬政府則是“心有旁騖”,被其他更緊迫的問題牽扯了注意力。達巍指出,從2013年的兩軍關系、2014年的氣候問題,到今年的網絡安全,中美關系里出現了一種新的工作方法,就是化困難點為合作點,把中美關系中最差、最弱的一個點變成中美關系的亮點,這種變化很大程度上體現了中國的思想解放,但美國方面為何較少出現這種思想轉變值得思考。王莉麗指出了中美經濟關系的三個趨勢性變化:貿易關系由過去的垂直分工向水平分工發展;投資關系從單向流動向雙向流動轉變;科技創新由中國對美國的單純技術模仿轉向自主創新。
針對習近平訪美結束后出現的近期重要事態,尤其是10月5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rans-Pacific Partnership,TPP)基本協議的達成,部分專家學者發表了自己的觀點。時殷弘認為,美國奧巴馬政府推動TPP一是為了振興美國經濟,二是為了主導區域甚至全球貿易體系的新規則體系,目前中國在貿易的高標準規則的執行能力方面顯然是弱者,所以中國深化改革的重要性顯得尤為突出。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世界經濟與國際政治中心主任雷達認為,美國對TPP的推動表明,美國是試圖通過一體化方式創造出貿易效應來刺激全球總需求水平的提高,同時利用TPP當中創造的高標準貿易制度作為未來建立世界貿易體系的談判籌碼。他進一步指出,從經濟依存度來說,中國理應成為TPP的重要成員,美國將中國排除在外的做法體現出,美國的對華政策沒有將經濟因素放在特別重要的位置,非經濟因素仍占據主導地位。
三、關于中國對美戰略的思考。基于中美關系的現狀和可能的未來走向,與會學者圍繞中國的對美戰略提出了許多觀點和建議。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副院長方長平提出,在處理中美關系時,需要注意四個方面的問題:一是在擴大共同利益的同時要直面分歧和沖突點,因為共同利益往往體現在功能性議題上,分歧和沖突往往體現在戰略性議題上,二者具有不同屬性,功能性領域的共識難以從根本上消除戰略領域的結構性矛盾;二是要注意區別中美之間的戰略性沖突和認知沖突,避免對對方戰略意圖的誤解;三是要思考中美之間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是客觀存在還是人為建構的,避免形成自我實現的預言;四是中美之間要構筑新型大國關系,首先是要做新型大國,而新型大國應該有什么樣的特質,則需要學界在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做更深入的思考。外交學院教授、《外交評論》執行主編陳志瑞認為,要對中美關系的發展和前景,對中國所處的地位和立場有清醒的認識,要做大做強自己,改變自己的觀念,在懷有大國抱負時不要為其所累。此外,他還從學術研究的角度,強調沒有好的學理研究就沒有好的政策分析,沒有好的政策分析就沒有好的決策,呼吁學界更加深入地研究沖突與合作的關系、大國抱負及合作共贏等問題,更加重視美國國別研究的質量問題,做更多細致扎實的研究,做到知己知彼,從而推動中美關系的良性健康發展。清華大學國際關系系副主任孫學峰指出了周邊國家與中美關系的重要戰略關聯,強調重視第三方因素對中美關系的影響。他指出,中國的周邊國家可以分為四種類型:第一類是總體比較富強的美國安全保護國,如日本、菲律賓;第二類是總體比較富強的非美國安全保護國,如印度、越南;第三類是總體比較接受中國的美國安全伙伴,如韓國、泰國;第四類是總體比較接受中國的非美國安全伙伴,如馬來西亞、中亞國家。針對不同類型的周邊國家群體,中國可以采取不同的策略組合,以穩定同周邊國家的關系,進而穩定中美關系。時殷弘強調,中國在很多方面不宜過于唱高調,不能將一些事情講得太高、太浪漫、太籠統,以免引起言與行之間的差距。要從實踐出發,將一些高調適度地降下來,并把自身的實際問題與實際行動聯系起來,以增強自身的可信性,使真正重要利益所需的行動不會受自己過分高調的牽制和約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