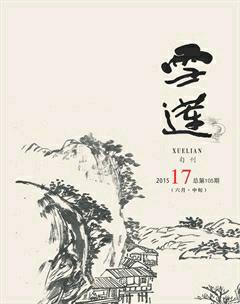簡析《追風箏的人》中的孤獨旅者——阿米爾
毛會娟
【摘 ?要】《追風箏的人》是胡塞尼的一部自傳式小說,以阿米爾和哈桑的友誼、親情為線索,以文化、社會和民族為視角,展示了阿米爾的心路成長的孤獨旅程——從放風箏的人成為“為你,千千萬萬遍”的追風箏的人,發人深省,震撼人心。
【關鍵詞】追風箏的人;孤獨旅者;救贖;回歸
《追風箏的人》(The Kite Runner)是阿富汗裔美籍作家卡勒德·胡賽尼(Khaled Hosseini)的處女作,小說以阿富汗富家少年普什圖人阿米爾和其仆人哈扎拉人哈桑之間的友誼和親情為線索,講述了阿米爾的從背叛走上回歸、救贖的孤獨心路成長歷程。
一、少年阿米爾——優越心理的孤獨者
哈桑與阿米爾年紀相仿,一起長大。“哈桑與他喝過同樣的乳汁,他們在同一個院子里的同一片草坪上邁出了第一步,在同一個屋檐下,說出第一個字,阿米爾說的是‘爸爸,哈桑說的是‘阿米爾”。但在阿米爾心中,哈桑從始至終不是他的朋友。在一次風箏比賽中,為了幫他追回獲勝的風箏,哈桑被阿塞夫等人毒打凌辱、冷嘲熱諷道:“在你為他獻身之前,你想過嗎?他會為你獻身嗎?難道你沒有覺得奇怪,為什么他跟客人玩總不喊上你?為什么他總在沒人的時候才理睬你?我告訴你為什么,哈扎拉人。因為對他來說,你什么都不是,你只是一只丑陋的寵物,一種無聊的時候可以玩的東西,一種發怒的時候可以踢開的東西。別欺騙自己了,別以為你意味著更多”。然而,哈桑還是紅著臉,堅持說:“阿米爾少爺跟我是朋友。”但這并沒有喚起袖手旁觀的阿米爾挺身而出,相反,為了自保,他跑開了。受到毒打和凌辱之后,哈桑走過來,阿米爾第一眼看到的是那只能讓他受到父親贊賞的風箏,“哈桑的長袍沾滿泥土,襯衫領子下面開裂,哈桑站著,雙腿搖搖晃晃,似乎隨時都會倒下,接著他站穩了,把風箏遞給阿米爾”。而阿米爾假裝沒有聽到哈桑委屈的哽咽,沒有看到哈桑雙腿之間淌下的血滴。為了獲得心理上的逃逸和安全,更是想方設法將哈桑趕走。為了阿米爾,哈桑默認一切,離開了阿米爾的家。他無時不刻都在用實際行動詮釋對阿米爾的忠誠,捍衛對阿米爾的尊敬——“為你,千千萬萬遍”。相對哈桑的忘我與無私付出,阿米爾是孤獨的,他的孤獨源自于他的優越,是普什圖人,有一個令人羨慕的父親。物質、身份、地位帶來的優越非但沒有掩飾他的孤獨,卻加劇了他的自私、懦弱,使他更加孤獨。
二、青年阿米爾——文化沖突的孤獨者
戰爭的爆發使阿米爾和父親不得不背井離鄉,“我永遠不會忘記那聲回蕩的槍響,不會忘記那一道閃光和濺出的血紅”,“米格戰斗機在頭頂轟鳴,斷斷續續的槍聲,旁邊有驢子昂昂叫,一陣鈴鐺的聲音和羊群的綿綿叫……黑暗中嬰孩的哭嚎,汽油、嘔吐物和糞便的臭味”。此時,逃亡、移居成為了一種特殊的求生方式,阿米爾開始了文化沖突的孤獨心路歷程。初到美國的阿米爾認為這是有一個全新的起點和開始,可以埋葬往事,沖淡過去。“美國是河流,奔騰前進,往事無人提起。我可以進進這條大川,讓自己的罪惡沉在最深處,讓流水把我帶往遠方”。剛到美國的阿米爾滿懷希望開始了全新的生活,收獲了愛情、事業,成為醫生,后來成為作家。但他并不能真正與過去徹底告別:首先,來自父親的影響,作為阿米爾心目中膜拜的榜樣,父親在生病期間拒絕俄羅斯醫生為他看病,反映了他對祖國的眷戀,也喚醒了阿米爾對阿富汗的思鄉之情;其次,雖然生活在阿富汗人的聚居圈,但無法真正完全融入到美國社會里,他被逼而來,寄居的痛苦和孤獨以及美國社會的排斥和沖擊時刻纏繞著他。面對這些壓力,阿米爾只能獨自默默忍受。從文化層面來講,阿米爾的身份是尷尬的,原本作為純粹的阿富汗人,具有對民族優劣血統認同和傳統的宗教文化信仰,隨著移居,為了生存而變得不再完整和純潔,形成了一種“民族身份創傷”。例如,同樣來自阿富汗的他的妻子,在結婚前已經不再是處女,這在今天的阿富汗也是不能被容忍的,甚至有被處死的可能,但是,身在美國社會,阿米爾不得不選擇認同美國文化,背離自己的傳統文化,成為身處矛盾和背叛中的文化“失落者”。文化滲透和融合的沖擊過程在阿米爾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既有阿富汗文化剝離的失落感,又有美國文化滲入的背叛感。可以說,從踏上美國國土的那一刻,注定了他會淪為生存在兩種文化邊緣的人,成為文化沖突中的孤獨者。
三、中年阿米爾——回歸救贖的孤獨者
作為阿富汗人,并且在阿富汗度過了多年的美好童年時光,阿富汗終究是阿米爾揮之不去的心靈故鄉。在美國待的時間愈久,鄉愁愈濃,重歸阿富汗的愿望就愈強烈。在接到拉辛汗從巴基斯坦打來的電話后,他也曾一度猶豫,內心充滿矛盾,拉辛汗那句“來吧,這兒又再次成為好人的路”讓他決心踏上回歸救贖的旅程。“我知道自己要盡快起程,我害怕自己會改變主意,我害怕自己會猶豫不決,瞻前顧后,寢食難安,尋找理由,說服自己不要前去。我害怕來自美國生活的誘惑會將我拉回去,而我再也不會趟進這條大河,讓自己遺忘,讓這幾天知道的一切沉在水底。我害怕河水將我沖走,將我沖離那些當仁不讓的責任,沖離哈桑,沖離那正在召喚我的往事,沖離最后一次贖罪的機會”。見到拉辛汗后,當他得知哈桑為了保護自己的家園而被塔利班殘忍槍殺,而且他是自己同父異母的兄弟時,阿米爾內心更加悔恨和愧疚,他終于明白了父親那句話“哈桑就在這里陪著我們,他屬于這里,這里是他的家,我們是他的家人”背后的含義。哈桑已死,哈桑的兒子索拉博成為了阿米爾唯一救贖的目標和希望。“哈桑曾經深愛過我,以前無人那樣待我,日后也永遠不會有,他已經走了,但他的一部分還在,在喀布爾。”當時,成為孤兒的索拉博被已經成為塔利班份子的阿塞夫從孤兒院買走并控制,成為玩偶,如同他的父親一樣被玩弄和凌辱。此時,兒時哈桑的遭遇再次在阿米爾腦中重現,這一次,他選擇的不是無動于衷和逃避,而是挺身而出、奮力搏斗。他的努力讓人動容,使人感動。在成功救出索拉博后,阿米爾將他帶到美國,并收養了他,成為了為他“追風箏的人”,并且和哈桑一樣,要“為你,千千萬萬遍”。由此可見,阿米爾救贖的結果是成功的,但過程是痛苦的,需要勇氣和堅持,忍受孤獨。
四、結論
《追風箏的人》中,阿米爾的心路歷程是艱辛與孤獨的,這種感受源自生命賦予的責任和重托,也是對生存環境的屈從與折服。對阿米爾來說,風箏象征著親情、友情、真摯、善良等美好的東西,是他人性中不可缺少的部分。追風箏的過程,可以視為他自我完善和救贖的孤獨心路歷程。同時,阿米爾自身也是一只“風箏”,一生漂泊,跌宕起伏,無所依附,孤獨飛翔。通過阿米爾孤獨的救贖過程,使讀者能夠在閱讀的過程中被人的精神及人類特有的行為所感染和震撼,并會對自己成長過程中存在或發現的自身或社會問題進行反思,引發情感共鳴。
參考文獻:
[1][美]卡勒德·胡賽尼著,李繼宏譯.追風箏的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