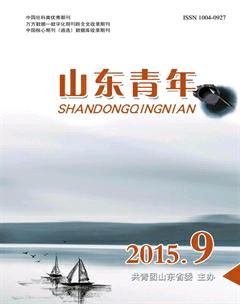節儉
管吉哲
摘要:從中國消費思想變遷的整體脈絡上看,“崇儉黜奢”始終是中國傳統消費觀念的核心價值取向。傳統文化奉節儉為美德,包含克己之儉、義禮之儉、養德之儉、興邦之儉四個維度的價值。對傳統消費觀念價值取向的探究對構建適合當代中國國情的新型消費倫理具有寶貴的借鑒意義。
關鍵詞:節儉;傳統消費觀念;美德
中國傳統文化崇尚節儉,從中國消費思想變遷的整體脈絡上看,“崇儉黜奢”始終是其思想的主流。其表現在消費領域,即以節儉為榮、以浪費為恥的崇儉消費觀念;表現在道德層面,即以節儉為美德,通過節制欲望,達到修身養性、養德興邦的作用。考察中國傳統消費觀念就勢必要厘清中國傳統節儉觀念之價值追求。
一、傳統消費觀念的崇儉價值取向
傳統節儉觀圍繞先秦“儉奢之爭”、“義利之辨”等問題確立并發展起來,自漢以后成為封建社會的正統價值觀。長久以來,節儉作為一種美德規范著傳統中國社會人們的生活。翻開古代典籍,不難發現先賢們有關節儉價值的深刻思考。
(一)義禮之儉。“義利之辨”是中國傳統思想的核心問題,“義”關注人對崇高道德境界的追求,“利”則代表人對物質利益的欲求。中國傳統文化基本堅持了重義輕利的價值取向,消費領域亦是如此。“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論語·里仁》)相比富貴與否,孔子更關注逐利方式是否正當。對財富無論追求還是享受,他都強調主觀動機的合道德性,輕視獲利多少的客觀實際。因此當義利不可兼得時,他說“不義而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論語·述而》)孔子對名利的淡泊源于他對生活樂趣的獨到見解:“士志于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論語·里仁》)他不在乎衣食是否華美;“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論語·顏淵》)他也不追求奢華的生活;“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論語·述而》)即使從清貧的生活中他依然能體味到生活的樂趣。孟子也說:“飽食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于禽獸”。(《孟子·滕文公上》)他將人分為“大體”與“小體”,“大體”指人之德性,“小體”指人之本能。“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為其養小以失大也”。(《孟子·告子上》)若只重物質享受而不重德性追求便會“養小失大”。以上反映出傳統節儉觀自身始終秉持“用不傷義”的價值原則,即相比對物質利益的追求人們更注重對精神境界的提高。而人們在實踐節儉的過程中始終堅持的另一個原則是“儉不違禮”。即“儉”并不是無原則絕對的,而是在其消費水準與地位尊卑相符的前提下盡量節儉,這實際是強調依照社會階級地位的高下來區分不同消費者的消費品質與數量。正如孔子說,“禮,與其奢也,寧儉。”(《論語·八佾》)當季氏的消費標準逾越了他的等級,孔子驚呼“八佾舞于庭,是可忍,孰不可忍。”(《論語·八佾》)另外孔子在祭祖時反對節省獻祭用的羔羊,認為這是“失禮”行為;顏淵死后,反對厚葬顏淵,認為這不符合顏淵的等級身份。這些事例說明孔子既反對逾越等級、奢靡無度的消費方式又反對因過分節儉而不符合等級身份的失禮行為,這實際是用身份等級替代評價儉奢的客觀經濟標準,是種等級消費觀。
(二)克己之儉。傳統節儉觀認為“克己”作為一種價值追求,可以通過節儉的生活方式來實現。荀子曾說,“饑而欲食,寒而欲暖,勞而欲息,好利而惡害”、“食欲有芻豢,衣欲有文繡,行欲有輿馬”。(《荀子·榮辱》)欲望,特別是對美食美物的貪欲乃人之本性,人皆有之。有些情欲合理,利己利人;有些不合理,害己害人。可是“理智無力;欲無眼”[1],欲望本身并沒有善惡評價標準。缺乏道德規范與價值指引、一味逐欲的活動會讓人類陷入混亂。誠如老子所言:“五色使人目盲,五味使人口爽,五音使人耳聾,馳騁田獵使人心發狂,難得之貨使人行妨。”(《老子·第十二章》)所以他告誡我們“禍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老子·第四十六章》)對貪欲的恐懼催生了對貪欲的克制,為了避免縱欲引起的災禍,我們就必須“克己”以管理自己的情欲,但“克己”如何實現?“欲雖不可盡,可以近盡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荀子·正名》)荀子認為雖然欲望不能根除,但是通過簡樸節制的生活便可以實現對欲望的控制。其實先賢們很早就看到了“儉”、“奢”同欲望的關系:“侈則多欲”,“多欲則貪慕富貴,枉道速揚人在物我關系、消費生活中的主體地位;追求“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樸真生活境界;體現了對人類生存發展狀態的理性關懷。禍”、“多欲則多求妄用,敗家喪身,是以居官必賄,居鄉必盜。”(《訓儉示康》)欲壑難填,奢侈的行為會刺激人的貪欲,釀成災禍;而“儉則寡欲”,“寡欲則不役于物,可以直道而行”、“寡欲則能謹身節用,遠罪豐家”。(《訓儉示康》)節儉可以教人們克制不合理欲望,培養合理欲望,因此節儉的生活方式是人們克己制欲的應然之選。
(三)養德之儉。節儉不僅是一種消費觀念,古人更是以儉為德。一方面,節儉本身即是一種美德。子曰:“以約失之者鮮矣”(《論語·里仁》),朱熹也說“儉德極好,凡是儉則鮮失”(《朱子語類·卷一百二十五》),節儉即“節制”,節制內涵理性御己之意,因而“鮮失”。節儉也作“簡約”,提倡“見素抱樸”、簡約生活,以將精力用來追求更高的精神需要。孟子說“養心莫善于寡欲”(《孟子》),人的精神追求雖以一定的物質生活為基礎,但并不限于物質生活。相反,人若一味沉溺于聲色犬馬,便會消磨志向,喪失精神目標。因此,于志寧總結道:“克儉節用,實弘道之源;崇侈恣情,乃敗德之本。”(《舊唐書·于志寧傳》)。另一方面,節儉還是培養其他美德的手段。正所謂“靜以修身,儉以養德”(《誡子書》),“有道者皆由儉來也”。傳統道德中節儉總是同勤勞、貴生等美德緊密相連。一則,我們常說“勤儉”,“勤”與“儉”分別從生產、消費兩個環節對主體的經濟活動提出了道德要求。“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朱子家訓》),只有辛勤勞動方知勞動成果來之不易。勤勞教我們熱愛勞動,節儉教我們珍惜勞動成果;勤勞創造財富,節儉積累財富。再則,中國傳統注重養德貴生。何為“貴生”?“所謂貴生,亦即貴生賤物、重生輕物,也就是把自己分為‘生和‘物,而認為自己的生命貴于自己生命之外的東西,因而也就是自己最寶貴、最有價值的東西。”[2]“物”乃“生”外之物,生命質量的高低與占有物資的多寡并沒有必然聯系。過分的貪欲反而會使人役于物、累于形、害于生,導致生理、心理嚴重失衡,更甚者將危及自身乃至他人的生命,釀成悲劇。所以老子告誡我們:“名與身孰親?身與貨孰多?得與亡孰病?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故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老子·第四十四章》)。人只有常懷“節儉”之心,溯本清源、祛除物敝、保持身心和諧,方能知足、知止、生命長久。“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左傳》),儉乃大德、侈乃大惡,珍愛生命即要趨善避惡、“以儉德避難”(《易經》)。可見,通過節儉的生活提高德性修養,促進身心和諧乃是傳統節儉觀念的旨趣所在。endprint
(四)興邦之儉。“禁奢崇儉,美政也。”節儉既是美德又是“美政”。儒家很重視節儉對于裕民、富國的重要性。孔子說“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論語·學而》),并說“百姓足,君孰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顏淵》)他提出了通過節用而裕民,裕民而國富的美好治國愿景。荀子則更加明確的指出節儉對經濟發展的重要性,他說“足國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余。節用以禮,裕民以政。彼裕民,故多余”(《荀子·富國》);他也很注重節約資源、積累財富,因此他說“強本而節用,則天不能貧”(《荀子·天論》)。荀子還很推崇可持續消費:“節用御欲,收斂蓄藏以繼之也”(《荀子·榮辱》),節約開支是為了有備無患,保持生產生活的可持續性。但他也強調“天下尚儉而彌貧”,社會上各階層、各領域無差別的厲行節儉只能使人民更加貧困,是不可持續的。古人也很警惕“奢侈”對于社會和諧、國家安定的巨大破壞作用。李商隱曾說:“歷覽前賢國與家,成由勤儉敗由奢。”奢靡的行為輕則腐蝕人心、敗壞個人道德,重則破壞社會風尚、亡家亡國。“國侈則用費,用費則民貧,民貧則奸智生,奸智生則邪巧作。故奸邪之所生,生于匱不足;匱不足之所生,生于侈;侈之所生,生于毋度。”《管子·八觀》中認為奢靡的行為源于“毋度”,即人對自己行為的放縱。因此應當“審度量,節衣服,儉財用,禁侈泰”(同上),通過提倡節儉來杜絕浪費現象、整肅奢靡的不良風氣,此乃“國之急也”。
二、傳統消費觀念崇儉價值取向的當代困境
以上便是中國傳統消費觀念的崇儉價值取向。“義禮”從外,強調倫理綱常對儉行的規范;“克己”于內,重視儉德對人欲望的管理。“養德”從倫理角度,闡明節儉是個人修身養性的基礎;“興邦”從政治角度,將節儉提升到了持家治國的高度。可見傳統節儉觀對節儉價值的思考是立體、多元的。
當然,應當看到傳統消費思想“崇儉黜奢”的價值取向更多是出于對儉奢道德價值的判斷,而缺少經濟維度價值的追求與重視。它是“重義輕利”思想在消費領域的延伸,體現了傳統消費觀念重道德評價輕經濟評價的價值傾向,即相對于評價儉奢的客觀經濟標準,傳統文化更關注儉奢行為的合道德性。這一視角客觀上限制了人們對財富以及物質享受的合理追求,無力對當前社會多元化、個性化的消費方式構成有效道德辯護。
當前,我國消費革命方興未艾,信用消費、分期付款等許多嶄新的消費方式相繼涌現,超前消費等種種極具時代性的消費理念正日益被人們認可接受。傳統節儉觀念提倡節欲、儲蓄的單一消費理念已遠不能為諸多新穎的消費方式提供合理的道德辯護,一些不合傳統道德要求卻符合經濟發展需要的消費方式更超出了傳統文化的評價能力之外。傳統消費文化與社會實際消費生活相背離,崇儉消費態度與擴內需的經濟要求相背離,單一的評價角度與多元的消費方式相背離,這些都是當前社會“節儉悖論”的生動體現。這要求我們必須重新解讀傳統節儉文化,為現代消費倫理注入新的內涵。
[參考文獻]
[1] 馮友蘭.三松堂全集第四卷[M].河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6.518.
[2] 王海明.倫理學原理[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298.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