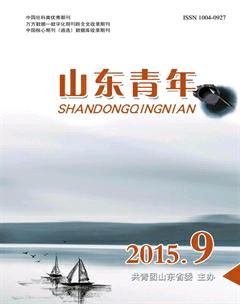淺論軍事立法技術的科學化
劉瓅黎
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了“科學立法、嚴格執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的新16字方針,這表明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已進入了新階段。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已經形成的今天,立法工作也從解決“有無”問題,轉變為解決“科學”問題。立法技術通常包括立法結構和立法語言兩大核心技術,是立法活動中所遵循的用以促使立法臻于科學化的方法和操作技巧,并從根本上決定執法、司法和守法工作能否順利展開。立法名稱和立法語言作為法律形式載體的兩大要素,不僅是衡量立法技術是否成熟的重要標準,同時也決定著法律內容本身是否合理。在我國,軍事部門法仍是一門年輕的學科,無論是立法名稱還是立法語言,在科學性標準上都有所欠缺,這在未來的軍事立法改革中應當引起足夠重視。
一、立法名稱的科學化
法律的名稱應當做到準確、精練、概括和規范。一般來說,某一法律文件的名稱包括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反映適用區域,第二部分反映主要內容,第三部分反映效力等級,因此,法律名稱的科學化通常決定著法律結構的科學化。目前看,我國的軍事法文件名稱存在問題較多。一是稱謂繁多。現在使用的法、條例、條令、概則、規定、規則、辦法、訓練大綱、標準,歷史上曾用的命令、訓令、布告、方法、意見等稱謂,共計超過了30種。如此繁多龐雜的稱謂,不僅容易使立法者抉擇不一,而且往往難以分辨它們的調整內容、效力等級,甚至難以辨認出某些文件是否屬于軍事法的范疇。二是等級不清。這又分為:1、不同的等級適用相同的名稱。如人大常委會制定的《軍官軍銜條例》屬于軍事法律,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制定的《現役士兵服役條例》是軍事行政法規, 但它們都稱之為“條例”。再比如,中央軍委制定的三大條令,空軍制定的飛行條令,海軍制定的艦艇條令,都稱為“條令”,但無法看出是哪一級立法機關制定的。2、相同的等級使用不同的名稱。比如,《征兵工作條例》《中國人民解放軍士官退出現役安置暫行辦法》與《飛行基本規則》都是國務院與中央軍委聯合制定的軍事行政法規, 卻分別稱為“條例”、“辦法”和“規則”。三是標準不明。在軍事法文件的諸多名稱中,每一種名稱確切的含義和使用時區分的標準是什么并沒有明確的標準。
2003年出臺的《軍事法規軍事規章條例》對軍事法規和規章的名稱使用做了統一規范。《條例》第62條明確:“軍事法規、軍事規章的名稱,應當準確反映其調整對象和效力等級。軍事法規的名稱為條令、條例、綱要、概則、規定、辦法。軍事規章的名稱為規定、規則、辦法、細則、標準等;除規范作戰行為的軍事規章可以稱“條令”外,軍事規章不得稱“條令”、“條例”。軍事法規和總部規章的名稱中通常應當冠有“中國人民解放軍”或者“軍隊”字樣;軍兵種、軍區規章的名稱中應當冠有制定機關的名稱。”但事實上,我國軍事立法主體包括全國人大、國務院及其部委、享有立法權的地方權力機關及其常務委員會和地方人民政府,以及中央軍事委員會、軍委各總部、各軍兵種、各大軍區等軍事機關,數量較大,同時,各個立法主體所制定的軍事法律文件形式除了軍事法規和軍事規章,還包括上位的軍事基本法律及下位的具有軍事法規范性質的文件(又稱準軍事規章)。不同主體之間信息不相互公開,上傳下達也并不及時透明,更何況《條例》所規定的名稱規范僅適用軍事法規和規章,對其他層級的軍事法律文件“鞭長莫及”,這就導致不同位階或是同一位階的軍事法之間名稱不規范的現象仍很常見。筆者認為,解決這一問題,一是要在未來的立法改革中將名稱逐漸加以修訂,二是當法律適用發生沖突時,可以將名稱沖突的裁決權賦予某同一位階法律文件的上位立法機關或者不同位階法律文件的共同上位立法機關,以權威機關解釋的方式明確不同名稱法律文件的地位和效力。
二、立法語言的科學化
《軍事法規軍事規章條例》第64條規定:“軍事法規、軍事規章的用語應當準確、簡潔、規范,符合語法規則。表達同一概念應當使用同一詞語。對含義復雜或者涉及適用范圍的重要詞語,應當在條文中對其含義或者適用范圍予以明確界定。”該條規定對軍事立法用語和使用概念的科學化做了原則上的要求,對規范軍事立法語言有很大的指導意義。
(一)立法用語規范化
所謂“法言法語”,講求的是立法用語的準確、簡練、嚴謹等特征,這是立法用語的一般風格,而我國的軍事立法用語又具有呼號化、口語化、藝術化的特有風格。比如《現役軍官法》第8條“忠于祖國忠于中國共產黨,有堅定的革命理想信念,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自覺獻身國防事業”的表述,《政治工作條例》第45條“民主生活制度每半年召開一次支部委員會或支部黨員大會進行交心通氣”中“交心通氣”一詞的使用、《紀律條令》第78條中“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表述,等等。一方面,這種特殊風格是宣揚軍事法政治屬性、體現軍事行為神圣性莊重性的需要,而另一面,這種風格又極易造成理解上的模糊不清,給司法和執法帶來困難。因此,筆者認為,軍事立法中的語言表達應該堅守法的本質體現在用語上的要求,更多地保證和彰顯軍事立法用語的一般風格,而對其特有風格,則應盡量減少和嚴格限制使用,以增強軍事法律條文的確定性和可操作性。
(二)使用概念統一化
《婚姻法》第33條規定:“現役軍人的配偶要求離婚,須得軍人同意,但軍人一方有重大過錯的除外。”在這里可以理解為,在同一法條中為避免重復,“現役軍人”和“軍人”指的是同一概念。再看《刑法》。《刑法》第7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而第259條關于破壞軍婚罪的規定則是:“明知是現役軍人的配偶而與之同居或者結婚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同一部法典中,“軍人”和“現役軍人”兩個概念是否等同,似乎并不清楚,更不用說《兵役法》中的“現役軍人”、《軍人撫恤優待條例》中的“軍人”,以及其他不同法律法規中對這兩個詞語的使用是否等同。再舉現有軍事法律用語中“戰時”表述一例。《刑法》第451條規定:“本章所稱戰時,是指國家宣布進入戰爭狀態、部隊受領作戰任務或者遭敵突然襲擊時。部隊執行戒嚴任務或者處置突發性暴力事件時,以戰時論。”可見《刑法》對“戰時”的界定是廣義上的,然而,這種定義過于“包羅萬象”,導致“戰時”的概念與其他近似概念混淆不清。比如《國防法》第44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權、統一、領土完整和安全遭受威脅時,國家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進行全國總動員或者局部動員。”再比如《戒嚴法》中對戒嚴狀態的規定是“發生嚴重危及國家的統一、安全或者社會公共安全的動亂、暴亂或者嚴重騷亂,不采取非常措施不足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的緊急狀態時”。2004年憲法修正案將“戒嚴”改為“緊急狀態”,由此,憲法規定的非常法律狀態為緊急狀態、戰爭和動員三類,而這三類狀態的明確定義似乎又都包含在了“戰時”的范圍之內,學者和專家的解釋也莫衷一是。由此引發的問題還體現在對日內瓦第四公約,即《關于戰時保護平民之日內瓦公約》的適用上。公約本身未明確何為“戰時”,因此這一概念仰仗我國法律的解讀,而“戰時”準確概念的缺失勢必會對戰爭中平民的保護產生影響。
以上兩例足以見微知著,現行軍事法律對某些基本概念仍然缺乏統一的界定。在接下來的立法改革中,應注意不僅要在一部法律文件中規范某一概念的具體定義,在不同的法律文件中也應將同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明確化。而對于現有的相互存在沖突的概念,對整部法律文件進行修改程序啟動較為復雜,有權機關可靈活采用法律解釋的形式予以說明,以為法律的準確適用提供便利。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