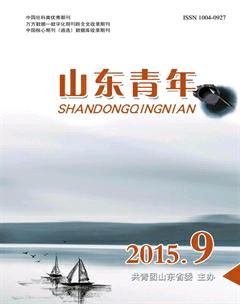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界限
張新新
摘要: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司法機關只能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認定和懲治犯罪,是實現刑事法治的重要途徑。由于刑法規定必然存在不完備處,刑事政策介入刑法的司法適用存在一定的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但是不能突破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對于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應探索合理界限,防止借貫徹刑事政策之名濫用刑罰權。
關鍵詞:罪刑法定原則;刑事政策;刑法
在刑事領域刑事政策一直發揮著重要作用,不過刑事政策如何介入、多大程度上可以介入刑法的司法實踐(以下簡稱刑法司法)仍需詳細探討,這一問題也關系到實現和保障刑事領域的法治。作為刑法基本原則之一的罪刑法定原則是刑事法治的重要保障,現從該原則出發,探討下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界限。
一、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界限問題
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是: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其基本要求是法定化、實定化、明確化,[1]可以看出,該原則發揮作用基本立足點是形式方面的要求,即司法人員嚴格根據刑法規定定罪量刑,理論上最理想的狀態是立法已事先對各種犯罪構成要件和刑罰作了完善的規定,司法人員嚴格依據法律規定適用即可,無需自由裁量,如此,可以杜絕國家意志隨意侵入定罪量刑過程,實現限制國家權力、保障公民權利的價值。在這種最理想狀態下,刑法在司法適用中基本沒有直接受刑事政策影響的可能,刑事政策只有上升為立法,才能作用于司法實踐,正是基于此,德國學者李斯特提出“罪刑法定是刑事政策不可逾越的鴻溝”的論斷。
但是,刑法本身具有法律規范固有的不足,如法律語言本身比較抽象,理解上容易出現偏差和困惑;法律條文不可能窮盡現實社會中所有情況,不可避免存在彈性條款甚至立法疏漏;法律規定不可能完全適應社會發展變化,存在一定程度的滯后。這些因素導致刑法不可能嚴絲合縫地適用于社會生活,不可避免存在不明確地帶,為司法人員發揮能動性留下空間,也為刑事政策介入刑法的司法實踐提供可能,這具有一定不可避免性和合理性。
不過,這并不意味著對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沒有任何限制或約束。刑事政策具有靈活性、宏觀性的特點,與刑法本身較為固定、具體的特點存在一定沖突,如果對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不加合理規制,則可能出現借貫徹刑事政策之名肆意出入罪、侵犯公民權益的情況。罪刑法定原則發揮功能的基本點是刑法的明確性,因此,立法上應在合理范圍內將刑事政策要求明確落實于法律規定,防止司法擅斷,而對于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也應探索合理界限,形成可操作性規范,使其有較明確規則可循,防止借貫徹刑事政策之名濫用刑罰權。
二、當前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主要途徑
(一)關于犯罪的定義。刑法第十三條對犯罪作了實質界定,其中有“但書”規定:“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實踐中可以遵循刑事政策精神,將一些情節輕微行為出罪。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第四款第四項規定:偶爾偷開機動車輛,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認為是犯罪。該解釋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精神,將輕微行為出罪。
(二)對兜底條款的規定。“兜底條款是指刑法對犯罪的構成要件在列舉規定以外,采用‘其他……這樣一種蓋然性方式所作的規定,以避免列舉不全。”[2]例如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條規定的非法經營罪的兜底條款:“其他嚴重擾亂市場秩序的非法經營行為”。對于一些法律條文沒有明確規定但嚴重危害社會的行為,遵循刑事政策的精神可通過適用兜底條款將其入罪。
(三)關于免除處罰的規定。刑法第三十七條規定:“對于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于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責令具結悔過……”,該條為依據刑事政策精神法內除罪提供了可能。例如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七條規定,對未成年罪犯如果悔罪表現好,并且有自首、立功等情節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十七條的規定免予刑事處罰。體現了對未成年人犯罪“教育、感化、挽救”的刑事政策精神。
(四)關于在法定刑下判處刑罰的規定。刑法第六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犯罪分子雖不具有本法規定的減輕處罰情節,但是根據案件的特殊情況,經最高人民法院核準,也可以在法定刑以下判處刑罰。”可以按照刑事政策的精神對某些特殊情形案件適用該規定減輕處罰。例如曾經轟動一時的許霆案,廣州市中院認定,許霆“盜竊金融機構,數額特別巨大,依法本應適用‘無期徒刑或者死刑,并處沒收財產的刑罰”,但是“根據本案具體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對許霆可在法定刑下判處刑罰”,因此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準,判處許霆五年有期徒刑。[3]該案如果機械套用有關盜竊罪規定處罰,將有違社會一般的公平觀念,法院這一判決貫徹了寬嚴相濟刑事政策要求,避免了執法機械和不公。
(五)關于量刑情節的規定。刑法中對大部分犯罪都規定了一定量刑幅度,給刑事政策適用留下空間,這主要是通過對量刑情節的考慮實現的。量刑情節包括法定和酌定兩類,酌定情節的種類法律沒有明文規定,而是根據有關法律精神和刑事政策,在司法審判實踐中總結出的,如犯罪動機、手段、時間、地點等。量刑情節是實現刑事政策目的的重要途徑。如1999年《全國法院維護農村穩定刑事審判工作座談會紀要》規定:“對故意殺人犯罪是否判處死刑,不僅要看是否造成了被害人死亡結果,還要綜合考慮案件的全部情況。對于因婚姻家庭、鄰里糾紛等民間矛盾激化引發的故意殺人犯罪,適用死刑一定要十分慎重,應當與發生在社會上的嚴重危害社會治安的其他故意殺人犯罪案件有所區別。對于被害人一方有明顯過錯或對矛盾激化負有直接責任,或者被告人有法定從輕處罰情節的,一般不應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該規定貫徹了“少殺、慎殺”的死刑刑事政策。
(六)刑法解釋。刑法本身沒有規定解釋規則,但是解釋和刑法適用息息相關。規范意義上的刑法解釋就是立法或司法解釋,其中立法解釋是立法活動的一種。前面提及的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幾種途徑本身就有解釋的問題,如何理解情節輕微?如何界定兜底條款如“嚴重擾亂市場秩序”?除此之外,有的條文對犯罪構成規定比較完備,但是用詞本身存在解釋問題,也為刑事政策適用留下空間。例如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定: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應當負刑事政策。這八種犯罪究竟是指具體罪名還是罪行存在爭議,很明顯,依罪行說得出的處罰犯罪范圍寬于罪名說。2002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關于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承擔刑事責任范圍問題的答復意見》采取的是罪行說,2003年4月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的人承擔刑事責任范圍有關問題的答復》再次確認了罪行說。但是,2006年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作出相反認定,該解釋第五條規定:“已滿 14周歲不滿16周歲的人實施刑法第 17 條第 2 款規定以外的行為,如果同時觸犯了刑法第17條第2款規定的,應當依照刑法第 17 條第2款的規定確定罪名,定罪處罰。”其采取的是罪名說,體現了對未成年特殊保護的刑事政策精神。
三、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界限
(一)總體要求
從罪刑法定原則出發,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應堅持以下幾點:1、刑事政策介入刑法應以罪刑法定原則為前提,刑法對定罪量刑有明文規定,不存在法律漏洞或不明確之處的,不能借貫徹刑事政策之名不予適用或突破刑法規定。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的,應通過前述刑法預留的途徑,不能直接援引刑事政策的規定。2、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要符合其他刑法基本原則、刑法價值和精神的要求,如罪刑相適應、平等適用刑法等原則,保障人權價值、謙抑性精神等。尤其是謙抑性,不能一味追求刑事政策的符合性,對一個認為有社會危害性但刑法缺乏明確規定的行為,要先看該行為是否能由其他法律如民法、行政法等進行規制,如果無法抑制這種行為的,才有可能通過刑法解釋、適用兜底條款等方式入罪。3、要保持刑法的整體性,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要注意與其他條文的協調,不能更改、超越其他條文的規定。4、要盡量保持司法標準的統一性。有權機關特別是最高司法機關應當及時總結,通過司法解釋或指導性案例、意見等方式規范刑事政策介入刑法司法,盡可能避免司法擅斷。5、應注意及時完善立法。刑事政策畢竟存在較大彈性,易引發爭議,因此對于實踐中比較成熟的做法應盡量上升為立法規定,限制司法裁量權。下面對若干具體問題作一討論。
(二)“但書”適用的規范
應注意但書的適用要和具體犯罪構成要件緊密結合起來,即行為要從形式上已符合一個犯罪要件,在此前提下,才能討論是否情節顯著輕微不認為是犯罪,不能將但書的規定異化為可以根據情節輕重單獨認定是否構成犯罪,否則刑法對于犯罪構成的規定將失去意義,罪刑法定原則也失去適用余地。 例如,對于情節犯刑法明文規定“情節較重”或“情節嚴重”才構成犯罪,該類犯罪要么行為情節較輕或顯著輕微不構成犯罪,要么情節較重或情節嚴重構成犯罪,但書對該類犯罪不具有適用可能性。[4]
(三)兜底條款適用的規范
兜底條款往往彈性較大,因此適用時要謹慎,尤其要注意對兜底條款的理解應盡量注意體系性、整體性,注意立法目的,解讀兜底條款時應注意實質含義不能與前面條款抵觸,要符合立法本意。例如,我國刑法第一百九十三條規定了5種貸款詐騙方法,其中前4項列舉了具體方式,第5項是兜底條款: 以其他方法詐騙貸款的。從前4種行為規定看,貸款詐騙的本質為行為人在申請貸款的過程中,虛構事實,隱瞞真相,騙取銀行或其他金融機構的貸款,因此第5項兜底條款規定的行為應當與前4種方法屬于同一性質且危害相當。有觀點認為合法取得貸款后隱匿、轉移抵押財產,惡意不歸還貸款的,屬于第5項“以其他方法詐騙貸款”,但是這種情形并未采用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這種觀點并不符合系統性要求。同時,適用兜底條款應遵循刑法謙抑性要求,特別是涉及經濟活動的罪名如非法經營罪和貸款詐騙罪,避免對經濟活動造成不當干擾。另外,兜底條款一般彈性較大,如果作司法解釋很可能創設出新的罪狀或法定刑,變相進行了立法,因此由立法機關解釋為宜。
(四)量刑情節適用的規范
法定量刑情節刑法已有明確規定,但是酌定量刑情節的種類和適用條件刑法都無明文規定,有更大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因此尤需加以規制。在考慮量刑情節包括酌定量刑情節時,要注意參考以往的司法慣例、判例。同時最高司法機關也應出臺有關指導性意見,如最高人民法院 2010 年制定了《人民法院量刑指導意見(試行)》。從長遠看,為了更有效防止酌定量刑情節的不當適用,至少應將一些常見的、已被司法實踐廣泛接受的、操作較成熟的酌定量刑情節法定化。另外,在對酌定量刑情節進行規范和適用時,要注意其只能是和犯罪、責任認定有關的因素,不應包括與犯罪本身沒有聯系的因素,如社會治安形勢、民意等。
(五)刑法解釋的規范
刑法解釋的方法一般可以分為文理解釋和論理解釋,而論理解釋又可分為擴張解釋、限制解釋、當然解釋、沿革解釋、目的解釋等。[5]各種解釋方法之間是否存在一定的位階關系存在爭論。應當說,文理解釋(或文義解釋)是對法律條文規定嚴格依據語法等語言文字自身的規律、規范作的解釋,應當是首選的解釋方法,因為罪刑法定原則基本要求是刑罰權能嚴格依據法律規定行使,法律文字承載了立法者的要求和設想,法律文字可能的理解范圍應成為裁判權行使的界限,因此如果通過文理解釋就能明確法律條文含義的,就無需再借助其他解釋方法;而文理解釋不能得出確切結論,必須適用其他解釋方法時,也應從對文意的解釋開始,而且應在法律文字可能的語義范圍內進行。“法學之終極目的, 固在窮究法之目的,惟終不能離開法文字句,一旦離開法文字句, 即無以維持法律之尊嚴及其適用之安定性,故法律解釋之第一步系文義解釋,而其終也,亦不能超越其可能之文義。”[6]經過文理解釋,仍不能得出確切結論,適用其他解釋方法還是得出不同結論,應當采用符合法條目的的解釋。[7]
在此需要特別關注的是擴張解釋和類推解釋問題。擴張解釋對刑法條文用語的理解只能從通常含義擴大到可能語義的邊緣,一旦超過可能語義邊緣,就淪為類推解釋,類推解釋是指對于法無明文規定的行為,按照刑法中最相類似的條文加以解釋,[8]是被罪刑法定原則堅決摒棄的。例如,2001年4月頒布的《關于辦理生產銷售偽劣商品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六條規定: 醫療機構或者個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是不符合保障人體健康的國家標準、行業標準的醫療器械、醫用衛生材料而購買、使用,對人體健康造成嚴重危害的,以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定罪處罰。該司法解釋出發點是嚴厲打擊危害公共衛生安全的行為,但這種界定與刑法其他條款中購買、使用和銷售的規定不一致,也與日常生活中有關理解不一致,超出了法條文義的最外延邊界,是一種類推解釋。
[參考文獻]
[1] 陳興良.規范刑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第39頁。
[2] 陳興良.刑法的明確性問題:以〈刑法〉第225條第4項為例的分析[J].中國法學,2011年第4期。
[3]許霆案重審判決書[EB/OL]: http://www.zjzllawyer.com/news_view.asp?newsid=187,引用日期:2015年5月30日。
[4] 張永紅.刑法第13條但書的適用范圍[J].黑龍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學院學報,2006年第6期。
[5] 陳興良.規范刑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第35頁。
[6] 楊仁壽.法學方法論[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20-121頁。
[7] 張明楷:刑法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年第四版,第40頁。
[8]陳興良.規范刑法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3年第三版,第4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