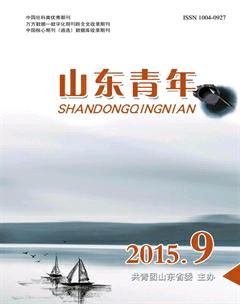檢察機關終結性法律文書公開的三個問題
鄭成功 蘇正茂 沈春鳳
我國各級檢察機關的信息公開被稱為“檢務公開”,隨著法治化進程的加快以及“依法治國”的客觀需要,檢務公開工作日益受到重視,早在2006年6月,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定的《關于進一步深化人民檢察院“檢務公開”的意見》一文當中就明確指出“就依法可以公開的訴訟程序、訴訟期限、辦案流程、案件處理情況。法律文書、辦案紀律等信息,要主動予以公開”。2013年11月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也明確要求“推進審批公開、檢務公開。”為了落實中央精神,在最高人民檢察院2013年12月公布的《2014-2018年基層人民檢察院建設規劃》再一次明確要求:深入推進基層人民檢務公開工作……健全主動公開和依申請公開制度。除法律規定需要保密的以外,執法依據、執法程序、辦案過程和檢察機關終結性法律文書一律向社會公開。
“執法依據、執法程序、辦案過程”相對比較明確,有的直接是法律的明文規定,所以公開起來相對容易,但是對于“終結性法律文書”的公開,還有不少需要探討的地方。
一、什么是“終結性法律文書”
對于“終結性法律文書”的定義,沒有官方的說明,學理上也沒有權威的定論,只能從其表述中對其特點進行一定的分析,以便于確定范圍。
終結性法律文書屬于法律文書的一部分,其有別于檢察機關其他文書的最大特點在于其有“終結性”,一種確定性很強,不受以其他司法機關意志為轉移的法律文書,是在特定程序上對當事人所涉及的特定法律關系做出終局性的決定,概括而言應該包括兩個方面:第一是某項刑事訴訟活動的終點,比如:不起訴決定書,該法律文書向當事人宣布后,做出決定的檢察機關針對被不起訴人的刑事訴訟程序就已經結束;第二是非因法定理由,不得再次啟動程序。比如《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第302條規定:人民檢察院直接受理立案偵查的案件,撤銷案件以后,又發現新的事實或者證據,認為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責任的,可以重新立案。可見撤案決定具有終結性,要重新立案符合“發現新的事實或者證據”這一明確法定理由。
此外,終結性法律文書是檢察機關在辦理自行偵查、審查批捕、審查起訴、刑罰執行變更監督等階段產生的,是對案件進行了司法審查之后依法做出的一種結論,所以它具有明確的司法屬性。
二、需要公開的終結性法律文書的特征和范圍
人民檢察院不是行政機關,但也是掌握著公權力、要為人民服務的單位,所以《政府信息公開條例》所確立的“以公開為原則,以不公開為例外”的信息公開標準對檢務公開工作也有較強的指導意義。進行最大幅度的公開,可以保證“權力在陽光下行使”,減少公權力被濫用的隱患。
但是,人民檢察院作為刑事訴訟法律活動的主要參與者,其工作也有特殊性,部分工作的內容和對象還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所以在進行檢務公開的過程中,要注意可以公開的終結性法律文書的范圍。
對照2012年最高人民檢察院修訂后引發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法律文書格式樣本》來審視,各級檢察機關制作的法律文書共有223種,分成十一大類。根據中國檢察出版社出版的《檢務公開論》和最高人民檢察院《建立檢察機關終結性法律文書向社會公開制度》的論述來分析,233種法律文書中需要公開的有31種。
部分地方檢察機關也對終結性法律文書公開的工作進行了一定的探索,比較典型的有:廣東省人民檢察決定將不批捕、不起訴、不抗訴、不賠償等終結性法律文書在網上公開;河南省檢察院要求在征得當事人明確同意后,將立案偵查案件的不立案、不起訴、撤銷案件的決定書面向社會公開。
從最高人民檢察院制度的相關制度、各地的公開實踐和相關的理論研究可以歸納出需要公開的終結性法律文書也以下幾個特點:
第一是程序上的終局性,這一點在第一部分已經有過論述,在此不再贅述。
第二是這類法律文書一般具有否定性,需要公開的終結性法律文書一般是對實體和程序上的一種“否定性回答”,通俗的說就是“不同意”、“不允許”或者“不繼續”。因為這類文書往往涉及到當事人或者單位的利益,所以有必要進行公開,一來起到告知的作用,二來也能讓與此密切相關的其他人或單位了解情況。
第三是不涉及保密內容,檢察機關的工作時常涉及國家秘密、商業秘密或者個人隱私,在進行終結性法律文書公開的過程中也要加以重視,對于有保密要求的文書,不應公開;確實需要公開或者部分涉密不影響整體公開的終結性法律文書,在公開之前應當刪除或者覆蓋涉密的內容。
對照以上標準,可以全面公開的終結性法律文書包括:《不立案通知書》、《不批準逮捕決定書》等,在做好保密工作之后,可以公開的有《起訴書》、《不提出強制醫療申請決定書》、《刑事申訴復查決定書》等等。
三、終結性法律文書公開的方式
明確了需要公開的終結性法律文書的特點和范圍之后,接下去就工作就是進行公開,以何種方式進行公開是一個事關成效的重要問題。結合當前社會信息化的背景,有以下三種方式可供選擇各級檢察機關采用:
(一)公開宣告
通過公開宣告的方式將特定的終結性法律文書進行“廣而告之”,并不僅僅是檢務公開過程中的一種探索,同時也是現行法律中規定的一種形式。進行公開宣告,即是一種法定的送達方式,也是讓當事人周圍的人或者單位周知此事的一種最直接的辦法。比如對一個取保候審的當事人的不起訴決定,可以在當事人所在的社區或者轄區派出所進行宣告。當然,這種方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因為公開宣告是在一定范圍內進行的,雖然在場的對象可以是不確定性,但是接下去依靠在場的人進行“口口相傳”的傳播,速度和范圍也有限。
(二)通過新聞媒體進行公開
此處的“新聞媒體”是指傳統媒體,比如:報紙、電視、廣播等,這一渠道的優點在于權威性、一定區域或者范圍內內受眾的普遍性。因為傳統媒體經過幾十年的發展,已經有了相對固定的受眾群體,不少還帶有官方背景,比如:各類地方日報、省級衛視等等,權威性相對較強,是進行檢察公開的一種良好選擇。
但是新聞媒體在進行報道時,很少會整版面、大時長的全文刊播法律文書,一般都會選擇文書當中特定的內容或者章節段落進行報道,或者刪除它們認為沒有必要的內容,并且還會進行一些點評。所以通過新聞媒體進行公開,可能會影響法律文書的客觀性,甚至被還會被傾向性解讀,引發爭議。
(三)通過網絡公開
終結性法律文書通過網絡公開,可靠的渠道是三個:第一是通過本院或者本系統其他官方網站、官方微信、官方微博進行公開,比如:浙江檢察網;第二是通過本地宣傳部門的官方微信微博進行公開,比如:“浙江發布”官方微信;第三是通過傳統媒體的電子版或者它們自建的新媒體進行公開,比如:浙江日報報業集團主辦的“浙江在線”網站。
通過這三種方式進行網上公開,可以將終結性法律文書全文上傳或者以圖片的形式全文上傳,確保了客觀性,又可以保證發布渠道的權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