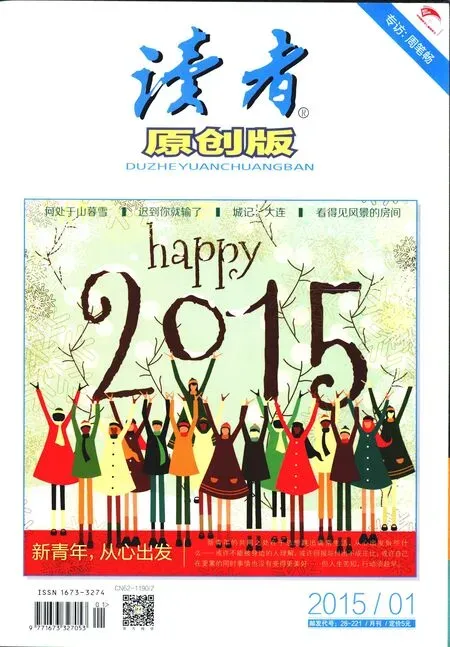三個捐贈箱
文_另 維
三個捐贈箱
文_另 維
另維,前NBA主播。襄樊四中畢業,目前就讀于華盛頓大學,主修會計和商業管理,還有第二學位心理學。
2013年休學,經停北上廣,2014年返校。時而賺錢,暫不攢錢,游記和照片是目前全部的財產。
專欄中的小故事,發生在她停留過的不同的城市。里面的人她遇了又散,里面的故事她打包帶走。
一
我走出學校超市時,撞上一個男孩。
我手里抱著滿滿一袋食物:哈根達斯、費列羅巧克力、芝士蛋糕……我剛剛花完學生卡里的余額。卡里的錢只能在食堂和超市消費,每學期清零一次。食物買回去壞掉一半,也好過錢被電腦系統吞掉。
我撞上的男孩同樣滿載而歸。我見他褐色頭發,藍色眼睛,一張臉像極了王力宏,不由得眼睛一亮。
他的紙袋被我撞翻了,物品四處滾落—吞拿魚罐頭、玉米罐頭、豌豆罐頭、牛肉罐頭、雞肉罐頭,都賣1.99美元。
“竟然有人在暑假前大量囤罐頭。”我一邊撿一邊小聲評論。
男孩看了我一眼:“如果我事先知道會撞到可愛的女孩,就會省下買罐頭的錢請她喝咖啡了。”
說完,他把罐頭一一放進超市門口的紙箱里。
紙箱放在那里已經一周了,我沒注意過,此刻定睛一看,上面寫著“donate food here, for Seattle refugee kids(給西雅圖難民小孩們的食物捐贈箱在這里)”。
原來他把余額換成罐頭,是要給缺食少糧的小孩。
這時又有兩個人在路過捐贈箱時蹲下,把多買的罐頭放進箱子。我低頭看了看自己的袋子,覺得好像做錯了事。
二
和男孩一同離開超市,聊起捐贈箱,我說我知道每到學期末,圖書館、寢室、校園超市門口都會放這么個箱子,但沒注意過。
他要為我私人定制“觀箱游”,這期間我得知他叫Connor,學心理學,是大三學長。
我端著他買的白巧克力摩卡,他抱著我的紙袋,我們慢悠悠地走過紅磚鋪砌的地面,頭頂是鉛灰色的天空,陰且潮濕。偶爾走過幾個學生,都一臉興奮。
這是春季學期的最后一天,學校規定所有人在兩天內搬出寢室,學生卡里的余額兩小時后清零。
Connor拉開圖書館大門,我走進去,捐贈箱在正前方。
“School supplies”,這次是學習用品。
箱子里有彩色蠟筆、文件夾、書本、作業本、圓珠筆、橡皮……倒也不是精美的東西,但都干凈能用。
“每次箱子擺出來,半天就滿了。放假后會有人把物資送到難民營里的中小學校。”Connor說。
這時,一個3歲左右的男孩蹣跚進門,順手把嘴里的棒棒糖扔進箱子。“成功!”他歡呼雀躍,但馬上就被跟上來的爸爸捉住了手臂。
“說你永遠不會再做這樣的事情!”爸爸像是這里的學生,他把嚇壞了的小男孩摟進懷里拍了拍,伸手進箱。
黏糊糊的糖汁殘留在文件夾上,爸爸放下書包,我以為他要掏紙巾擦拭,但他拿出的是自己的文件夾。他取出試卷,把空夾子放進捐贈箱,臨走時對我們說了一句“sorry”,似乎是在為這一幕道歉。
“大家還真尊重這個箱子。”我說。
“是的。”
“是因為宗教思想吧,天主教總是強調分享。”怪現象總要有解釋。
周日做禮拜,但我不是信徒,只蹭早餐。教堂不僅回回歡迎,還讓我把剩余的食物帶回家,說我年紀輕輕,獨自在外,學業忙碌,比他們這些有家有收入的人艱辛,更需要豐盛的食物。教堂的早餐資金,應該是來自每次禮拜結束時幾美元、幾十美元的捐贈。
我沒有捐錢的習慣,是因為曾在蘇丹難民區做過課業輔導。我們抱著零食、飲料去中學圖書館,吸引學生前來接受輔導。人來了,往桌前一坐,書包是Kipling的,帽子是CK的,自動鉛筆都是我挑好后發現太貴又放回去的款式。
我覺得他們應該給我捐錢。
如今想起來,對他們而言,那些商標大約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善意,而不是貼在身上指望象征什么的標簽。
“看來難民比流浪漢幸福多了。”我說。
“流浪漢四海為家,還時不時有Food Bank(食物銀行)供給免費食物。我將來要是失業租不起房,去做一段時間的流浪漢也不錯。”
“Food Bank?”
“它們收集社會各界捐贈的食物,分類裝箱,定時開門,流浪漢排隊領取。學校后面就有一家,每周五10:20開門,到時帶你去看。”
“你這是在申請第二次約會嗎?”
“是的,因為你看起來很享受跟我一起玩。”
三
天黑了,寢室門口的捐贈箱隱沒在暗夜中。杯子、小書架、筆筒、臺燈、刷子、鍵盤……搬家帶不走的東西都在這里了。不知道它們會被擺在誰的窗前,成為主人愛不釋手的新伙伴。
我的目光落在箱子邊的一摞書上,眼前一亮。我看到了一本《生物心理學》。
開學前,我從學校書店租了這樣一本書,定價165美元的課本,租金65美元,期末歸還。
今天上午,書店拒收了這本書,因為我滴上的水造成頁面起皺,屬于“損毀”。我只能留著這本書,再補100美元。
我即將花100美元買一本一眼也不會看的書。我心情不好了一整天,直到遇上Connor。而面前的這一本,沒有任何瑕疵,我抓起它,手舞足蹈地講了來龍去脈。
“Connor,我要用我的書換這一本,不過拿走捐贈箱里的東西,感覺真糟糕。”
“這是聰明。快去拿你的書,完成交換吧。”
我是在電梯里收到學弟微信的,他愿意出70美元買下課本,下學期用。70美元可以買許多食物

和文具。難民小孩用不上大學課本,學弟卻能省下將近100美元。
學弟收了我的書,歡天喜地。我拿著70美元換了130支鉛筆、17盒罐頭,蹲在超市門口的捐贈箱前,模仿Connor的輕巧自然,全部放進去,起身離開。沒有人投以贊許的目光,沒有人覺得我做了一件偉大的事,但我感覺棒極了。我覺得那夜回家路上的路燈都因我而分外明亮,直到睡著,我的心跳都沒有回到正常頻率。
四
我對自己說了三遍,20歲的成年人應該擁有解決誤會的能力。
睡醒時看到Connor的短信,他說沒有在捐贈箱里看到我拿走的書,那已經是3小時后。我所謂的馬上取書放回是個謊言,他感到失望和氣憤,但因為看過我如何使用學生卡里的余額,他不覺得意外。
發送了解釋,我滿腦子都在猜想他讀短信時的表情,猜想他能否及時看到、正確理解,又會如何回復。我一整天都捧著手機,手機響心尖顫,不響也心尖顫。
他終究沒有回復,我的解釋確實像一個牽強的借口。我也不再試圖聯絡—再好的男孩,也犯不著觍著臉追。
五
2014年3月,我結束為期一年的休學,回到課堂。
第一節課,教授介紹助教,念到Connor Johnson時,起身的那個人許久不見卻依然熟悉。
我在課后叫住他,他還記得我,只是忘了名字。說起那條沒有回復的短信,他瞪圓了眼睛。
“一定是手機停機了,我沒收到。”他想了一會兒,補充道,“沒錯,是停機了。我還記得發信息后我有點愧疚,想打電話,為我說話太重道歉,但是沒有打通。”
一同走出教學樓,我們的話題徹底漫無邊際了。心理學專業的助教都是研究生,我祝賀他考進全美最好的心理學研究院,他稱贊我休學旅行有勇氣。就這樣走到岔路口,他提議一起喝杯咖啡,我搶先埋了單。我說:“我欠你一杯咖啡很久了。”
我們一邊走一邊喝咖啡,路過相遇的校園超市,還是許久之前的樣子。Connor笑著說起我一頭撞上他時的狼狽,我跟著笑。
“Got a boyfriend now(你有男朋友了嗎)?”
“Yup(是的)!”
“Congratulations(恭喜)!”
“Thanks(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