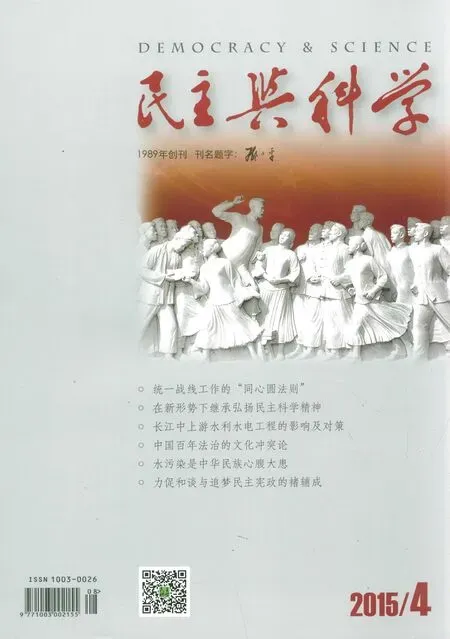建立長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
毛 前 陳海雄
(毛前為浙江水利水電學院教授;陳海雄為浙江水利水電學院講師)
生態補償機制是可以量化生態損失的一種手段。
長江上游的戰略地位決定了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必要性。
將水電工程對生態造成的損失從定性層面量化換算成經濟指標,讓“看不見的手”發揮作用。
生態補償機制是可以量化生態損失的一種手段。生態補償是國際上流行的可持續發展公共策略,是解決發展中引發的“效率”與“公平”問題比較有效的管理手段之一,基本原理是從發展中獲益一方對造成的外部環境損害進行賠償;而當一方為了保護環境放棄發展機會時,也有權獲取相應補償。上世紀80年代,我國有學者開始對生態補償有所關注。2006年4月,在第六次全國環境保護大會上,時任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指出,要按照誰開發誰保護、誰破壞誰恢復、誰受益誰補償、誰排污誰付費的原則,完善生態補償政策,建立生態補償機制。2007年9月,國家環保總局印發《關于開展生態補償試點工作的指導意見》。這是我國中央政府首次對開展生態補償措施發布指導性文件。但從總體看,我國的生態補償機制仍處于初級階段,尚未形成一套完整體系,還沒能在可持續發展中發揮應有作用。
長江上游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戰略地位決定了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的必要性。對于長江上游大型水利工程,經濟效益絕對數無疑是巨大的,但效益分析如果只談正面效益,不考慮生態環境破壞等負面效益是不科學的。目前大部分情況下,水庫開發對生態造成的影響還停留在定性層面上,如果沒有量化估算,結論總是缺乏說服力,迫切需要量化手段,除了對損失范圍、數量和時間估算外,最好能將生態損失換算成經濟指標。只有將生態損害提升到定量估算,才能為防洪、發電、航運等正效益提供參照。將生態補償費用直接當作水利開發過程中對生態影響的一種量化,納入水利開發成本,用市場機制影響項目投資決策。
構建長江流域生態補償機制,系統、科學地制定長江流域生態補償政策,實現全流域合作共贏迫在眉睫。
一是盡早出臺生態補償法。我國至今還沒有一部專門針對生態補償的法律法規。現階段對流域環境的保護主要參照《環境保護法》《水污染防治法》的有關規定。地方政策上,雖然有的省出臺相應規章、意見或辦法,但因對補償主體、補償標準、補償對象等找不到執行依據,可操作性不強。
2015年4月25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意見》明確提出,要“研究制定節能評估審查、節水、應對氣候變化、生態補償、濕地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土壤環境保護等方面的法律法規”。應該抓住時機,早日出臺生態補償法,使生態補償制度建設得到法律保障,特別是對長江流域這樣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地區,既要開發利用好其豐富的水利資源,又要在國家層面專門建立生態補償機制,使之走上良性循環軌道。
二是明確生態補償主體。將水利開發單位作為長江流域生態補償主體,補償資金計入開發成本,水利項目正面生態效益的收益計入該項目效益。另外,對水體造成負面影響的上游企業排放繳款或罰款由其統籌。這樣既可以避免生態補償管理中九龍治水現象,也理順了生態補償的資金來源。如果水利開發單位因為生態補償款入不敷出,則說明該項目弊大于利,反之則證明項目開發是值得的。流域生態補償客體可以是治理污染或改善生態的政府和企業,包括對生態環境的保護做出貢獻的政府、企業和個人。例如,國家為了保護魚類資源,每年進行增殖放流經濟物種,其中僅2010年就向長江投入約2.5 億元人民幣。這筆費用至少一部分應該獲得生態補償。
三是推動多方位生態補償實踐。從發達國家和地區經驗看,生態補償應該是全方位的。例如美國在農業、自然環境保護、采掘業、流域水管理、環境污染防治等領域廣泛建立補償機制;歐盟建立有機農業、生態農業、傳統水土保持、甚至地邊田梗生物多樣性補償機制;日本在造林、水污染防治、自然保護區、農業等領域建立生態補償機制。我國即使是走在最前面的浙江省,新安江試點也只是針對水質這一單一指標進行。補償范圍太窄,不能滿足生態文明建設的迫切需求。建議推動多方位生態補償實踐,積極發揮市場機制調節作用,形成適合我國國情的生態補償機制和實務體系,讓生態補償納入水利項目開發成本,讓生態問題對水利開發項目決策的影響由“看得見的手”過渡到“看不見的手”。
四是制定有差別的區域生態補償標準。長江作為我國第一大河,干流流經10 個省、市、自治區,流域范圍涉及19 個省、市、自治區,流域內人口眾多,不同省份經濟發展差異性很大,不宜搞大一統的國家標準,國家應該只負責立法、出臺一些引導性政策,并提供一些指導示范性案例,由地方政府、行業主管部門根據各種環境保護措施所導致的收益損失確定補償標準,可以根據不同地區環境條件等因素制定出有差別的區域補償標準,也可以通過雙邊或多邊談判確定,盡力避免政府直接的垂直補償。
五是推動生態補償科學和政策研究。生態補償機制的建立將倒逼相關科學研究開展和運用,如水庫群生態聯合調度研究和各河段生態基流確定。因為如果生態補償納入水利開發成本,開發主體就有義務和動力去開展相應研究,為減少補償額提供依據,同時引導水利開發向生態正效益、環境可持續方向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