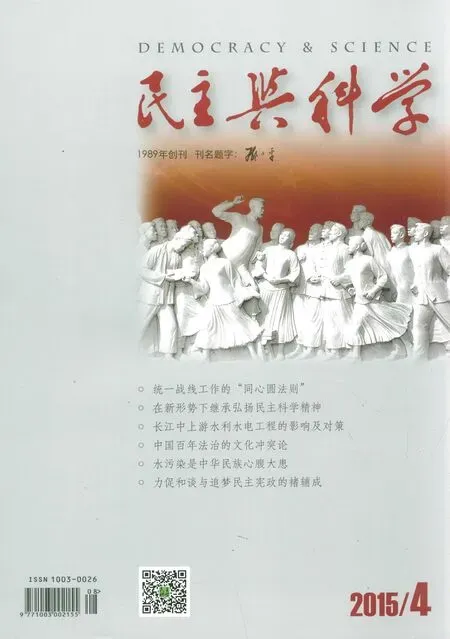“一帶一路”建設與跨文化傳播
陳力丹
(作者為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院責任教授)
“絲綢之路經濟帶”是習近平2013年9月7日在哈薩克斯坦納扎爾巴耶夫大學發表演講時提出的。他說:“我們可以用創新的合作模式,共同建設‘絲綢之路經濟帶’,以點帶面,從線到片,逐步形成區域大合作。”2013年10月3日習近平在印尼國會發表演講時進一步提出“共同建設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2014年,他在APEC 會上概括為“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是中國大戰略。把“一帶一路”說成是中國與全球經濟一體化接軌,這是認識的誤區。一帶一路是中國全球化的初始階段,不是與美國推動的美元全球化銜接。很多人以為全球化是一個歷史潮流,不是的,全球化是大國推進的趨勢。“一帶一路”是中國的全球化,對此我們要有清醒定位。在這個意義上,成功的跨文化傳播對中國“一帶一路”建設極為關鍵。
有的官員講中國搞“一帶一路”沒有任何政治訴求,也沒有意識形態輸出需求,就是要搞經濟,就是要跟沿線國家互利互惠。這樣講給別人聽沒有錯,但我們自己若這樣認識,一定會出問題。“一帶一路”是中國對美國戰略東移的一種非對抗性選擇。
中國西北地區特別是新疆處于“一帶”主干道上。中國從這里走出去便是中亞,主要是突厥語族和斯拉夫語族國家。新疆處于這兩個語族與漢語族的交融地帶,其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等民族的語言都屬于阿爾泰語系突厥語族,蒙古語、錫伯語分屬蒙古語族和通古斯滿語族。俄羅斯語屬于印歐語系斯拉夫語族,塔吉克族是我國唯一講印歐語系伊朗語族語言的民族。這些民族與漢族有千年共同生活與交流的經驗。
再向西就是歐洲。我們與更多印歐語系民族和國家接觸。除了斯拉夫語族各種語言,還有日耳曼語族的德語、英語和北歐各種語言,拉丁語族的法語、意大利語、西班牙語等。至少新疆境內的俄羅斯語、塔吉克語與漢語交流的經驗,可以作為進一步走出去交流的研究基礎。
最初的跨文化傳播對雙方來說都是一種陌生人之間的傳播。“陌生”帶來不確定性,可怕但也可能帶來發展機遇。我組織中國人民大學研究生做的論文《陌生人理論在跨文化傳播及人際傳播中的應用》,從德國社會學家格奧爾格·齊美爾的“陌生人理論”談起,對跨文化人際傳播作了一番論述,可能引發讀者對陌生人理論的興趣。
我組織研究生做的論文《APEC 峰會期間中國對外傳播翻譯實踐分析》,分析了15句習近平講話中具有中國特色的漢語,討論這些言語如何與國外習慣的話語體系、表述方式對接,易于為國際社會理解和接受。這些言語是中國文化的體現,折射著一定政治內涵。通過研究,可以為“一帶”建設過程中更為復雜的多種語言之間的深度理解和交流提供經驗。
新疆跨文化傳播研究有充分的天時地利人和條件。傳播學與語言學研究者結合,有可能做出有效的科研成果。新疆大學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韓強與他的研究生做的關于哈薩克斯坦受眾情況的文章,就為中亞跨文化傳播研究做了基礎性工作。
習近平談到對外傳播時提出:“要著力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創新對外宣傳方式,加強話語體系建設,著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講好中國故事……”習近平論述的重點是“創新對外傳播方式”和打造“三新”,而媒體把“講好中國故事”變成了套話,卻不談對外傳播如何打造新概念、新范疇、新表述,不談如何創新。現在除了“學習粉絲團”關于習近平的報道和介紹形式上有所創新外,日常的對外傳播思路和內容基本是老一套,不見起色。創新對外宣傳方式,絕不是花上千萬元到紐約時代廣場做個廣告,更不是跟外國人講中國人在做什么夢。
為此有必要先研究一下不多的成果,例如曾經出版《我在伊朗長大》的法國達高出版社,2009年商業化推出的漫畫集 《從小李到老李——一個中國人的一生》在世界70 多個國家流通,有12 種外文版本,獲得多項國際大獎。它通過講述一個普通中國人的一生,向世界展示一個真實的中國。我的碩士生今年的碩士論文《跨文化傳播中的故事表達》,從敘事題材、人物塑造、繪畫風格三方面,討論了為什么這么多的外國人喜歡它,提出了三方面的經驗:外國人想聽什么(量體裁衣,選對主題);怎樣講好故事(中國故事,國際表達);避免刻意打扮(平衡客觀,去意識形態)。
當然,去意識形態并非沒有意識形態和政治。我們走出去會遇到各種無法回避的意識形態問題,以及我國與別國由于不同文化傳統、宗教而發生的從觀念到行為的沖突。
如何處理這類跨文化交流的問題?這里講一個教訓。就在習近平8·19 講話之前的8月1日,我國所有的主要網站在首要位置連續48小時刊登一篇文章,說俄羅斯是“經濟上無關緊要的世界二三流國家”,“在工業體系崩潰后肯定是窮得要死的國家”。俄官方中文“俄羅斯之聲”8月15日發表回應文章,第一段全文是:“我的中國朋友們讓我開始關注中國國內對蘇聯解體的影響這一話題的討論。事實上,我們在俄羅斯國內對這個問題也爭論不休,比如電視屏幕上的政治家、報紙上的知識分子、火車上的旅伴以及茶余飯后的一家人等等。需要指出的是,我們現在能公開對國家的過去進行辯論就已經是后蘇聯時期的一大進步了,這是俄羅斯歷史上首次出現的現象。下面我從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和新世紀頭10年這三個年代中每個年代俄羅斯人的生活中列舉一些實例。我想強調的是,我要談的是普通人的生活。”
我們不會說話,更不會溫和地說話,而人家利用我們踢過來的球,進行了一次溫和的反宣傳。這方面我們需要向人家學習。習近平的8·19 講話要求宣傳工作胸懷大局,順勢而為,要求創新對外傳播方式和打造“三新”,是有針對性的。
還有一個選題思路不可忽視,即外國人關于中國傳播內容與形式的研究,我國這方面還很落后,停留在分析批判人家媒體,對如何歪曲中國方面,缺少建設性研究。2015年1月15日至24日,KBS 電視臺推出7 集新年特別企劃紀錄片《超級中國》。該片給韓國和世界帶來了哪些關于中國的印象,我沒有看到有分量的研究文章。5月8日,俄羅斯國家電視臺播出中國紀錄片,展現二戰期間兩國通力合作與法西斯斗爭的歷史,以及現在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從文化傳統著眼講述了中國人的精神世界。外國人看待中國的視角和傳播心理,應該成為中國跨文化傳播研究的一個重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