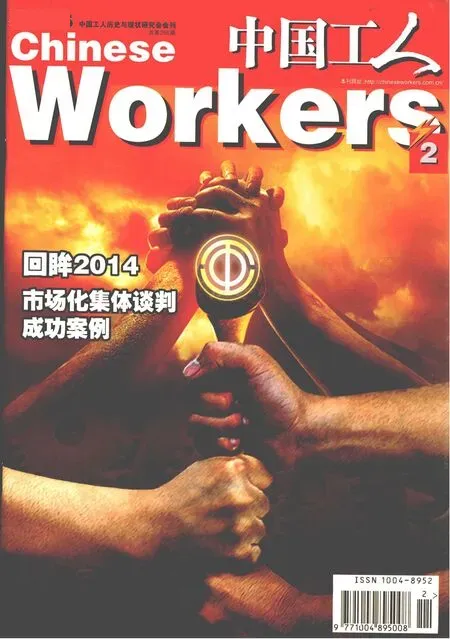2014:勞工事件盤點
清華大學社會學系 竇學偉
在已經過去的2014年,許多具有重大意義的產業沖突事件陸續發生,共同織就了一幅勞動關系日趨緊張的畫卷。在這些產業沖突事件中,勞動關系的多主體參與博弈成為了我國勞資矛盾發展的新特征,例如,勞方集體協商代表的積極作用,媒體曝光勞資沖突事件的影響,勞工信息傳播和話語建構,基層工會改革等都呈現出新的景象。因此,圍繞工人主體的社會各界整合不斷深化,一個融合了工人、社會工作者、知識分子、傳媒人、法律人等群體的多方互動博弈的集體勞動爭議模式正在萌生和發育之中。
本文通過盤點本年度發生的幾起重大勞工事件,并通過對這些事件過程的再現,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同時,也為集體勞動爭議的現狀與治理探討更多可能性。
常德沃爾瑪閉店事件
2014年3月5日,沃爾瑪湖南常德水星樓分店負責人向員工宣布閉店及安置方案,涉及135名員工。在一份貼在店門口的《安置方案》中,沃爾瑪要求員工于19日前在分流安置和買斷補償兩個安置方案中選擇其一。而在3月4日,沃爾瑪即調用了大批人員進駐店內,開始閉店的相關準備工作。
3月6日,員工集會表達訴求。他們認為閉店行為過于突然,“簡單粗暴、完全不尊重”員工,異地安置方案沒有可行性,而且沃爾瑪沒有按照勞動法律提前30天通知全體員工或工會,未就安置方案與員工或工會進行溝通,沒有履行法律義務,屬于非法解除勞動合同。資方非法解除勞動合同應當給予工人不低于兩倍的經濟賠償,而沃爾瑪給出的買斷賠償方案只給予一倍的經濟賠償。
之后的幾個月里,在工會主席黃興國和其領導的分店工會的組織下,員工進行了持續的抗議,不斷地在體制內尋求支持。由于企業工會的積極作為,此案引起了國內外勞工界的普遍關注,眾多知名的勞資關系專家介入其中,協助維權或組織協商。4月初,“常德沃爾瑪工會組織化抗爭事件研討會暨集體談判論壇”在河南登封舉辦,對勞工界的整合、分工與合作提出了具體的建議和發展方向。
4月25日,69名員工和分店工會分別向常德市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會提起勞動爭議仲裁申請,常德沃爾瑪事件走上“法律途徑”。經過仲裁之后,部分員工接受資方提出的調解方案,另外一部分員工向法院提起訴訟。
此事件引起了勞工界對沃爾瑪優化重組戰略下勞工權益受損狀況的持續關注。按照計劃這家在大陸經營近20年的全球最大零售商將會在三年內新設110家門店,同時,原有的20多家分點將會關閉。沃爾瑪工人維權案例折射出兩個有關集體勞動爭議治理的新問題。其一,由于企業經營戰略變化所引發的集體勞動爭議如何在保護工人合理、合法權益方面進行規制?其二,如何通過有效的勞資對話機制的構建來預防這類勞動爭議的發生?
東莞裕元鞋廠罷工
2014年4月份,裕元鞋廠工人的大罷工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裕元集團是一家臺資企業,為耐克、阿迪達斯等世界名牌運動鞋代工,是全球最大的代工鞋廠。其生產基地主要集中在中國、印尼、越南、柬埔寨和孟加拉,其中最大的一家廠區就是這次發生罷工的東莞市高埗鎮廠區,始建于1988年,現有約6萬員工。
年初,幾位已經退休的老工人在領取養老金時發現金額不對,經過調查發現裕元沒有給工人足額繳納社會保險。消息迅速傳開,4月5日,數千名工人自發聚集,向資方和高管討要說法。在得到高管“研究解決、限期答復”的承諾后,工人散去。在4月15日的大會上,工人的訴求沒有得到滿足,更大規模的罷工隨即爆發。
在隨后的兩個星期里,數萬名工人參與到罷工之中,在東莞各個分廠形成了大規模的罷工潮。4月28日,在政府、工會等有關部門的介入之下,裕元集團承諾從5月1日起足額補繳社保。隨后在多方壓力下,罷工工人陸續復工。
部分學者認為,這反映出了中國勞工維護自身權益的新特點。以前大部分罷工的主要矛盾,集中在加工資或加班問題,如2010年以南海本田工人抗爭引發的汽車行業罷工潮。而這次罷工的要求則比較特別,“第一次要求賠償社保”。從“長工資”到“追社保”的變化暗示出在企業產權變動的環境下觸發了工人的權利意識增長,特別是對于在企業工作了時間較長的工人對養老問題更為重視。而過往企業欠繳社保的問題,則形成了歷史負債集中爆發的態勢。政府如何通過工會來督促企業承擔法律責任應成為未來治理策略中亟待研究的問題。
深圳哥士比的工人抗爭
深圳市龍崗區橫崗快浩(哥士比)鞋廠有員工600余人,原屬“三來一補”企業,一直為國際品牌代工生產鞋子。2014年5月19日,資方向員工發出企業轉型(從“三來一補企業”轉為獨資企業)通告。該公司員工發現,資方有拖欠工資、遲交社保以及工廠訂單減少、供應商貨款出現拖欠等情況。工人們對新公司的前途表示擔憂,擔心自己未來的權益受損,尤其是工齡待遇問題。
5月26日,幾乎全廠工人參與了罷工(部分文員和新工人除外),主張新公司發放“原公司下發的長期服務補償金”。工人們先后到當地勞動站、鎮政府投訴,但沒能得到有效的回復,還被警察驅散。
5月27日,工人們繼續主張訴求。資方對工人的談判要求置之不理,并要求工人最遲6月4日復工,否則將解雇罷工工人。6月4日,工人復工。但是資方不顧之前公告承諾,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分批解雇了109位工人,直到最后解雇名單上一名女工墜樓身亡。7月17日起,被解雇工人依照法律程序進行維權,仲裁結果對工人的主張不予支持。
在珠三角企業轉型的背景下,由于閉廠或搬廠引發的勞資爭議日漸增多。在“工廠搬空、無工可罷”這種情況下,工人的權益如何保障,成為社會各界共同思考的問題。
廣州勝美達工會
1984年10月成立的廣州番禺勝美達舊水坑電子廠,是勝美達集團最大的生產基地,主要生產電子線圈類產品,用于數碼相機、DV、車載部品等。工廠現有員工6600人左右,99%是女工。
2013年,1500多名勝美達工人采取集體維權的方式,迫使廠方承諾補繳2002年以后的社保。但是勝美達通過一系列的方法對工人團結進行分化,并辭退了幾個工人代表。工人們開始意識到成立工會的必要性:“為了保護爭取的成果、為了保護工人代表們不被工廠秋后算賬,我們強烈想要成立勝美達工會”。
2014年4月21日,幾位積極工人正式向街道工會提交申請,要求籌備成立工會。在接下來的幾個月,為了籌備工會,勝美達的工人們在街道工會和上級工會以及公司之間不斷奔波。雖然勞動法律對于工人自發成立工會的行為有一定的規范,但是在實踐中,工人們在各個部門頻頻碰壁。
6月9日,工廠迫于壓力,公布了籌備組成員名單。讓工人們不解和憤怒的是,此前的維權積極分子完全被排斥在名單之外,一開始就阻撓工人成立工會的人事部負責人擔當組長,17名組員僅有8名一線工人,其余均為高層管理人員,甚至有幾個人根本不是本廠工人。進入籌備組名單中的部分工人對此毫不知情,也對工會一無所知。經過一個月多的運作,不顧工人的反對,工廠工會籌備組組織工會選舉,成立了工廠工會。
有關工人工會選舉的問題亦是學界廣泛討論的一個問題。然而,勝美達案再次對基層工會是否能夠通過建立有效的選舉制度來團結工人提出了挑戰。不可否認的是,資方對企業工會選舉進行干涉已經是一個普遍的問題。但是,在工人已經意識到工會組建和選舉的必要性的時候,基層工會應該依照《工會法》組織工人參與選舉,組建自己的工會。
廣州大學城環衛工集體維權
2014年8月21日,中山大學開學之日,廣州大學城200余環衛工在中山大學東校區核心位置“GOGO新天地”罷工維權,他們拉出橫幅“日曬雨淋九年合同終止,不承認工齡,請政府幫幫我們”。
事件起因是原物業公司在“大學城環衛作業競標”中失利,將于8月31日撤出。環衛工人對于將來產生焦慮,擔心失去“在大學城從事環衛作業”的工作,擔心之前的工齡在新公司接收后會被清零,得不到應有補償。在8月9日至20日持續多日抗議無果的情況下,于21日采取罷工行動。
這次維權引起了大學生和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中大學生陳偉祥(祥子)等學生前往現場了解事件原委以及工人訴求,并將這一事件撰寫成文《開學日,大學城環衛工罷工維權!》發在網絡上,倡議更多的學生和社會人士關注;此文獲得多家校媒和大學城的公眾賬號轉載,引發近20萬閱讀,次日大學城環衛工罷工事件引發廣泛關注。
8月23日,廣東番禺打工族文書服務部開始為環衛工人提供維權指導。在之后的37天時間里,環衛工人持續罷工。經過多輪的集體談判,在地方政府的斡旋下,環衛工人的訴求基本得到滿足。
在大學城環衛工維權過程中,與環衛工身處同一生態共同體的大學生,以關注、傳播、聲援、辯論、送水、捐款、調研、訪談、陪伴和維權等方式廣泛而深入地的參與。
公共服務行業的罷工也是本年度較為典型的一類個案,包括環衛工人、出租車司機、醫院護工和中小城市的中小學教師群體發起的罷工行動屢見報端。公共服務行業在從事業編制向市場化的轉型過程中往往會遭遇權益受損的問題。而這些弱者也可以依靠社會不同群體對他們所抱有的同情之心以及他們足以影響社會公共空間的“弱者的武器”來主動維權。因此,政府應正視這一群體勞資沖突的問題,以有效的機制補償他們受損的利益。
廣州新生鞋廠工人維權被拘
2014年8月,廣州番禺區新生飾物制品有限公司鞋部(新生鞋廠)開始搬廠。長期以來,資方在用工方面存在違法現象,如不為工人繳交社保、公積金,不安排帶薪年休假和法定節日休假,不支付加班工資、高溫津貼,不安排職業健康體檢等。此次搬廠行動也沒有跟工人協商安置方案。在一次交涉中,管理人員的一句話深深地刺痛了工人的自尊心:“你們做再多的貨,公司也決定只給發放番禺區最低工資。你們愛干就干,不干就自己辭職走人。”
2014年9月2日,在廣東勞維律師事務所的協助下,工人采用集體行動進行維權。他們向資方遞交了《訴求書》,向勞監部門遞交了《投訴書》,向廣州市總工會提交了《請求書》。此后,工人持續采用罷工、請愿等方式進行維權。
10月31日,廣州市政府有關領導向工人表態支持工人,要求政府相關部門嚴格執法,“不得強迫工人走勞動仲裁程序”,并在規定的期限內解決問題。
然而,事件在11月3日急轉直下。當天,200多警察出動對工人代表實施抓捕,有14位工人被帶走,其中7人被以“干擾企業經營罪”刑事拘留。該事件尚未有結果。
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出臺
除了以上具有代表性的一系列個案之外,廣東省在2014年也在制度推動上有所進步。2014年9月25日,《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由廣東省人大常務委員會通過,將于2015年1月1日起施行。這份以集體勞動關系的規制為主要內容的地方條例經過了數年的醞釀,經歷了勞資政多方的多輪博弈。
廣東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李煥新在一次研討會上用“八年抗戰,一而再再而三”來形容這部條例的立法進程。“由于資方——特別是香港六大商會的強力反對,該條例立法進程曾先后兩次暫停。此后由于廣東省主要領導的過問,才最終決定該條例不能停,立法要繼續。”
2013年10月,該條例的前身《廣東省企業集體協商和集體合同條例(修訂草案征求意見稿)》發布,向社會各界征求意見。大陸勞工界為此提交多份意見書,代表工人發出聲音。
2014年3月,《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修訂草案)》提交廣東省人大常委會審議。條例規定,只要有三分之一以上的職工提出邀約,企業老板就必須和職工集體協商工資和各項待遇。
4月15日,香港六大商會致函香港特首和內地13個相關政府部門,對條例出臺提出反對意見。5月15日,香港各界商會聯合會議在香港多家報紙刊登整版廣告,強烈反對該條例。香港商會曾經成功阻擊《勞動合同法》對于集體協商的相關規制,也成功迫使廣東省和深圳市放棄集體協商立法。
為回應香港商會的反對意見,大陸和香港的勞工組織、勞工學者紛紛發聲,在批評香港商會意見的同時,對條例提出了具體的修改意見。
2014年9月,《廣東省企業集體合同條例(修訂草案修改二稿征求意見稿)》發布,做出了有利于資方的諸多變動,尤其是“協商破裂后,工人有條件停工”的條款被刪除。9月25日,該條例正式發布。
對于“停工權”問題,李煥新在上述研討會上透露,全國人大法工委認為,這“涉及公民的基本權利,是憲法規定的范疇,是國家立法的使命,地方立法沒有這個權利”。再三請示全國人大法工委后,廣東省人大法工委最終將有關條款刪除。
本文簡述了幾個被媒體曝光,并在社會各界引起較大影響的典型事件。當然,還有一些其他事件同樣引發大規模關注,但是囿于篇幅不能盡述。
通過上述幾個事件,我們可以看到,工人越來越嫻熟于以集體行動的方式維權,其團結意識和組織能力都有了長足發展。不過,這些事件主要發生在南方,以珠三角最為典型,大多呈現出勞、資、政、工會、社會組織和力量多方互動且更為復雜的特點。工人在傳統抗爭的基礎上,以“集體談判”為標識、以法律為標準提出主要訴求,探索了勞工三權的實踐之路。一種工人抗爭觸發、多方參與互動、以權利爭議為特征的集體勞動爭議模式正在形成。但由于制度環境的不可預測性,能否發展成為一種成熟穩定的模式,尚需更長時間的觀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