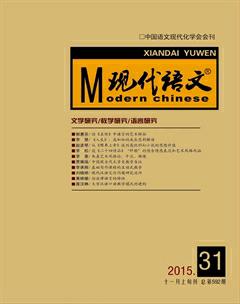論《左傳》中諫言的藝術特征
摘 要:《左傳》載有大量的諫言,這些諫言大多獨立成章,體系統一,情辭激切,理據充分,邏輯性強,呈現出獨特而鮮明的藝術特征:以“德禮”為敘述系統;以“義正辭嚴、怨而不怒”為風格特征;以引證、例證為主要論證手段。
關鍵詞:《左傳》 諫言 藝術特征
《周禮·司諫》注曰:“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在中國古代政治制度中,納諫與進諫是君臣之間的一種道德契約。《左傳》中載有大量的君臣對話,其中大多是臣下就君王不當或錯誤的言行、政策直言進諫、獻言獻策。這類諫言不同于后代興盛的書諫,不僅增加了歷史人物的血肉和厚度,對歷史事件的敘事有很大的作用,而且這些諫言大多獨立成章,體系統一,情辭激切,理據充分,邏輯性強,呈現出獨特而鮮明的藝術特征。
一、以“德禮”為敘述系統
《左傳》是為《春秋》作注,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明確說到“仲尼厄而作《春秋》”,所以關于《春秋》的作者,一般都認為是孔子。孔子一生以維護、恢復“周禮”為己任,然而身處亂世,孔夫子積極奔走卻收效甚微,只能將其恢復周禮的偉大理想訴諸筆端,留下了寓褒貶、別善惡的《春秋》一書。因此,《左傳》必然與周禮有著天然的聯系。有很多學者也把“德”“禮”作為先秦時期思想史的關鍵詞,作為史傳敘事的一部分,言諫敘事不可避免地染上了“德禮”的成分。更重要的是,對國君的勸諫都是因為國君不守禮、不修德,作為臣下,在對君王勸諫時,德禮就成了他們最合法、最有力的理論依據。
(1)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大廟。非禮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臨照百官,猶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 左傳·桓公二年》)
臧哀伯明確地說:“作為百姓的君主,要發揚道德而阻塞邪惡,以為百官的表率,即使這樣,仍然擔心有所失誤,所以顯揚美德以示范于子孫。”
(2)蔡侯歸自晉,入于鄭。鄭伯享之,不敬。子產曰:“蔡侯其不免乎?日其過此也,君使子展勞于東門之外,而傲。吾曰:‘猶將更之。今還,受享而惰,乃其心也……其為君也,淫而不父。僑聞之,如是者,恒有子禍。”(《左傳·襄公二十八年》)
蔡景侯從晉國回國,鄭簡公設享禮宴請他,他卻表現得不恭敬,子產由此對鄭公說出了這樣一番勸諫之言:“蔡侯恐怕要不免于禍難了吧。”因為身為國君的景侯傲、惰、淫,都表現了對禮的不敬。終于,襄公三十年“太子弒景候”。從這個例子中我們可以看出,內心恭敬、循禮,是人君必備的素養。
(3)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于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左傳·昭公五年》)
其后,女叔齊進一步揭示了魯侯只是“儀”,而非“禮”。他認為禮是用來保護國家,推行政令,不失去人民的;而昭公違反大國的盟約,欺凌虐待小國,利用別人的禍難,不憂慮自己地位的岌岌可危,對禮本末倒置。可謂以“禮”為據,大膽揭露,毫不留情。
以上諸例均反映出德禮系統在《左傳》的言諫敘事中所承擔的角色,而且德禮有點不分家。顧頡剛、劉起釪也認為:“所謂的禮就是有德者的行為儀節的規范化。”春秋時期禮崩樂壞,很多人要求恢復周朝禮制傳統,在勸諫時用禮諫就顯得很自然。在現實中,德是勸諫的策略和準則,在歷史敘事中則使言諫的存在具有了歷史的意義,所謂“前事不忘,后事之師”。
二、以“義正辭嚴、怨而不怒”為風格特征
同《左傳》中行人辭令委曲達意、婉而有致的特征不同,《左傳》中的諫言明顯地呈現出義正辭嚴、怨而不怒的風格特征。諫臣以“德禮”為敘述依據,他們匡君之過、矯君之失的舉動就有了強有力的支撐,充分表現出諫者的正義與責任,編者也時而借他人之口對他們的勇氣與卓識給予熱烈的歌頌。如“季梁諫追楚師”(《左傳·桓公六年》)、“司馬子魚諫宋公勿以人祭祀”(《左傳·僖公十九年》)、“蹇叔諫秦穆公勿伐鄭”(《左傳·僖公三十二年》),等等。由于這些諫言都是為了進善衛道、匡救君失、拯世濟民,所以諫辭疏直激切、詞氣慷慨、義正辭嚴,充分體現了進諫者胸懷坦蕩、光明磊落、無所畏懼的大丈夫品格。
但另一方面,與行人辭令以“智”為靈魂不同,諫言以“忠”為中心,森嚴的等級制度要求人臣對君王忠貞順從,“敬王命,順之道也”(《左傳·周語上》);而諫臣的使命又是“諫過”,因此諫臣很容易陷入一種尷尬境地,不諫是罪,諫也是罪。“諫”體現了忠心與職責,“不諫”是不忠與失職,話語權完全掌控在君王手中,“諫”而不中聽也會罹罪。于是,除了講究諫之技巧之外,在諫言風格上也明顯呈現出“險而不懟,怨而不怒”的特點,也就是對君王的違禮行為,心中雖然怨恨不滿,也不會情緒失控,怒形于色,而《左傳》中的言諫大多數則以“王弗聽”而遭拒斥,諫臣也大多不了了之。說得直白一點,就是“說不說在我,聽不聽在你”,而“我”不動氣、不動怒,不會因為自己動怒而加劇當權者的怒進而加速了自己的死亡,但以“忠”為精神核心的諫臣雖“怨而不怒”,但也有用自己的方式改寫“王弗聽”這結果的例子。
如“石碏諫寵州吁”(《左傳·隱公三年》)里,石碏為了勸諫莊公不要過分溺愛州吁,先分析了導致邪惡的四種惡習,然后正反假設論證立不立州吁為太子的區別,再正反羅列了六種背理和順理的事,可謂據理力爭、辭懇意切、頭頭是道,但莊公仍“弗聽”。石碏“其子厚與州吁游”,石碏“禁之”,然“不可”,等到桓公即位,石碏告老還鄉。后來州吁果然變本加厲,暴虐異常,殺死衛桓公而自立為君,石碏借陳國之手殺了州吁,自己派人殺了自己的兒子,即所謂為救國而“大義滅親”。自始至終,石碏并沒有因為勸諫受阻而怒,而是用行動解救了國難,于是編者在《左傳·隱公四年》中借“君子”之口大力表揚石碏為“純臣”。
三、以引證與例證為主要論證手段
(4)公曰:“吾享祀豐潔,神必據我。”對曰:“臣聞之,鬼神非人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則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馮依,將在德矣。若晉取虞而明德以薦馨香,神其吐之乎?”(左傳·僖公五年)
這段文字引自《左傳·僖公五年》中有名的“宮之奇諫假道”,它典型地反映了《左傳》在藝術手段方面的特色,即經常引用歷史故事、古人名言或《詩經》《尚書》等典籍中的語句,乃至諺語民謠來進行論證。
進諫者若既要盡到為人臣“忠”的職責,又要保住自己的腦袋,必須在諫言的技巧上狠下工夫,既達到諫的目的,又實現對“忠”的追求。外交辭令雖以婉曲為主要特征,但有時為了達成效果,使臣也會十分熟練地使用對比和反問,以求把利害關系一目了然地擺出來,如“燭之武退秦師”(《左傳·僖公三十三年》)中,燭之武為秦穆公清楚地羅列了“亡鄭無益而有害”與“舍鄭有益而無害”,利弊明顯,又進一步用反問挑撥離間——“夫晉何厭之有?”“不闕秦,將焉取之?”與此很不相同的一點是,諫言擅長論證,除了引證法之外,也通過大量喻證法、例證法展開論證。這是因為考慮到進諫者與君主之間對話地位的不平等和諫言本身的目的性,就必須顧及君主的心理變化,既要用十分有力而充分的論證予以闡明,又要采取一些聰明而巧妙的技巧,把道理說得形象,把指責說得委婉。
(5)夏,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左傳·成公四年》)
(6)秋,公至自晉,欲求成于楚而叛晉,季文子曰:“不可。晉雖無道,未可叛也。國大臣睦,而邇于我,諸侯聽焉,未可以貳。《史佚之志》有之,曰:‘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楚雖大,非吾族也,其肯字我乎?”公乃止。(《左傳·成公四年》)
以上兩例均出自《左傳·成公四年》,季文子為了勸諫魯成公,引用《詩》《史佚之志》之言作為例證。
(7)……越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大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左傳·哀公元年》)
例(7)中,越王勾踐與吳王夫差交戰,越王退守到會稽山,并派大夫文鐘通過吳國太宰伯嚭去求和。吳王夫差準備同意越國的請求,伍員勸阻。他先以諺語鋪墊“樹立德行不如越多越好,去除病痛不如越徹底越好”。然后又講述了一個留下后患的例子證明不可放過越王,接著又比較了越國和少康的實力,說:“比越國弱小的少康都能東山再起,何況越國呢?在我們戰勝越國時不把它滅掉,卻要保存它,這就違背了天意,助長了仇敵,日后即使后悔,也無法消除禍患了。”可惜吳王“弗聽”,事實果然如伍員所說:“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為沼乎!”
值得一提的是,技巧終是表皮。對照僖公十三年和十四年,晉國鬧饑荒時,秦穆公問臣下給不給晉國糧食,有的說給,有的說不給,有的請求乘此機會攻打晉國,而秦公說:“我們厭惡他的國君,他的百姓有什么罪呢?給!”他的臣子也沒發表多言論。但到了十四年,秦國鬧饑荒了,派人到晉國購買糧食,晉國不同意。慶鄭列舉了不仁不孝不義的行為,又運用了反問“何以守國?”“棄信背鄰,患孰恤之?”“近猶仇之,況怨敵乎?”終究是“弗聽”。“多行不義,必自斃”,晉公最終沒有好下場。臣下說得好不好真不是關鍵,關鍵還在于“受諫”之君王從主觀上是如何決策的。
(基金項目:本文為江蘇高校哲學社會科學研究指導項目“先秦諫言文學研究”[編號:2015SJD384]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
[1]左丘明.左傳[M].北京:中華書局,2014.
[2]何等紅.《左傳》諫例敘事研究之敘事模式[J].齊齊哈爾大學學報,2015,(1).
[3]寧登國.論《國語》《左傳》的諫體文學特征[J].殷都學刊,2008,(29).
[4]何等紅.淺析言諫敘事中語境話語敘述[J].銅仁學院學報,2005,(1).
(郭惠芬 無錫城市職業技術學院 2141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