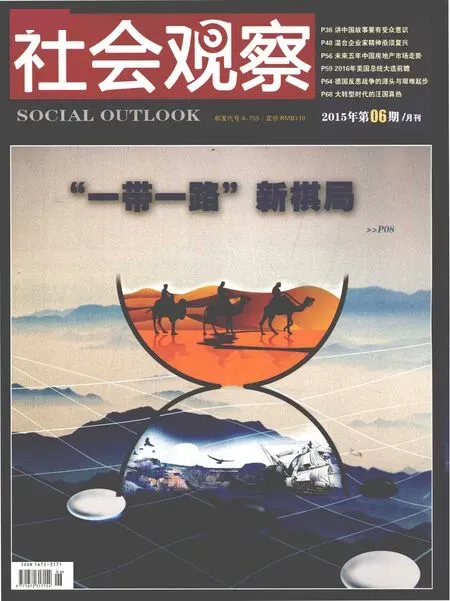“一帶一路”與中國外交轉型
文/黃軍甫
胡錦濤主席時期倡導的和平發展戰略及“政治上平等民主,經濟上互利合作,文化上交流共進”為特征的和諧世界的構想,是中國外交轉型初露端倪的具體體現;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則是中國外交轉型輪廓清晰化的重要標志。
2013年9月習近平主席出訪哈薩克斯坦及同年10月出訪印度尼西亞時,分別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一石激起千層浪。習主席倡議甫一提出即引起全球學者、政要及各路商家的廣泛關注。“一帶一路”戰略基于何種背景、動機,欲達到何種目標,一時間,眾說紛紜,莫衷一是。由于人們身份、背景的不同,也由于個人的認知差異、價值訴求和利益導向的差異,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的態度和評價至今達不成共識。在新加坡學者鄭永年看來,對“一帶一路”戰略,國際社會的態度大致可分為三類:一是與“一帶一路”戰略構想相關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是中亞、西亞及南亞各國,由于它們基礎設施落后,資金嚴重不足,經濟發展內生動力不足,所以對“一帶一路”戰略總體持支持態度;二是現有世界秩序的既得利益者,諸如美國和日本,對“一帶一路”戰略發自內心的厭惡和百般抗拒;三是一些國家既想分享“一帶一路”戰略可能的好處,又畏懼美、日壓力,以及擔憂“一帶一路”戰略實施中的某些不確定性,因而持懷疑、觀望態度。
如何順利推進“一帶一路”戰略,減少推進過程中不必要的摩擦、沖突甚至對抗,使中間力量放下包袱,反對力量消除敵意,關鍵是我們必須將“一帶一路”戰略的總體構想、基本原則、目標模式等問題向國際社會進行深度解讀和廣泛宣傳。
中國崛起引發美國遏制戰略
就2015年3月28日我國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的內容來看,筆者認為,“一帶一路”戰略,是在冷戰結束之后,世界政治經濟格局及中國綜合國力和改革開放水平都發生了質的變化背景下,中國新一屆政府審時度勢,以新的視野、新的理念應對變化,從而“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國際合作的全球安全戰略。根據《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這一戰略是在遵守現有國際秩序準則,發揮現有世界治理機制及利用多重國際合作機制的前提下,“以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為主要內容”,各個國際行為主體、經濟組織和平合作、相向而行,從而實現“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目標建構。顯然,這一戰略有中國新一屆政府改變國內經濟發展戰略、提升改革開放水平的具體考量,但在更宏觀的層面上則凸顯了中國外交政策的轉型。
國際關系的實質是國際關系行為主體的利益關系。無論何時何地,外交都是服務于國內政策的。改革開放迄今,基于國內經濟發展的考量,中國的對外政策微觀調整不斷,但總體戰略卻變化不多。
大體而論,可以分為兩個階段:第二代領導集體和第三代領導集體執政時期為一個階段,十六大之后的一屆領導集體執政開始到今天為第二個階段。第一階段,世界格局處在冷戰和后冷戰時期,全球化水平不高,東西方對抗尚未消解。而這一時期的中國,無論經濟發展,還是改革開放的水平都比較低。據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國際風云變幻的1989年,中國的GDP僅有3439.7億美元,大致是美國的1/16,日本的1/9。蘇聯解體,也就是冷戰格局結束的1991年,中國的GDP只有3794.7億美元,而同期美國的GDP為61740億美元,日本的為35368億美元,衰退中的俄羅斯GDP為5093.8億美元。冷戰格局瓦解后的2003年,中國的GDP也僅占全球GDP的3.8%,而同期美國GDP占全球28%。所以,這一時期,經濟發展所需的資金、技術、管理經驗,中國都有求于西方,尤其是美日這樣的大國,中國因而處在一種被動服從國際秩序的狀態。這樣,為了減少摩擦,避免與大國沖突 ,我們只能避其鋒芒,委曲求全。面對當時復雜的國際局勢,鄧小平在冷戰格局瓦解之初告誡國人:“冷靜觀察、穩住陣腳、沉著應對、韜光養晦、善于守拙、決不當頭、抓住機遇、有所作為。”鄧小平高屋建瓴,僅用32個字即描繪了當時中國政府處理國際國內問題的方略。鄧小平這一方略表現在外交上就是韜光養晦,不與西方大國尤其是美國正面對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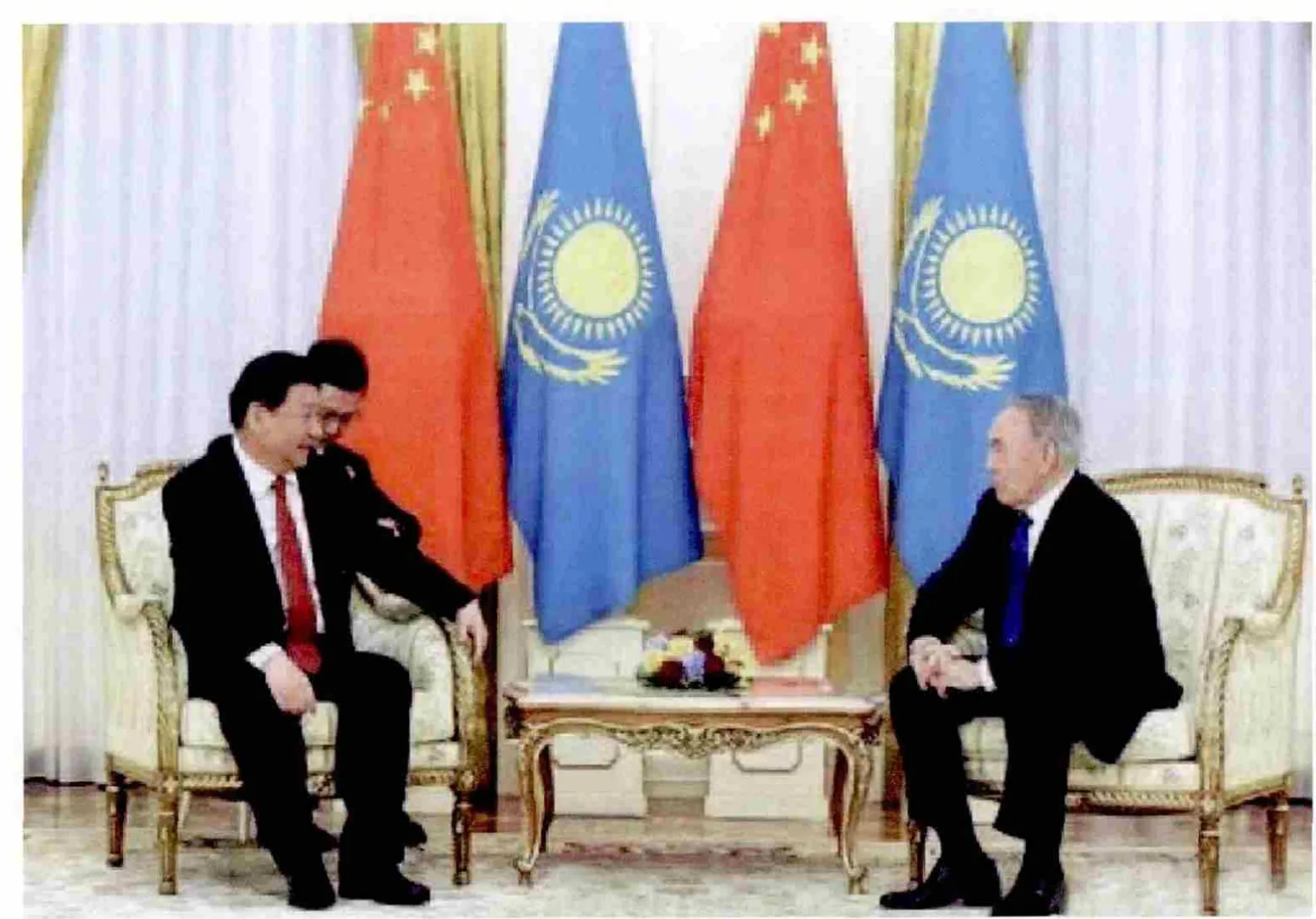
2013年9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訪哈薩克斯坦期間,首次提出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倡議。 圖/新華網
縱觀1978年到2002年,中國的外交政策其間雖有小的調整,但總的脈絡是韜光養晦。這一方略雖然在特定情境里,在涉及某些國家核心利益問題和民族感情問題上,中國有讓步、有屈辱,但它卻是中國當時為了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大業必須奉行的政策。它是由世界格局和中國的國力決定的。這一方略對中國此后經濟的長期高速發展產生了不可估量的積極效果。當然,這一時期中國之所以能夠較為順利地實施韜光養晦的外交,一個重要的因素是西方尤其是美國當時對中國的認知和態度。韜光養晦,按照美國學者的解讀,就是“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即“掩蓋自身力量,等待時機,東山再起”。這一解讀顯然是不懷好意的曲解。問題在于,美國人既然擔心中國人等待時機,秋后算賬,何以袖手旁觀,任憑中國坐大?關鍵在于,中國當時國力弱,不足以對西方構成挑戰。美國認為中國不但不構成威脅,反而認為崛起的中國是抗衡蘇聯(及后來的俄羅斯)的戰略力量。從歷史和地緣政治考量,蘇聯(俄羅斯)才是西方的最大威脅。為了借助中國反制俄國,自1972年尼克松訪華開始,美國一直鼓勵、支持中國發展、開放以及參與全球化,以期中國既有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形態最終“融入自由國際秩序”。
冷戰之后,尤其是進入21世紀以后,中國的綜合國力大幅度提升,世界力量對比發生了很大變化。2013年,中國的GDP已達91850億美元,占全球GDP的12%左右,而美國GDP為167975億美元,雖然仍穩居全球第一,但伴隨全球化所帶來的紅利,新興市場經濟國家,尤其是金磚國家迅速崛起,美國在全球經濟中的份額迅速下降,由1991年占全球經濟總量的34%左右下降到2013年的20%左右。特別是2008年導源于美國的金融危機,打破了冷戰后全球范圍內生產與消費的脆弱平衡。馬克思意義上的經濟危機越來越向著深度和廣度發展。隨著世界經濟力量的變化以及經濟危機的延展,國際政治格局也處在急劇變化中。世界格局多極化,國際關系民主化,以及建立適應全球化的世界秩序和世界治理機制,成了全球多數國家的強烈訴求。
在變化了的世界面前,西方國家尤其是美國開始重新定義自己和中國。美國外交關系協會最近發表的特別報告《修訂美國對中國的大戰略》,再明顯不過地暴露了美國決策者的內心世界。該報告認為,中國迅速崛起,且“美國讓中國融入自由國際秩序的努力如今已對美國在亞洲的主導地位產生新的威脅,并且最終可能對美國全球影響力構成重大挑戰,華盛頓需要針對中國出臺新的大戰略,核心是遏制中國影響力的上升,而不是繼續協助其崛起”。為此目標,美國精英提出要聯合盟國尤其是諸如日本、菲律賓等亞洲盟國,對中國實施遏制。這是一種非常危險的新冷戰信號,如果變為外交政策,它將對中美關系及兩國利益,甚至世界格局產生極大的負面影響。
不幸的是,大體自2001年起,美國政府即開始逐漸推行圍堵中國的政策。小布什入主白宮伊始便公開表示,中美不是朋友和戰略伙伴,而是對手。2002年3月,《洛杉磯時報》曝光了一份美國國防部遞交給國會的機密報告《核態勢評估》,公然把中國與俄羅斯、朝鮮、敘利亞、利比亞等列為未來可能的核打擊對象國。2006年9月,普林斯頓大學一批學者在有官方背景的福特基金會的支持下,炮制了一份《鑄造法治下的自由世界——21世紀美國國家安全戰略》(即通常講的《普林斯頓報告》)。該報告聲稱,“美國及其盟國在二戰后所建立的、在冷戰期間穩步擴展的國際制度體系,已經破裂”,“美國顯然不能再依靠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組織”,為此,美國“必須與其友邦及盟國共同努力,創立一個全球性的‘民主國家共同體’,即一項旨在加強世界自由民主國家安全合作的新制度。這個共同體將使‘民主和平’得以確認并制度化。如果聯合國無法進行成功的改革,民主共同體就將為自由民主國家提供一個替代性論壇,以超級多數表決的形式,授權包括使用武力在內的集體行動”。雖然該報告不主張公開遏制中國,甚至聲稱“幫助中國在當前的國際秩序中實現其正當合理的抱負”,但報告中所主張的所謂自由民主國家的合作及集體行動顯然主要是對準中俄等國家的。這也促使奧巴馬入主白宮不久便宣布美國重返亞洲,并深度介入南中國海、釣魚島等關乎中國核心利益的問題。美國著名智庫蘭德公司更是在2011年推出一份研究報告,警示美國政府中美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的沖突不可避免,并危言聳聽地講:在朝鮮、臺灣、網絡空間、南中國海、中日關系、中印關系等6個問題上,中美可能沖突并可能引發為戰爭。
在美國朝野不絕于耳的對中國韃伐聲中,奧巴馬開始了他的第二屆總統任期,并隨即加緊了對中國的圍堵和遏制。尤其是今年以來,美國針對中國頻頻出手,先是重申“亞太再平衡戰略”,后又與日本簽署《新合作防衛指針》。這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和國家安全的極大挑戰。
中國外交轉型勢在必行
世界已發生了深刻變化,西方對我們的態度和政策也發生了變化。我們必須直面變化,接受挑戰,并為此調整我們的外交政策。
其實,十六大后的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已開始悄悄地調整我國的對外政策。十八大之后,中國外交轉型的輪廓日益清晰。既然作為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已無法再掩藏自身實力,既然西方國家開始視中國為威脅而不允許我們低調行事,那么,過去那種一味地避人鋒芒、妥協退讓的韜光養晦外交政策必須適時調整,實現轉型。這種轉型,中心內容是在不拋棄韜光養晦精神的前提下,改變過去的某些做法,在外交實踐中,在一系列重要問題上積極進取,有所作為。具體講,在涉及國家主權、領土完整、經濟社會發展、基本政治制度和主流文化以及民族尊嚴、民族感情等核心國家利益和原則問題上,決不妥協,決不讓步,以斗爭求合作,求和平;以機動靈活的策略應對各種挑戰,把握斗爭的分寸,不做無原則的斗爭,不因斗爭而使雙邊及多邊關系破裂;對于諸如現有國際機制的改革、新的世界治理機制建構及具體的地區事務、熱點問題等要積極介入、參與,做負責任的大國;外交政策始終服務于國內的經濟社會發展及國家地緣政治安全。
胡錦濤主席時期倡導的和平發展戰略及“政治上平等民主,經濟上互利合作,文化上交流共進”為特征的和諧世界的構想,是中國外交轉型初露端倪的具體體現。而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一帶一路”戰略,則是中國外交轉型輪廓清晰化的重要標志。
當然,一味的韜光養晦、妥協退讓注定沒有將來,但一味地沖突、對抗更沒有希望。如果中國不在崛起過程中妥善處理與外部世界尤其是與美國等既得利益國家的關系,從而使沖突、對抗不可管控而引發戰爭,將會對全球經濟帶來毀滅性的后果。有專家估計,僅南中國海地區若發生中美間的局部戰爭,便會給相關國家造成至少4萬億美元的經濟損失。倘如此,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將會受到顛覆性影響。
推進“一帶一路”戰略,就是本著“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綢之路精神,世界各國相向而行,探索國際合作及全球治理的新模式,從而避開基于彼此猜疑的囚徒困境和新型國家崛起過程中的修昔底德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