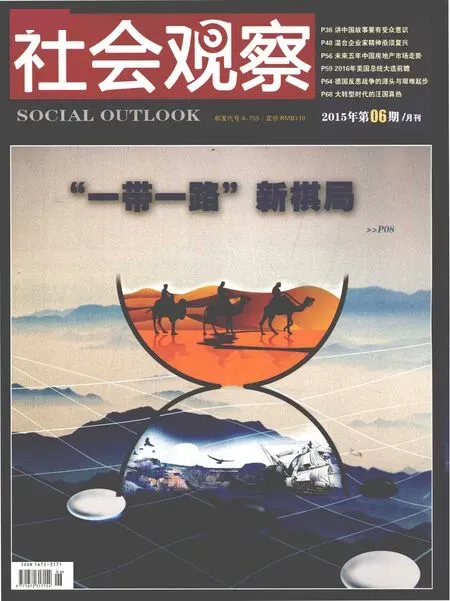以文化共融塑造絲路精神
文/倪稼民
“一帶一路”是謀求共同合作發展的理念、藍圖和倡議。如何讓理想成為現實,除了依靠中國與沿途沿線國家和地區既有的雙邊多邊合作機制、充分研究論證各種可行性和風險預測、唱好經濟發展互惠共贏這出戲以外,也需要著力搭建文化認同共融這座平臺。
“一帶一路”并不是一個實體和機制,而是謀求共同合作發展的理念、藍圖和倡議。如何讓理想成為現實,除了依靠中國與沿途沿線國家和地區既有的雙邊多邊合作機制、充分研究論證各種可行性和風險預測、唱好經濟發展互惠共贏這出戲以外,更需要著力搭建文化認同共融這座平臺。前者是顯性的、眼前的,后者是隱性的,但卻是長遠的。
文化共通是新老絲綢之路的前提
人類學家不斷證實:不同族群和文化背景的人之所以能夠交流合作,首先應該歸功于人類固有的文化共通性,即由人類生理機制的一致與人類心理本性的相同,導致不同族群的初始文化在一些觀念、幻想、習俗、欲望甚至價值觀上驚人相似。神話和宗教通常被認為是我們了解人類起始生活的腳本。盡管不同地域、不同部族的神話作品體現出形式與內容上的多樣性和差異性,而不同的宗教其具體教義、信條以及體系也不盡相同,有的甚至對立沖突幾乎不可調和;然而,諸神的品格、性情、功能以及這些神話、宗教所傳遞的價值信息和反映的思維方式卻存在實質上的相近性和內在的統一性。
比較系統的全球指向的文化價值理念,在古代的東西方文化中都能夠發現其源頭:在中國,《禮記》的“大同說”是其代表,在西方,則可以追溯至古希臘晚期的斯多葛派,這些思想倡導“世界大同”、“人類普遍理性”和宇宙人生哲學,可以說是真正意義的全球主義思想的濫觴。
人類正是基于這種與生俱來的共通性和內在的沖動及生存發展的需求,才能得以從封閉的、隔絕的、地域的走向開放的、聯系的、世界的,于是就有了海陸古絲綢之路。絡繹于途的絲綢、瓷器、香料、茶葉等商品貿易和多種文化碰撞交匯將中國與亞、歐、非三大洲的不同國家和族群聯系起來,既體現了中國人沖破阻隔、交流互鑒的膽魄和毅力,也使中國開始了解世界并影響世界,為推動東西方經濟文化交流交融、人類文明多樣化發展譜寫了重要的歷史篇章。而處于全球化大潮的當今世界,提出確認和建立人類共同價值和發展共同體實際上已不僅僅是美好的愿望,更是現實的需要。縱觀激蕩的百年史,人類面臨的環境危機、戰爭威脅和諸多的全球性問題的困擾,使人類越來越產生被綁在一起的感覺,越來越體驗到利害交織在一起的事實,也越來越意識到人類進行全球治理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在這種背景下,中國倡導共建“一帶一路”,其影響廣大、意義深遠,不僅只是意識、領悟到開放和融入世界的必要,更是對人類面臨共同問題、危機的深刻體認:其主旨即借用古絲綢之路的歷史符號,在和平發展的旗幟下,主動地發展與沿途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經濟合作伙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把握“一”與“多”的關系
當然,僅僅承認人類文化共通還是難以實現這種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的,我們還要回答這種共通是基于什么樣的標準?怎么解決普世與特殊的矛盾?試看18、19世紀的全球主義者(基本上是歐洲人)關注的其實是一種歐洲的“全球性”,本質上就是“西方中心論”和“西方一元論”,他們(如萊布尼茨、康德、空想社會主義者甚至包括馬克思等)在很大程度上忽視或低估了種族和宗教這一深深植根于族群文化的堅韌和保守力量(或在轉型為民族主義后)在現代性中的頑強作用;而當代較多的全球主義者(如湯因比)又超越了民族國家依然還是目前世界經濟政治文化主導的事實,主張突破民族國家,建立世界性機構,顯得過于理想化。再看現實,在全球主義使命的表象后面,帝國主義權力游戲一幕又一幕上演,西方發達國家利用強勢賦予其政治經濟制度以普世主義的使命,并竭力從“世界共同利益、共同命運和共同責任”中獲得更多更新的權力資源,而更多的落后的東方國家則感受到的卻是腥風血雨般的悲慘、凄苦和絕望。正如存在主義大師薩特曾尖銳地揭露西方的這種虛假普世主義那樣:“我知道這些關于自由、平等、博愛、愛情、榮譽、祖國的廢話,它們無礙于我們同時堅持種族主義的說法:骯臟的黑人、猶太人、阿拉伯人。……在我們這里沒有任何事情比種族人道主義更為始終如一,因為歐洲人只有通過制造奴隸和怪物,才能使自己成為人。”不可否認,這種“普世主義”在行進中確實突破了地域和傳統的樊籬,但卻是以排斥或消弭非西方文化來解決普世性與多樣性(即“一”和“多”)問題的文化帝國主義方式展開的,從而引發和加劇了非西方弱勢社會的那種強烈的被壓抑、被異化和被剝奪感,造成更大的緊張和隔閡。在這種背景下,作為已經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崛起中的中國,在提出共建“一帶一路”戰略構想時,不能排除可能會引發周遭眾多的發展中國家對殖民地歷史的痛苦的集體回憶,以及對新帝國主義的警惕,不能排除他們在希冀獲取經濟發展的同時會表現出本能的保守和不信任感。
中國倡導“一帶一路”,打贏經濟合作發展之戰,就必然需要一種道德力量支撐。這種道德力量不是凌駕于一切民族文化之上的絕對律令,更不是某一種強勢文化居高臨下的宰制,而是從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中提升出最具人性的、最賦予生命真諦的人類共性。
如何消解沿途眾多發展中國家的疑慮和擔憂,關鍵就在于我們將怎樣詮釋和處理“我們—他們”文化中的普世性(即“一”)與“我們—他們”文化中的特殊性(即“多”)的關系,也就是要尋找到將普世主義特殊化和特殊主義普世化雙向良性互動的中軸,既不固執于本土特殊性的文化原教旨主義,又反對將自身文化普世化。就中國而言,既要弘揚和挖掘我們傳統文化中富有特色但又有普世意義和吸引力的一面,又要虛心地承認和吸取他國文化中值得學習借鑒的精華的一面,承認任何一種文化都有其共通的一面又有其獨特的一面,如同孔子、老莊、蘇格拉底、阿威羅伊到近現代的康德、托爾斯泰等思想作品,既彰顯了民族文化的輝煌燦爛又已經成為世界文化的豐碩成果而為世人所認同。所以,我們更應該主動、誠意、平等地與沿途國家和地區進行各種形式、內容和層面的交流與對話,切不可因為擁有一定的經濟、政治、財富、資源等優勢而顯出盛氣凌人或頤指氣使的傾向,否則不僅將消解自身對世界和平與發展的貢獻,而且本身的安全也會受到危害。對相對弱勢國家或民族來說,強化本土性和民族認同意識固然必要,但如果這種民族認同變成了一種排他性的原教旨主義、封閉主義,就有可能造成文明沖突而更加延緩了發展步伐,所以最重要的方式也是對話。這就是說,各方都應該看到差異,承認多樣性,在和諧中抱持獨特,在尊異中求同。這種同一不是以強勢壓倒弱勢的文化霸權主宰方式進行,而是能夠像哈貝馬斯的“交往行為理論”所提倡的那樣,先在不同的族群、不同的文化之間進行對話、商談,取得共識后再制定出一個共同遵守的規則。
任何一種現成的特殊的文化體系都不可能或根本沒有資格充當作為人類文化共通的“一”的全部樣板,它必須是基于國際社會公共理性和多元文化之間的“全體對話”,以達成一種合乎理性的“重疊共識”(羅爾斯),從而最終形成一種可以為所有信奉不同宗教和道德觀念、承接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們所共同認可和踐行的普遍正義的價值觀念。“一帶一路”所期盼的利益、命運和責任共同體只有基于這樣一種“一”與“多”的對立統一關系,才能獲得成功和持續久遠。
塑造作為道德力量的文化共識

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還需加強文化交流。圖為2015年5月14日,第十一屆中國(深圳)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以“一帶一路”為主題,首次設立“絲綢之路專館”,引來各方熱切關注。 圖/CFP
事實上,純粹的普世文化是不存在的。所謂文化的普世性、共性總是相對于文化的特殊性、多樣性而言,離開了特殊性和多樣性的普世性和共性是空泛和無意義的。普世性、共性、統一性如果是在抹殺特殊性、個性和多樣性的基礎上顯現,那么,文化就喪失了過去,也就喪失了認同感、自尊心、方向感和創造力。
文化首先是地方性、民族性的,任何跨文化傳統的價值目標和價值認同都必須基于這一前提,它關系到一個民族和國家的生存理由和命運,除非人類世界已不再有國家、民族存在。人類所有偉大的成就都深深地烙上民族的、地方的和個人的印記,但是從人文意義來看,它們又都超越了這種特殊性和個體性。真正的民族文化精華是既在塑造性格、心靈和想象力的過程中張揚個性,又在賦予生命和生機的價值層面中彰顯普世性、共性或統一性。“凡是歷史上鮮明、具體和特殊的東西,現在都成了真善美的載體并從而增強了普世價值的內涵”,所以,普世性就本質而言是一種道德力量,甚至美與真都最終依賴于這種力量(克萊斯·瑞恩)。
中國倡導“一帶一路”,打贏經濟合作發展之戰,就必然需要這樣一種道德力量支撐。這種道德力量不是凌駕于一切民族文化之上的絕對律令,更不是某一種強勢文化居高臨下的宰制,而是從不同民族文化的多樣性中提升出最具人性的、最賦予生命真諦的人類共性。這種文化揚棄了多樣性中狹隘、自私、頹廢、鹵莽和殘忍,洗練出人性中博大、寬容、進取、溫和及謙讓。這種文化要求各個民族“從自己切身的文化關懷出發,培養像托爾斯泰、愛因斯坦和甘地這樣的博大胸懷,在這個被種族、宗教、語言、文化分裂及至破壞的世界上,面對人類共同的問題和困境,不但負起對自己的命運,而且也負起對全人類命運的道德責任”(王緝思)。只有這種道德力量,才能真正讓沿途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交相輝映、激蕩匯合,積淀形成“和平、開放、包容、互信、互利”的絲綢之路精神,只有這種道德力量,才能永葆絲路精神為沿途各國各民族認同和推崇,并不斷注入時代內涵,造福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