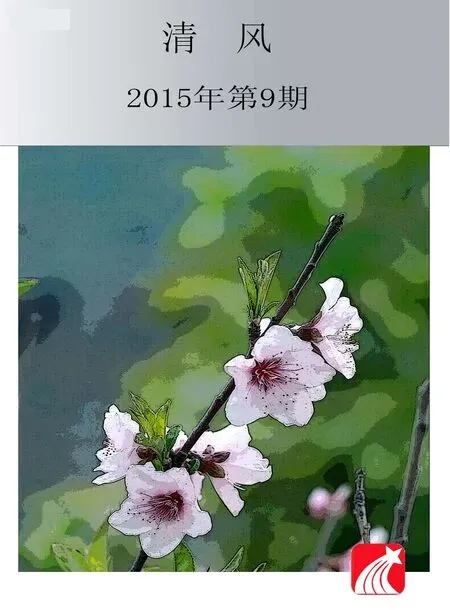“辮子定律”與“黑暗森林猜疑鏈”
文_林永芳
“辮子定律”與“黑暗森林猜疑鏈”
文_林永芳
有則言簡意賅的段子,一度刷爆微信朋友圈:“人生四大心愿:不勞而獲;不學而慧;無傷有愛;暴食不胖。”人們會心一笑,競相轉發,當然,大抵沒人會拿它當真。可你若認為它只是無意義的調侃,那就未免太天真了。事實上,凡能博得大眾不約而同轉發的東西,一定有其擊中人心、激發共鳴之處。換言之,上述每一個“心愿”,都抓住了人性的某個要害,折射出人類內心深處的隱秘渴盼:既希望占有盡可能多的優質資源,又不想付出辛勞和代價。而這,不正是騙子們最喜歡的“人性漏洞”嗎?
有漏洞方能乘虛而入,有辮子乃可一把揪住,肆意刷新“行騙史”上的種種紀錄。這一現象,不妨稱之為騙子的“辮子定律”。化用1793年法國大革命時期羅蘭夫人被送上斷頭臺時的那句吶喊——“人性小辮子”,多少騙局假汝以行!正因為成功的騙子都是心理學或人類學大師,所以才能像女士們接過快遞商品后三下五除二地撕掉外包裝一樣,迅速剝開種種道德偽飾,直抵人性本質。
比如,你說你黨性修養強、意志堅如鋼,我卻看見“柳下惠”的皮袍里分明長著登徒子的辮子,只要送你“趙紅霞”,你遲早會做“雷政富”;甚至,只需隨便撒出一迭移花接木無中生有的合成艷照,也能擊中那么幾根軟肋。前者可稱之為“種下‘情人’,長出鈔票”;后者干脆就是“冒充‘情人’,冒出鈔票”。
而與“冒充情人”不相上下的另一類騙局,則是“冒充領導”乃至“冒充高層”。許多人都接到過“我是某某領導,明天到我辦公室來一趟”的詐騙電話,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了:那是陷阱。可此類“小兒科”詐騙電話偏偏并未隨之消失,可見這門“生意”依然有利可圖。換言之,后腦勺長有“媚上”小辮子的人依然多得足以供養電話那頭那些煞有介事的“領導”。
至于幾年前轟動一時的著名官場騙子趙錫永,更是堪稱“騙界”的“勵志楷模”——以“國務院政策研究室司長”甚至“副部級官員”的身份四處為地方經濟“把脈”, 騙遍遼、湘、滇、魯、京、滬,獲得了從一些省領導到市主官,從一些企業老總到專家學者的一致敬佩。直到案發,被騙者依然衷心承認他“作報告令人折服,引進的項目運轉良好”,感嘆“這么有才的一個人,沒走正道可惜了”。
換言之,憑個人素質實力,趙完全可以勝任其假冒“國字號領導”所做的那些事,為何非要令人匪夷所思地冒充“國務院官員”呢?是否因為他深知,越是官場中人,越是從骨子里就根深蒂固地長著“只重衣冠(頭銜)不重人”的“心理小辮子”,若不借用“京官”大帽子,很難順利取信于他們,實現自己“只想在退休前實實在在地做一些事”的“抱負”?
的確,就連識字不多的農民都知道把自己“塑造”成“聯合國官員”,便可坐火車不給錢、騎摩托不帶證,甚至闖進監獄頤指氣使要提走在押犯人。
再者,那些所謂的風水大師、氣功大師,“玄之又玄”地讓一些官員不信馬列信鬼神,僅因“大師”一句話就能拆掉一座樓,僅憑“大師”的一句點撥,竟能讓某省部級高官跪倒俯首。
關于騙子的每則故事都貌似荒誕,卻又自有其得以“生存”的現實邏輯——首先是對“權有制”現實的深刻洞察、對高級權力的“習慣性敬畏”,一旦自稱高官,立即獲得了“免于被懷疑的自由”。其二是對項目、官位等的強烈渴求,強烈到恰似熱戀中人,一看見所愛之物,立即眉開眼笑智商降到零。
但歸根結底,還是在于對“潛規則”的迷信。比如,在“冒充高官”型的騙局中,騙與被騙雙方都相信,“高級職務”一定可以帶來“高級好處”;而在雷政富式“色誘官員”乃至“合成艷照敲詐”型的騙局中,騙子的“理論自信”與“道路自信”在于,認定“官員都是有縫的蛋”,要么已有桃色把柄,要么架不住桃色炸彈,只要功夫深,遲早墮入彀中。要怎樣的權力生態,經歷怎樣的漫長浸染,才能熏陶出這樣一套陰暗的官場與民間的社會心理?
說到這里,不得不提一提同樣彌漫于官場與民間的“黑暗森林猜疑鏈”。化用當代著名科幻小說作家劉慈欣在《三體2》中提出的宇宙社會學核心理論“黑暗森林法則”以及“猜疑鏈”概念,那就是,人人都認為,社會就是一座黑暗森林,在這片森林中,人人都很可能已在私下里不擇手段,只不過大家都小心翼翼隱藏自己不被他人發現而已。信奉“黑暗森林法則”者最易被騙子抓住“辮子”,而“黑暗森林猜疑鏈”又給騙子提供了閃轉騰挪的無限空間。這,算不算是文明社會的最大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