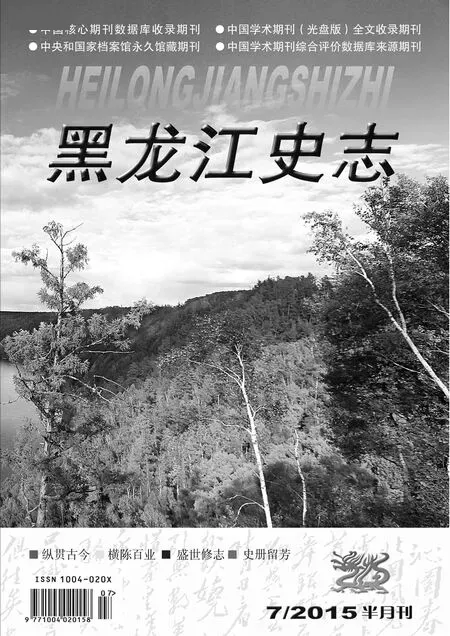鴉片戰爭時期中英之間的“情報戰”
黃付才
(東莞鴉片戰爭博物館 廣東 東莞 523900)
正如魏源所講:“不悉敵情,不可以行軍;不悉夷情,不可以籌遠。”情報很大程度上決定著戰爭的進程。鴉片戰爭時期,中英之間應不同的情報觀念,對情報搜集的精密及對情報分析、預判的迥異,嚴重影響了鴉片戰爭的走向。筆者試從情報觀念之淡漠與熱衷,情報渠道之粗簡與精密,情報預判之錯失與果斷,情報影響之失利與收獲四個方面,淺析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的“情報戰”。
一、情報觀念之淡漠與熱切
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因經濟體制、政治架構、對外政策及相應“華夷觀念”、民族心態的迥異,導致了雙方對彼此探尋、貿易、掠奪欲望的霄壤,進而促成了雙方對情報工作的不同觀念。
(一)清政府情報觀念之淡漠
中國自古以來便注重農業立國,重農抑商。在“男耕女織”、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不需依賴外國商品的進口,對外通商也主要是天朝施之于他國的恩惠,正如乾隆帝在給英王的敕諭中所說:“天朝物產豐盈,無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貨物以通有無。特因天朝所產茶葉、瓷器、絲斤,為西洋各國及爾國必需之物。是以加恩體恤,在澳門開設洋行,俾得日用有資,并沾余潤。”在此經濟基礎之上,為防御西方殖民者浮海東來的殖民擴張,防范漢人與殖民者勾結聯合反清,鴉片戰爭前,清政府實行嚴格限制中外交往的“閉關政策”。加之長期以來形成的“天朝上國”意識及華夷觀念,把周邊鄰國皆視為夷狄,把西方進步文明斥之為奇技淫巧,不齒于與他們交往,更不屑于去探尋、熟悉他們生活的世界。因此,鴉片戰爭前,甚至鴉片戰爭中,一直沒有注重對情報的搜集和有效利用。正如魏源在《海國圖志》中所說:“茍有議翻夷書、刺夷事者,則必曰多事”,“以通市二百年之國,竟莫知其方向,莫悉其離合,尚可謂留心邊事者乎?”
(二)英國情報觀念之熱切
確立資本主義制度較早的英國,更加注重商品貿易,熱衷于殖民擴展、殖民掠奪。通過早期的殖民戰爭,打敗了西班牙、荷蘭、法國,18世紀后期最終確立了海上殖民霸主地位。伴隨著工業革命的開展,英國把侵略的魔爪伸向日益腐朽沒落的大清帝國。經過多年殖民戰爭歷練的英國,深知情報對于遠洋作戰、陌生環境下作戰的重要性,便早早著手情報的搜集工作。馬嘎爾尼使團在訪華期間便收集了大量的中國情報。斯當東寫了《英使謁見乾隆紀實》,安德遜寫了《英使訪華錄》,馬嘎爾尼出版了他的日記,巴羅撰寫了《中國旅行記》,亞歷山大繪了大量畫圖,還有許多使團成員寫過中國見聞方面的文章和書。這些書和文章以親見親聞形式介紹了中國社會各個方面情況。魏源在《海國圖志》中對《澳門月報》對中國的論論述進行了記述,月報對中國土地之廣闊,歷史傳承之久遠,法度延續至不斷,兵民數目之統計,槍炮武器之分析,文化漢字之解讀,清政府對外人外事之態度等進行了客觀詳細的記錄。不難看出,英國在戰爭爆發前,已搜集了中國沿海的地形、氣候及清軍作戰能力等情報。因此,戰爭一開始,在什么季節、什么地方作戰,早已成竹在胸。
二、情報渠道之粗簡與精密
基于對情報重視程度的不同,鴉片戰爭時期中英雙方對情報的搜集工作花費懸殊的心力、物力、人力,使得中英雙方在情報搜集渠道上呈現出粗簡與精密的特點。
(一)清政府情報渠道之粗簡
清政府的情報渠道大致有三,一是外商的傳聞及通風報信。比如1840年2月,林則徐聽到澳門葡萄牙人在傳聞,英國將從本土及印度各調軍艦12艘來華;1840年4月,美國領事稟林則徐,告以本國及英國報紙載,6月份英國將封鎖廣州港,要求盡早讓美國船入口開艙。二是行商的信息傳遞中轉。行商除包攬進出口貿易外,還要充當外國商人與中國政府之間的中介,如外人在廣州居留與活動,要由洋商負責照管監督;遇有外事交涉,也要由他們經辦。因此,他們間接起到了情報搜集的作用。林則徐廣州禁煙期間,行商對鴉片躉船、鴉片走私及鴉片商人活動等信息的傳遞起到一定作用。在律勞卑來華事件中,兩廣總督盧坤第一時間派行商去打聽他的來華目的,并命令通事和行商詳明開導,也充分體現了行商的中轉及信息情報的傳遞工作。三是林則徐等探尋與學習。林則徐在廣州禁煙期間,他組織人翻譯英文《廣州日報》,以了解敵情;為通曉外國情況,組織人員翻譯《世界地理大全》,還選譯了《各國律例》、《對華貿易罪過論》及《華事夷言》等;搜集外國戰船圖式、大炮瞄準法等資料。
(二)英國情報渠道之精密
與清政府的情報來源相比,英國對情報的搜集更加主動、更用心,情報渠道更廣泛,情報更精密。
一是收買漢奸搜集情報。在浙江,漢奸陳秉均常在各處茶館探問軍情,報告給郭士立;漢奸方錫洪供稱:“每日都有漢奸許多起,在夷人處報官兵信息,得受洋錢”;漢奸虞得倡也供稱,“夷人所用漢奸,各處打聽信息,日日有報,或數十起,或一二十起”。情報內容包括清兵“虛實”、兵員數額、兵丁號衣式樣,何處有埋伏,何處兵勇強健、官員姓名年貌以及某處某人是富戶等。
二是傳教士借傳教搜集情報。英船阿美士德號上德籍傳教士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化名甲利(教名Charles的譯音),充當翻譯兼醫生,在沿海口岸以替人治病為名,進行調查和傳教活動。還有馬禮遜、馬儒翰等。
三是軍事偵察。英船阿美士德號偵察中國沿海,從1832年2月26日直到9月5日,從澳門出發沿中國海岸對南澳島、廈門、福州、舟山、寧波、上海、山東、朝鮮、琉球等地進行偵查,搜集了大量機密情報。對于沿途河道和海灣進行測量,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并繪制成詳細的航海圖;對各地的軍事情況作了認真偵查。如胡夏米對南澳進行偵查后,這樣向公司報告:“南澳是廣東第二個海軍根據地,一半位在廣東,一半位于福建,它是總兵官或提督的住所。在他的指揮下,共有軍隊5237人,其中4078名屬廣東,1159名屬福建。但是這些軍隊的實際存在,除了在花名冊中以外,是很可疑的。這個根據地的防御,據我們所見,共有七八只戰船。從外形看來,它們類似小型的福建商船;從各方面看來,比我們在廣州看到的戰船要差得多。海灣入口處有炮臺兩座,較高的一處有炮八尊,較低的一處有炮六尊。海灣內部另有小炮臺一座,上面并未架炮。”此外,英軍每次作戰前都會進行實地勘察。
四是通過洋行的信息傳遞中轉等。
三、情報預判之錯失與果斷
基于上述中英雙方對情報觀念的淡漠與熱切,情報搜集及情報渠道的粗簡與精密,致使雙方對情報的分析、預判及基于情報的決策出現了巨大的反差。
(一)清政府情報預判之錯失
鴉片戰爭時期,清政府由于對情報的重視不夠,對獲得的有限情報并沒有進行精確求證,認真推敲,因此在情報的利用上要么以訛傳訛,要么出現錯誤判斷。
一是對“邊釁”錯誤之估計。在廣州前線的林則徐也認為:“該國以七萬里之遙,其主若臣未必周知情狀,今他國通商如舊,而英國獨停,若該國查察情由,系因圖賣鴉片,抗違天朝新例,則內而自知理曲,外而顏面何存?彼亦不肯容義律等之詭計奸謀,以自壞其二百年來之生計也。”當英國國內正緊鑼密鼓地制造戰爭輿論,進行著戰爭的準備時,林則徐卻一無所知,直到鴉片戰爭前,林則徐仍然不相信英國敢于大舉侵華。
二是對英軍進軍路線的誤判。牛鑒斷言:“由吳淞而入揚子江,逆夷雖有內犯之言,然相距數百里水程,亦不過虛詞恫嚇,臣是以反復體察,逆夷不犯內河,竟屬卻有把握。”由于對英軍戰略意圖的誤判,而忽略了長江下游分防務,致使英艦如入無人之境,沿著長江上駛。
三是對英軍不善陸戰的誤認。江蘇省總督豫堃,在其給皇帝的一份令人鼓舞的報告中宣稱,“(英國人)身體僵硬,雙腿筆直。腿上穿著衣服,幾乎無法自由伸曲。一旦跌倒,無法站起。對于陸地作戰來講,這是致命的”。
四是對“漢奸”參戰的夸張。清朝統治者大肆渲染漢奸參戰,在奏報和諭旨中反復宣傳:戰爭失利,都是因為漢奸充斥,“助逆肆兇”造成的,“所有各處失陷之由,皆系漢奸作為內應”,逆夷“無一處不勾結漢奸,無一漢奸不得其重賄,為之致死,此其所以逞兇肆逆,各省不能取勝之實情也”。過分夸張漢奸對抗戰的破壞作用,以推脫戰敗的責任。
(二)英國情報判斷之精準
與清政府不同,鴉片戰爭時期,英國各方搜集情報,在統籌分析預判的基礎上,合理制定戰略方針,精心設計戰術。
一是戰略方面。英國派遣中國遠征軍之前,巴麥尊外相就整個的作戰方針做出了明確指示,“在珠江建立封鎖”、“占領舟山群島,并封鎖該島對面的海口,以及揚子江口和黃河口”。后來英軍的進攻路線,基本按照這一方針進行。英軍避開廣州北犯是在執行預定的戰略部署,并不是因為林則徐坐鎮廣州及其防務的嚴密,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一書中以有精深論述。
二是在戰術方面。英軍利用搜集的情報,借助漢奸引路,創造性地進行了戰術設計。茅海建認為:“英軍的這種戰艦攻擊正面、陸軍抄襲背后的戰術,體現出來的是近代的軍事學術。特別是其登陸部隊,搶占制高點,輔以野戰炮兵,次第攻擊山上小炮臺而山谷軍營而主炮臺,連續作戰,各個擊破,其攻擊路線流暢有序,在軍事史上屬上乘之作。”此外,英軍“揚子江戰役”計劃的核心,攻打漕運樞紐鎮江、截斷大運河,與英法七年戰爭中封鎖法國所有的沿海城市,幾乎使法國的商業貿易瀕臨崩潰有異曲同工之妙。
四、情報影響之失利與收獲
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學者更多注重了中國武器裝備的落后,政治制度的落伍及吏治的腐敗等,其實情報對近代戰爭影響至關重要。鴉片戰爭失敗后,魏源痛切地指出:“同一御敵,而知其形與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敵,而知其情與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他認為中國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不了解外請。姚瑩也于戰后指出:“海外事勢夷情,平日置之不講,故一旦海舶猝來,驚若鬼神,畏如雷霆,夫是以僨敗至此耳”。不可否認,鴉片戰爭時期,清政府對情報的搜集、分析、利用不夠,嚴重影響了戰爭的進程。而英國多方搜集情報,合理分析預判,統籌制定合理的戰略方針,創造性地設計戰術,最終迫使清政府簽訂喪權辱國的《南京條約》。
[1]魏源:《海國圖志》,中州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99頁。
[2]《乾隆致英王第二道敕諭》,《東華續錄》(王先謙著)乾隆朝一一八。
[3]蕭致治、楊衛東編:《鴉片戰爭前中西關系紀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360—368頁。
[4]南木:《鴉片戰爭以前英船“阿美士德”號在中國沿海的偵察活動》,見《鴉片戰爭史論文專集》,第106—107頁。
[5]中國史學會主編:《鴉片戰爭》第2冊,上海人民出版社、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22頁。
[6]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三聯書店1995年4月版,第112—116頁。
[7]《兩江總督年鑒奏為江蘇洋面靜謐現仍遵旨嚴防折》,《鴉片戰爭檔案史料》,第4冊,第355頁。
[8]轉引自:特拉維斯·黑尼斯三世,弗蘭克·薩奈羅著,周輝榮譯:《鴉片戰爭—一個帝國的沉迷和另一個帝國的墮落》,三聯書店2005年8月版,第110頁。
[9]轉引自鄭劍順:《晚清史研究》,岳麓書社2004年1月版,第99頁。
[10]《籌辦義務始末》(道光朝)三,卷四十三,中華書局1964年版,第1300頁。
[11]蕭致治、楊衛東編:《鴉片戰爭前中西關系紀事(1517—1840)》,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5月版,第25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