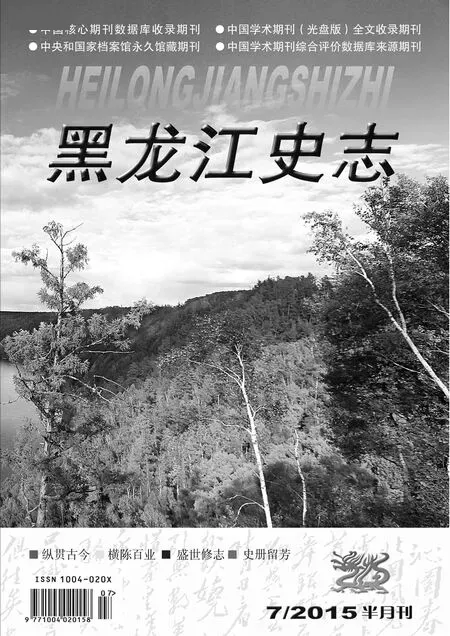明朝海運與漕運利弊簡析
趙成凱
(中國海洋大學 山東 青島 266000)
明朝海運與漕運利弊簡析
趙成凱
(中國海洋大學 山東 青島 266000)
海運的發展在明朝時期,經歷了一個興衰的過程。人們的海洋、海運意識卻是在不斷加強的。相較于漕運的諸多的弊端,海運更顯現了其優越性,體現了海洋開發、海洋利用的重要性以及趨勢。從漕運、海運二者的相互利弊的對比,可以從歷史角度來更好地認識到海洋發展這個潮流趨勢,對于今天我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及把握時代主題都有重要的意義。
明朝;漕運;海運
一、明朝漕運的弊端分析
明朝時期海運相比元朝時期有所衰落,人們最初反對海運,多源于海運多風濤之險。海上運輸在明朝時期被認為是十分艱辛而冒險的事業,特別是長途航運。明朝初年,遼東軍餉短缺,令從江浙往遼東運糧,結果有近一半的運糧商船沉覆在大海之中。盡管人們在長期的實踐中,積累了大量的海運經驗,但長途航運仍被視為十分危險的事業。特別是在季風季節,一般只有大型海船才敢貿然出海,而且必須“習知水性風勢”,“詳悉水勢地形”。
明朝受惠于元朝會通河的開通,大興漕運。《明史·河渠志》載:
“明成祖肇建北京,轉漕東南,水陸兼挽,仍元人之舊,參用海運。逮會通河開,海陸并罷。”
漕運雖較海運安全,但是運河的修建及使用亦有諸多弊端。
維修運河費用巨大。運河年年淤塞,年年修筑,浪費錢財。據《劍橋中國明代史》記,在大運河一段,沿徐州洪挖了半個世紀的淤泥……,花了80年,呂、梁洪才被清淤,阻塞的河道比較通暢。這只是涉及到運河的小段,可見費時之久。又據《劍橋中國明代史》:
“……雖然依附于一個有廣闊空間的大國對于一個普通耕作者來說能得到一定的好處,但也肯定要增加運輸負擔,對于耕作者來說負擔就轉化成更高的稅賦。在開始時,加于漕糧(以及其他稅項)的主要附加稅稱為“耗”。這是用來彌補糧食散落、霉爛和丟失的損耗。至于從湖廣遠運至北京的漕糧,附加稅可高達糧食成本的80%……明政府不愿把這些損失納入其財政制度的運營成本中,因此也就依靠納稅人支付運費。漕運制還把其基礎設施的費用,特別是維修大運河和造船的成本,分攤給運河流過的地方的文官政府和軍事單位。”
其次,沿河的人民力役負擔相當的繁重。《明史》載:
“弘治二年,河復決張秋,沖會通河,命戶部侍郎白昂相治。昂奏金龍口決口已淤,河并為一大支,由祥符合沁下徐州而去。其間河道淺隘,宜于所經七縣,筑堤岸以衛張秋……,越四年,河復決數道入運河,壞張秋東堤,奪汶水入海,漕流絕。時工部侍郎陳政總理河道,集夫十五萬,治未效而卒。”
“世宗之初,河數壞漕……諸大臣多進治河議。詹事霍韜謂:‘前議役山東、河南丁夫數萬,疏浚淤沙以通運。然沙隨水下,旋浚旋淤……’”
由此可見漕運的開挖疏浚,使加重的服役人民的負擔。
運河的修建及使用中違背了自然環境規律,造成了許多的危害。自隋修建大運河,元朝的開會通河等運河。致使黃河改道,使黃河進入了“河患”的頻繁期。關于運河與黃河的關系,我們從徐光啟的論述中可以看到:
“河以北諸水,皆會于衡、漳、恒、衛。以出于冀;河以南諸水,皆會于汴、泗、渦、淮,出于徐,則龍門而東、大水之入河者少也。入河之水少,而北不侵衛,南不侵淮,河得安行中道而東出于兗,故千年而無決溢之患也。有漕以來,惟務疏鑿之便,不見其害。自隋開皇中,引谷洛水達于河,又引河通于淮海,人以為百世之利矣,然而河遂南入于淮也,則隋煬之為也,……當在今東平之境,而邇年張秋之決,亦復近之。假令尋禹故跡,即會通廢矣,是會通成而河乃不入于衛,必入于淮,不復得有中道也,則仲暉之為也。故曰:漕能使河壞也。”
徐光啟指出運河諸多弊端,隋朝永濟渠,元朝會通的開通破壞了黃河流域各水系的入海通道,運河的發展還破壞了沿線的農業,其作用是消極的。
二、明朝興海運的原因分析
明朝結束亂世,承惠于隋唐、元朝的運河發展,從而大力興運河而罷海運。然而這并沒有阻擋興海運的愿望。
明朝丘浚較早提出了恢復海運的意見。他在成化二十三年進《大學衍義補》,提出海運與漕運并行的意見,其言:
“海舟一載千石,可當河舟三,用卒大減。河漕視陸運費省什三,海運視陸省什七,雖有漂溺患,然省牽卒之勞、駁淺之費、挨次之守,利害亦相當。宜訪素知海道者,講求勘視。”
雖然其說未行。可以看出海運均有運量大、費用低、省人力等好處。
丘浚針對“海道險遠,損人費財”的觀點又言:
“請以《元史》質之,其海運自至元二十年始至天歷二年止,備載逐年所至之數,以見其所失不無意也。竊恐今日河運之糧每年所失不止此數,況海運無剝淺之費、無挨次之守,而其支兌之加耗每石須有所減,恐亦浮于所失之數矣。此策既行,果利多而害少,又量將江淮、荊湖之漕折半入海運,除減軍卒以還隊伍,則兵食兩足而國家亦有水戰之備,可以制服邊海之夷,誠萬世之利。”
二十年,總河王以旂以河道梗澀,言:“海運雖難行,然中間平度州東南有南北新河一道,元時建閘直達安東,南北悉由內洋而行,路捷無險,所當講求。”帝以海道迂遠,卻其議。三十八年,遼東巡撫侯汝諒言:“天津入遼之路,自海口至右屯河通堡不及二百里,其中曹泊店、月坨桑、姜女墳、桃花島皆可灣泊。”部覆行之。四十五年,順天巡撫耿隨朝勘海道,自永平西下海,百四十五里至紀各莊,又四百二十六里至天津,皆傍岸行舟。其間開洋百二十里,有建河、糧河、小沽、大沽河可避風。初允其議,尋以御史劉翾疏沮而罷。是年,從給事中胡應嘉言,革遮洋總。”
嘉靖時期,雖然海運發生事故,但是仍有大臣仍提出發展海運。
“隆慶五年,徐、邳河淤,從給事中宋良佐言,復設遮洋總,存海運遺意。山東巡撫梁夢龍極論海運之利,言:“海道南自淮安至膠州,北自天津至海倉,島人商賈所出入。臣遣卒自淮、膠各運米麥至天津,無不利者。淮安至天津三千三百里,風便,兩旬可達。舟由近洋,島嶼聯絡,雖風可依,視殷明略故道甚安便。五月前風順而柔,此時出海可保無虞。”
六年,王宗沐督漕,請行海運。詔令運十二萬石自淮入海。其道,由云梯關東北歷鷹游山……,乞溝河入直沽,抵天津衛。凡三千三百九十里。
二十五年,倭寇作,自登州運糧給朝鮮軍。山東副使於仁廉復言:“餉遼莫如海運,海運莫如登、萊。蓋登、萊度金州六七百里,至旅順口僅五百馀里,順風揚帆一二日可至。又有沙門、鼉磯、皇城等島居其中,天設水遞,止宿避風。惟皇城至旅順二百里差遠,得便風不半日可度也。若天津至遼,則大洋無泊;淮安至膠州,雖僅三百里,而由膠至登千里而遙,礁礙難行。惟登、萊濟遼,勢便而事易。”時頗以其議為然,而未行也。四十六年,山東巡撫李長庚奏行海運,特設戶部侍郎一人督之,事具《長庚傳》。”
明朝時期有“三餉”,大臣們從實際出發,提出“餉遼莫如海運”的觀點,亦可見當時對興海運的認識。
“崇禎十二年,崇明人沈廷揚為內閣中書,復陳海運之便,且輯《海運書》五卷進呈。命造海舟試之。廷揚乘二舟,載米數百石,十三年六月朔,由淮安出海,望日抵天津。守風者五日,行僅一旬。帝大喜,加廷揚戶部郎中,命往登州與巡撫徐人龍計度。山東副總兵黃蔭恩亦上海運九議,帝即令督海運。先是,寧遠軍餉率用天津船赴登州,候東南風轉粟至天津,又候西南風轉至寧遠。廷揚自登州直輸寧遠,省費多。尋命赴淮安經理海運,為督漕侍郎硃大典所沮,乃命易駐登州,領寧遠餉務。十六年加光祿少卿。福王時,命廷揚以海舟防江,尋命兼理糧務。南都既失,廷揚崎嶇唐、魯二王間以死。”
可以看出,由于運河不斷的淤塞,黃河屢決,沿海的商船貿易發展,嘉靖、隆慶、萬歷間,有許多人提倡海運。社會各階層都認識到了海運的便利,對于海運在國家經濟安全、減輕百姓負擔、提高運輸等方面的優勢給予肯定。
綜上所述,對于海運的發展認識在明朝經歷了一個興衰的過程。但是可以看出人們的海洋、海運意識卻是在不斷加強的。縱然明朝沒有像元朝大力發展海運,但無論是上層還是下層百姓都認識到了海運之利。相較于漕運的諸多的弊端,海運更顯現了它的優越性,體現了海洋開發、海洋利用的重要性以及趨勢。從漕運、海運二者的相互利弊的對比,我們可以從歷史角度來更好地認識到海洋發展這個潮流趨勢,對于今天我們的經濟發展、社會穩定、國家安全及把握時代主題都有借鑒的意義。
[1]朱誠如《管窺集·明清史散論》,紫禁城出版社,第230頁。
[2]張廷玉《明史》簡體字版,卷49~卷100,中華書局,第1385頁。
[3][英]崔瑞德,[美]費正清《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79頁。
[4][英]崔瑞德,[美]費正清《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第574頁。
[5]張廷玉《明史》簡體字版,卷49~卷100,中華書局,第1389頁。
[6]張廷玉《明史》簡體字版,卷49~卷100,中華書局,第1390-139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