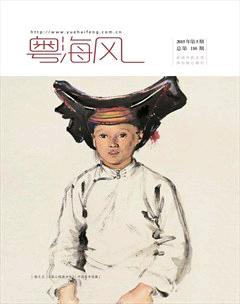新詩形式的內涵與底線瑣議
張立群
一
對于百年新詩發展歷程而言,“何謂形式”一直存有爭議。出于對舊體詩的“反叛”與“超越”,新詩自誕生之日起,就以“解放”的姿態打破了格律的“枷鎖”,從而進入了自由的時代。在詩歌語言、結構、韻律等要素共同更新的前提下,新詩形式之新可謂具體、直觀且靈活多變。不過,隨之而來的問題則是無法用某種規范或標準概括新詩的形式。時至今日,“分行的自由體”已成為識別新詩形式的最基本且最重要的“依據”,但同時,它也是最具爭議的表述。新詩是“分行的自由體”,但“分行的自由體”卻未必都是新詩,這看似簡單的邏輯已使新詩的形式問題遇到了源自文學內部的“挑戰”,而新詩的“合理性”、“合法化”也由此產生了“危機”。
回顧現代文學的歷史,對比其他文體創作,新詩的命運常常給人以更為坎坷的印象。新詩的難題或曰癥結在于形式,新詩有“形”無“式”雖顯武斷,但卻在一定程度上道出了新詩表象背后內部構造模糊不清的事實。有感于嘗試期新詩的“散而無紀”,很多新詩人一邊創作,一邊進行理論的探討。至20世紀20年代中期,“新月詩派”的聞一多更是在《詩的格律》一文中提出了著名的“三美”即“音樂美、繪畫美、建筑美”的主張,但如何對其進行廣泛而有效的實踐卻始終是一個難題:如何從格律詩那里汲取資源及怎樣保持汲取后創作的現代意識、靈活性,顯然是一個常常超出理論邊界的問題;而如果一旦讓新詩的形式過分格律化,新詩的“新”與自由勢必又受到損傷。與格律化追求一致的,在百年新詩的發展道路上,還有歌謠化、民歌體、圖像詩等形式實踐。然而,就其結果來看,上述實踐只是為新詩形式提供了某種可能,并未使問題本身獲得確定性的答案。進入80年代之后,新詩寫作日趨呈現出無拘無束、自由隨意的發展態勢。只要寫作者認定所寫對象為詩且獲得適當的認可,詩歌及其創作者的身份就可以被確定下來。詩歌鑒賞標準的寬松與降低使其形式問題常常湮沒于分行的文字之中,新詩形式是一個不言而喻、無需證明的論題,已成為時代語境賦予新詩的生存境遇。
二
對于新詩的形式,“內在的結構”是一個值得關注的看法。歷史地看,這一看法可以追溯到郭沫若、宗白華的詩歌理論,其后,徐志摩在《詩刊放假》中的“詩感”與“原動的詩意”說也與之接近[1],當代對于此闡釋得最為集中的是鄭敏的文章《詩的內在結構——兼論詩與散文的區別》。從理論上說,“內在的結構”使新詩獲得了詩意的本質和詩性的內核并與其他文體形式區分開來;詩歌的韻律、節奏、意境以及美的閱讀感受都可以從“內在的結構”中找到相應的寄居地。但顯然,“內在的結構”是一種理念、一種感知,而不是處處可見的物質形態。就作者來說,創作時對詩意、詩性的追求,無疑會使正在生成的詩歌具有詩的“內在結構”,不過,這一結構并不每次都會在讀者那里喚起同樣的“共鳴”,在此前提下,我們同樣可以說“內在的結構”是一種心態、一種創作上的倫理與美學追求,它距離那種帶有標志性的詩歌形式,還有一定的距離。
“內在的結構”一方面表明為新詩“賦形”的焦慮,而從深層上說,則可以理解為對詩歌本質的探尋、確認及其歷史化的過程。新詩之所以為詩,是因為其詩的本質,那些打著詩歌旗號但不是詩的創作終究會為人們所遺忘。新詩的形式是自由的,可以無“常體”或“定體”,但跳躍、凝煉,講求意境和美感等基本元素不可全部拋棄。結合新詩發展史可知:新詩是一種受語境影響十分顯著的文體形式。近些年新詩寫作突出表現為重視口語、敘事,在一定程度上已將詩歌寫作局限在一個相對狹窄的空間,至于由此而呈現的游戲式、流水帳式、說事而非寫詩、情感意識的普遍匱乏等等,更不利于新詩自身的良性發展。包括形式在內的一切關于新詩的問題,首先應當從確認“何為詩”的命題上出發,否則所有的探討都難免成為空談!
三
對比長達數千年的中國古典詩歌傳統,新詩短暫的歷史常常給人以積淀少、經典化程度不高的印象。談及新詩形式時常常有意或無意地以古典詩歌為參照就是一個明證。胡適在新詩嘗試時曾以“文學革命的運動,不論古今中外,大概都是從‘文的形式一方面下手,大概都是先要求語言文字文體等方面的大解放”[2]的論斷,為新詩的誕生找到了進化論的依據,然而,其相對于古典詩歌所必然秉持的平民化、通俗化立場也是十分明顯的。新詩需要相應的歷史去證明自身的合理性,同時,新詩只有被視為中國詩歌傳統的一部分、中國詩歌史的一個新階段時,才會緩解命名上的壓力。在我看來,在現代社會的文化語境中,探討中國詩歌的發展,只有不忽視同時期進行的古體詩、詞、歌詞等形式的創作,才能更有助于詩歌本身的理論探討與實踐。而將各種形式的詩歌創作共置一個場域,不斷進行“傳統”與“現代”的對話,也絕非是一種“向后看”的行為。它本身就是中國詩歌發展至現代應當呈現的局面,它可以使新詩擁有更為廣闊的實踐空間,并為形式實踐提供有益的經驗直至創新的可能。
從接受的角度上說,能夠證明新詩身份及其創作實績的當然是那些普遍為讀者接受的經典之作。從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穆旦等代表作的情況可知:新詩的經典化不僅取決于詩人的水準、作品的藝術、時間的沉積,還有汲取古今中外優秀詩歌創作經驗與經得起閱讀的檢驗。當然,確立新詩的典范、從中探究新詩的形式邊界,絕不是要求簡單的重復和形似,新詩自身的內涵決定只有寫出滿意之作、達到詩的境地,才會實現形式本身的邏輯建構。新詩的典范之作在形式化追求上取得了哪些重要成就、提供了怎樣的藝術實踐經驗,不僅關乎于量,還關乎于質。但凡稱得上新詩的優秀之作,都充分發揮了現代漢語的表意功能,而現代漢語究竟應當如何入詩?現代漢語入詩是否就是簡單的白話與口語的問題?探討這些問題,不難發現新詩形式層面的質素就蘊含其中。
四
在新詩發展已有百年歷史的背景下,我們依然可以將“分行的自由體”作為新詩形式的底線(此時不包括散文詩),但新詩形式的內涵卻遠比此復雜。從詩人的角度上說,新詩寫作及其形式問題可以借鑒戴望舒的“為自己制最合自己的腳的鞋子。”[3]從時代的角度上說,不同時代的社會文化與現實生活其實都為詩歌寫作及其形式提供了經驗,只是越是近距離的時間越容易使人們忽視詩歌寫作的變化。當代詩歌生存的語境由于網絡的繁榮、各式文體形式的交融,可以更為從容、自由的實踐。與此同時,詩人特別是對那些正在成長的詩人,不必過分迷信權威或一時之風氣。在追求自身風格化的道路上,不斷深度開掘詩歌本身的表現空間,才是詩人成長及至詩歌發展的正確方向。這個包括新詩教育、新詩鑒賞不斷普及、提高在內的過程,同樣是詩歌寫作倫理的重要組成部分。隨著新詩歷史的逐步延伸,新詩的形式問題會得到進一步的拓展,但其必定是一個復雜的集合體,需要以解析的方式呈現其應有的內涵。
注釋
[1]徐志摩:《詩刊放假》,1926年6月10日《晨報副刊·詩鐫》第11期。
[2]胡適:《談新詩——八年來一件大事》,1919年10月10日《星期評論》“雙十節紀念專號”。
[3]戴望舒:《望舒詩論》,《戴望舒全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12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