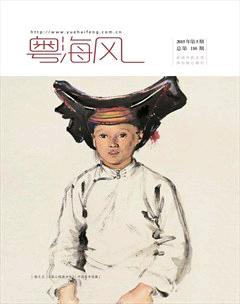地域文化與東莞美術(shù)
梁江
東莞是嶺南歷史文化名城。三國(guó)時(shí)期建郡,唐代已確名為“東莞”。1700多年來(lái),水壯而清,山雄以秀,英豪篤生,名聞遐邇。別的不說(shuō),書(shū)畫(huà)藝術(shù)界便有明代袁登道、王應(yīng)華、張穆,清代梁濤、尹源進(jìn)、范熙祥、周炳、黃友竹、張敬修、張嘉謨,近現(xiàn)代盧子樞、黃般若、鄧白等。晚清張敬修精心營(yíng)造的可園是廣東四大名園之一,居巢、居廉依托可園一二十年,成為開(kāi)一代風(fēng)氣的花鳥(niǎo)名家。享有盛名的嶺南畫(huà)派發(fā)軔于東莞可園,這已是近代美術(shù)史的定論。
《畫(huà)史會(huì)要》評(píng)袁登道“山水法叔明(王蒙),后法米顛(米芾),篆隸刻印皆工”。廣州美術(shù)館藏袁登道《筆底煙霞》圖卷,原為容庚先生舊藏。廣東省博物館藏《山水圖卷》,以積墨、破墨法寫(xiě)之。卷尾有作者跋云:“余乃法古而離古,直爛然涂鴉,不計(jì)其合與否”,表達(dá)了袁氏不屑為人束縛的豪情。
二十世紀(jì)上半葉的莞籍書(shū)畫(huà)家,有容祖椿、鄧爾疋、李鳳廷、黃般若、黃少梅、盧子樞等。1923年,黃般若、黃少梅、盧子樞與姚禮修、鄧芬、羅卓、黃君璧、趙浩等人在廣州組織“癸亥合作畫(huà)社”,1925年又與李鳳廷、溫其球、潘達(dá)微等聯(lián)手,擴(kuò)畫(huà)社為“廣東國(guó)畫(huà)研究會(huì)”,有會(huì)員一百多名。
由上面十分粗略的回溯中,已不難發(fā)現(xiàn),研究近古以來(lái)二三百年間莞籍書(shū)畫(huà)家的創(chuàng)作活動(dòng)和藝術(shù)取向,卻已觸摸到嶺南文脈及書(shū)畫(huà)思潮遷變之流向。從另一角度而言,研探嶺南畫(huà)壇,討論嶺南文化特色,東莞是一個(gè)繞不過(guò)去的話題。
朱萬(wàn)章君曾多年在博物館從事書(shū)畫(huà)鑒藏工作,接觸到相當(dāng)數(shù)量的嶺南書(shū)畫(huà)文物。他勤勉而專注,先后出版了《嶺南金石書(shū)法論叢》、《廣東傳世書(shū)跡知見(jiàn)錄》、《嶺南書(shū)法》、《粵畫(huà)訪古》、《廣東繪畫(huà)》、《居巢居廉研究》、《嶺南近代畫(huà)史叢稿》等十?dāng)?shù)種專著,不僅成果豐碩,且視角多與廣東近現(xiàn)代書(shū)畫(huà)源流相關(guān)。我以為,他之特別關(guān)注莞籍書(shū)畫(huà)家的史料及考辨,正是基于對(duì)嶺南文化歷史變遷的較全面了解。綱舉而目張,由東莞切入進(jìn)而探尋嶺南書(shū)畫(huà)流變,從方法論角度看實(shí)在是一個(gè)明智選擇。
話又說(shuō)回來(lái),萬(wàn)事開(kāi)頭難。以往有關(guān)東莞美術(shù)的研究雖不能說(shuō)空白,但多屬零散化,距全面、深入和系統(tǒng)化的要求相去仍甚遠(yuǎn)。萬(wàn)章君圍繞東莞美術(shù)的這一著述,匯集了他近年的若干專題文稿。集腋成裘,聚零為整,通過(guò)不同角度的整合,讓讀者逐漸獲得了較全面而清晰的印象,一個(gè)立體而且可信的東莞美術(shù)歷史輪廓開(kāi)始呈現(xiàn)眼前了。
這正是朱萬(wàn)章君這一專題著述的意義所在。他為之付出的努力很值得肯定,而他的貢獻(xiàn),主要不在于這是第一本東莞美術(shù)史專著,而在于引發(fā)了閱讀者對(duì)東莞美術(shù)的關(guān)注,以及為其后的研究提供了一個(gè)新的學(xué)術(shù)起點(diǎ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