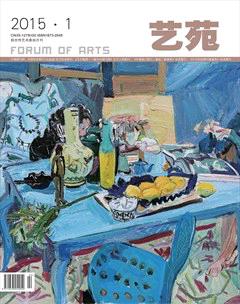《宋書·樂志》十五大曲流行年代補證
——兼論《阿干之歌》與《真人代歌》
文‖黎國韜
《宋書·樂志》十五大曲流行年代補證
——兼論《阿干之歌》與《真人代歌》
文‖黎國韜

六朝畫像磚中的鼓吹樂
《宋書·樂志》載有清商瑟調“十五大曲”的曲辭,是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的大曲文獻實例,其流行與當時清商署之設置、功能與性質有密切關系。由于西晉一朝樂官機構改革力度相當大,變更了曹魏清商署音樂表演局限于皇宮殿閣的特點,從而推動了清商大曲在朝廷上和社會上的傳播,所以十五大曲的“流行年代”理應定在西晉。此外,作為鮮卑族民歌的《阿干之歌》和《真人代歌》或多或少都曾受到西晉大曲形式的影響,這也補充證明了十五大曲的真正流行年代應在西晉時期,而這兩首民族歌曲在文學史、音樂史上的價值也再次獲得肯定。
十五大曲;西晉;清商署;《阿干之歌》;《真人代歌》
大曲是一種十分復雜的音樂表演形式,也是中古音樂發展到高峰的重要標志之一,其曲辭則屬于樂府詩范疇,故歷來受到文學和音樂研究者的共同關注。目前可見最早的大曲文獻實例是《宋書?樂志》記載的“十五大曲”曲辭,所以尤屬研究的焦點。
有關這批大曲的產生和流行年代,學界說法不一,筆者比較同意王小盾先生判定它們為“魏晉大曲”的觀點。[1]147-156但王說并非沒有補充、修正的余地,比如十五大曲均屬“清商三調”中的“瑟調曲”,所以與魏晉兩朝的清商署有著密切的聯系,但曹魏清商署與西晉清商署畢竟頗有差異,王氏未曾注意到這一點,從而影響了對這批大曲流行年代的判斷;此外,與鮮卑慕容部、拓跋部、吐谷渾族有關的《阿干之歌》和《真人代歌》,其產生、改編與演奏方式多受西晉樂舞的影響,亦與十五大曲的流行年代有關,從中可以看出十五大曲發展
到唐大曲的部分過程和脈絡,也有必要再加探討,以下試作考述。
一
沈約《宋書》卷二十一《樂志三》載有“大曲”曲辭十五首,文長不能俱引,茲錄其中的《東門行》(古詞四解)一首以見其體例:
出東門,不顧歸;來入門,悵欲悲。盎中無斗儲,還視桁上無懸衣。(一解)
拔劍出門去,兒女牽衣啼。它家但愿富貴,賤妾與君共餔糜。(二解)
共餔糜,上用倉浪天故,下為黃口小兒。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三解)
今時清廉,難犯教言,君復自愛莫為非。行!吾去為遲,平慎行,望吾歸。(四解)[2]616
對此“十五大曲”,郭茂倩的《樂府詩集》也有收錄,并作了簡要的“解題”,茲引如次:
《宋書·樂志》曰:“大曲十五曲:一曰《東門》,二曰《西山》,三曰《羅敷》,四曰《西門》,五曰《默默》,六曰《園桃》,七曰《白鵠》,八曰《碣石》,九曰《何嘗》,十曰《置酒》,十一曰《為樂》,十二曰《夏門》,十三曰《王者布大化》,十四曰《洛陽令》,十五曰《白頭吟》。《東門》,《東門行》;《羅敷》,《艷歌羅敷行》;《西門》,《西門行》;《默默》,《折楊柳行》;《白鵠》、《何嘗》,并《艷歌何嘗行》;《為樂》,《滿歌行》;《洛陽令》,《雁門太守行》;《白頭吟》,并古辭。《碣石》,《步出夏門行》,武帝辭。《西山》,《折楊柳行》;《園桃》,《煌煌京洛行》,并文帝辭。《夏門》,《步出夏門行》;《王者布大化》,《歌行》,并明帝辭。《置酒》,《野田黃爵行》,東阿王辭。《白頭吟》,與《歌》同調。其《羅敷》、《何嘗》、《夏門》三曲,前有艷,后有趨。《碣石》一篇,有艷。《白鵠》、《為樂》、《王者布大化》三曲,有趨。《白頭吟》一曲有亂。”
《古今樂錄》曰:“凡諸大曲竟,黃老彈獨出舞,無辭。”按王僧虔《技錄》:“《歌行》在瑟調,《白頭吟》在楚調。”而沈約云同調,未知孰是。[3]635
從上引《東門行》曲辭和郭氏的“解題”大致可以看出,當時的大曲是一種艷、曲、趨、亂相結合,曲辭分為多“解”,曲終往往有“獨舞”的復雜的音樂表演形式。若單從曲辭的角度來看,十五大曲應該多屬漢魏時期的作品,因為其中一部分是“三曹”及魏明帝所作,另一部分則是“古辭”,當指早于三曹的漢代歌辭。不過,曲辭產生的年代并不等同于大曲流行的年代,因為表演相當復雜,將曲辭運用到實際演奏當中,還須要很多的“后期加工”。
明白這些基本情況,對于確定十五大曲的產生和流行年代是頗有幫助的。近代以來,有關這一問題主要有三說:楊蔭瀏先生《中國古代音樂史稿》(第四編第五章《秦漢》)、丘瓊蓀先生《漢大曲管窺》(載《中華文史論叢》第一輯)等認為是在漢代;王小盾先生《論<宋書?樂志>所載十五大曲》(載《中國文化》1990年3期)認為“成立在魏,而行于西晉”,所以有“魏晉大曲”的提法;逯欽立先生《相和歌曲調考》(載《文史》第十四輯)則認為它們成立并流行于“晉宋之際”。
根據筆者的判斷,王小盾先生的觀點和實際情況較為接近,他在《論<宋書?樂志>所載十五大曲》一文(以下簡稱“《王文》”)中指出:
十五大曲,采詩合樂,雖然它的歌辭基本上產于漢魏,它的時代卻應按其樂曲的演奏情況來確定。它們應稱作“魏晉大曲”。到王僧虔作《大明三年宴樂技錄》的時代,即劉宋中葉,其辭已多不可歌,因此不能視作“劉宋大曲”。[1]151
按“樂曲的演奏情況來確定”是一種非常合理的見解,因為曲辭雖然漢魏之際已經存在,但要配合大曲的音樂和舞蹈進行表演,其時間就必須略為后延,而這種后延又無論如何不會晚到“晉宋之際”,所以楊蔭瀏、邱瓊蓀、逯欽立等先生的觀點都不如王說準確。此外,《王文》還指出了這批大曲得以成立的三個“主要條件”:
第一,是相和歌進到清商曲。即缺少嚴格樂律規定的不完全配樂的歌唱,接受平、清、瑟諸調式的節制,成為完全配樂的“歌弦”。
第二,是南北方俗樂的匯聚。它使單一風格的樂器曲和歌曲,發展為多種風格、多種功能的器樂與歌樂的結合,亦即艷、曲、趨、亂的結合。
第三,是專門俗樂機構的設立,即清商署的設立,它使大曲的制作和演奏有了人才條件、場所條件和其它物質條件。大曲產生于曹魏,便標志著中國第一批成熟的樂歌、依樂作辭的新型聲辭關系,都產生或形成在這一時代。它代表著中國音樂史上的一個重要里程碑。[1]155
以上所述,觀點明晰,論證有據,可以稱為十五大曲研究中的一項重要成果。換言之,曹魏時期(220-265)實已具備了十五大曲產生的一切條件,說它“成立在魏”是毫無問題的。但為什么又說它們“行于西晉”,也就流行于西晉時期(265-316)呢?對于這一點,《王文》沒有給出任何合理解釋,所以也是最須要補充和修正的地方;否則的話,十五大曲也有可能“成立在魏,且行于曹魏”,如此一來“魏晉大曲”恐怕就要改稱為“曹魏大曲”了。
要解決《王文》留下的疑問,最值得注意的是所謂“清商署的設立”。因為十五大曲均為“清商三調”中的“瑟調曲”,而清商署則是古代朝廷設置,并用于管理、演奏清商樂的樂官機構,對十五首清商大曲流行所起之作用可謂不言而喻。根據筆者多年來對“古代樂官制度”的研究發現(1),曹魏的清商署和西晉的清商署在功能、性質等方面存在著不少差異,《王文》因未意識到這一點,所以才無法解釋“行于曹魏”還是“行于西晉”的問題。
為此,我們必須對魏晉清商署的成立、發展及其性質、功能有所了解。據《三國志?齊王芳紀》注引《魏書》記載:
(齊王芳)于陵云臺曲中施帷,見九親婦女,帝臨宣曲觀,呼(郭)懷、(袁)信入帷共飲酒。懷、信等更行酒,婦女皆醉,戲侮無別。使保林李華、劉勛等與懷、信等戲,清商令令狐景呵華、勛曰:“諸女,上左右人,各有官職,何以得爾?”[4]129-130
由此可見,魏齊王芳(240-253)時已有“清商令”一職之設置,任者為
令狐景。《三國志?齊王芳紀》注引《魏書》又載:
太后遭郃陽君喪,帝日在后園,倡優音樂自若,不數往定省。清商丞龐熙諫帝:“皇太后至孝,今遭重憂,水漿不入口,陛下當數往寬慰,不可但在此作樂。”帝言:“我自爾,誰能奈我何?”……每見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4]130
由此可見,當時又有“清商丞”一職,任者為龐熙。由于令、丞一般為中央政府署級機構的正職和副職,這就更加確切證明了曹魏齊王芳時已有“清商署”。此外,從令狐景口中的“先帝”一詞看,此署可能在魏明帝(227-239)時期已經存在。這里還有一條佐證,據《晉書?五行志上》記載:“魏明帝太和五年五月,清商殿災。”[5]803由此可見,至遲明帝太和中已有“清商殿”的建立;既然有新殿閣的建成,由此設置新的令、丞以管理其中的人員、音樂等事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情。
不過,細勘上面的幾條引文可以發現,曹魏時期清商令、丞的職責以管理后庭人事為主,與專業性質的音樂表演之事關系并不大,比如令狐景之呵斥李華、劉勛,就是出于管理的責任。至于署內女子的功能,更不是單純的樂伎可比,例如令狐景說諸女是“上左右人,各有官職”,表明清商署所轄女子的性質屬于“內官”,即與皇帝存在配偶關系者;正因此,齊王芳才會做出“九親婦女有美色,或留以付清商”的舉動,看重的是其“色”而非其“伎”;而“清商殿災”一條,更說明清商署就設在后宮的重門深閣之內,署中之樂、奏樂之人又豈是一般人能夠看得到的?
此外,《三國志?齊王芳紀》注引《魏書》中還記錄了令狐景的另一件事情:“帝常喜以彈彈人,以此恚(令狐)景,彈景不避首目。景語帝曰:‘先帝持門戶急,今陛下日妃后游戲無度,至乃共觀倡優,裸袒為亂,不可令皇太后聞。景不愛死,為陛下計耳。’”[4]130引文中“持門戶急”一語頗值得注意,它反映了令狐景的另一項重要職責是管理殿閣門戶的安全,亦與樂事無關。總之,曹魏時的清商署雖與清商樂有一定聯系,署內亦必有一批精通清商樂的女子,但其功能和性質還算不上是專業的、純粹的樂官機構,后宮殿閣之樂亦不可能為外人所知。這種狀況,勢必阻礙了清商大曲的流行。
到了西晉司馬氏時期,仍沿用魏制而設清商,如《晉書?職官志》載:“光祿勛,統武賁中郎將、羽林郎將、冗從仆射、羽林左監、五官左右中郎將、東園匠、太官、御府、守宮、黃門、掖庭、清商、華林園、暴室等令。”[5]736但此時清商署的性質和功能與曹魏時期相比卻出現了顯著區別,有《通典?樂典》所載為證:
(晉武帝泰始)九年,荀勖以杜夔所制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荀遂典知樂事,啟朝士解音者共掌之。[6]3598
這條記載清楚顯示,西晉時期的樂官機構共有太樂、總章、鼓吹、清商四個。與前代相比,西晉清商署在音樂表演方面一定更為專業,所以才會出現荀勖“依古尺作新律呂”成功后,“遂頒下太常……施用”的做法。另外,西晉時四署的“樂事”由“朝士解音者共掌之”,表明清商大曲的演奏應已經普遍流行到社會的上層,其演奏范圍肯定不再局限于后宮殿閣,而演奏者也不會限于只能“面圣”的內官了。
實際上,這種情況的出現應歸功于西晉一朝對于樂官機構的改革,其時的改革力度可謂相當巨大,而且決不限于清商一署。比如曹魏時期原隸軍籍的鼓吹樂人,至此就統被劃歸太常轄下的鼓吹署,西晉也成為歷史上第一個建立“鼓吹署”的朝代。[7]53-63鑒于這種背景,清商署能夠成為專業樂署并進一步促成十五大曲的流行,就不足為奇了。當然,制定“新律呂”(即荀氏笛律)的荀勖之功勞也非常大,他對于曹魏以來流行的清商樂深有研究,故其律制可以“施用”于清商署中;他甚至編集了一部關于清商樂的《伎錄》,后人一般稱之為《荀氏錄》,可惜該書已經亡佚了。
上述種種情況說明,曹魏時期成立的清商署經過晉人改造后,性質和功能有了較大的轉變,已經成為一個比較純粹、專業的樂官機構。這一樂官機構的出現,才真正具備了推動清樂十五大曲廣泛流行的“歷史條件”。自此角度而言,十五大曲雖成立在魏,但其流行年代則應當限定在西晉時期,這是前人包括《王文》都未曾注意的。
二
清商署性質和功能的變更是清商樂十五大曲流行年代的有力“補證”之一,除此以外,尚有一些重要的歷史事件和音樂作品可以作為佐證,比如著名的鮮卑族民歌《阿干之歌》及相關大曲的創作,還有受《阿干之歌》影響的《真人代歌》等,以下接著討論。
所謂《阿干之歌》,或簡稱《阿干歌》,是鮮卑族慕容部的民歌,與吐谷渾族亦有密切關系。學界曾有不少文章對此曲作過探討(2),但均未專從“大曲”的角度出發,所以尚留有研究空間,以下先看兩條史料:
引文中提到的“廆”指慕容廆,是徒何鮮卑的首領。《通鑒?晉紀八》將慕容廆稱“大單于”的時間定為西晉永嘉元年(307),[9]2735則其作《阿干之歌》約在此年略后,當在西晉的末年。及后,慕容廆之子慕容皝稱“燕王”,時在東晉咸康三年(337)。[9]3013再后,慕容皝第二子慕容儁于東晉永和八年(352)出兵擊滅冉閔,自稱“燕皇帝”,初都薊,后定都于鄴,史稱“前燕”。[5]2831-2834如果引文中提到的“子孫僭號”是指慕容皝,則《阿干之歌》被改為“輦后鼓吹大曲”的時間約在東晉初;若指慕容儁,則要稍后一點,但也在東晉中期以前。
那么慕容廆所“追思”的“吐谷渾”
又是什么人呢?原來,吐谷渾是徒何鮮卑慕容氏的支庶。西晉前期,鮮卑慕容氏的正支由慕容廆率領,開始向遼水東西移動,后來被稱為“徒何鮮卑”。廆的庶兄慕容吐谷渾因與廆失和,遂在晉武帝太康六年(285)前后帶領部落沿陰山山脈西行,度過隴坂,一度將帳幕安置在枹罕(今甘肅臨夏)、西平(今青海西寧市)一帶。[10]640-641《阿干之歌》就是慕容廆追思離開本部的吐谷渾而作,阿干即阿步干,鮮卑語“兄長”的意思,而廆的子孫又將這一民族歌曲改編成“輦后鼓吹大曲”。
“輦后大曲”和“鼓吹大曲”是引文中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如前所述,大曲是一種頗為復雜的音樂表演形式,在慕容鮮卑這種文化相對落后的部落中產生的可能性極小,所以只能是鮮卑人從文化相對進步的晉人手中得到,并進一步改編本族的《阿干之歌》而成。據《晉書?樂志》記載:
由此可見,在經歷西晉末年的大動亂后,東晉初期樂官、樂器亡散非常嚴重,不太可能產生新的、復雜的音樂表演形式,也不太可能給鮮卑慕容氏提供什么藝術借鑒。所以我們仍然要將焦點聚集在西晉,據《魏書?樂志》記載:
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為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于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于長子,及(慕容)垂平永,并入中山。[8]2827
這條史料很清楚表明,對慕容鮮卑音樂有重大影響的主要是“西晉”的“伶官樂器”。由于晉末永嘉之亂,這批“伶官樂器”初為劉、石所得,繼而因慕容儁平冉閔,又搶得了這批藝術財富,其后除一度被前秦苻氏掠得外,主要就保存在鮮卑慕容氏所建立的各個政權之中。由此不難推斷,前燕的“輦后鼓吹大曲”當是借鏡西晉樂官(伶官)所奏清商大曲而產生的一種比較復雜的藝術形式。而這也成為《宋書?樂志》十五大曲流行于西晉時期的一個佐證。
《阿干之歌》被改編成大曲不但佐證了十五大曲在西晉的流行,而且也牽連到另一首著名的鮮卑族民歌,這就是北魏的《真人代歌》,巧合的是,此歌也是以“大曲”形式呈現的音樂。據《魏書?樂志》載北魏太祖道武帝(386-409)時事云:
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8]2828
由此可見,《真人代歌》是北魏初期有關拓跋部的一首史詩式的作品。說它采用了大曲的形式,則有以下理由:其一,此曲凡“一百五十章”,須“昏晨歌之”,恐怕一兩天也唱不完,所以其曲辭必定有很多“解”,這與《宋書?樂志》十五大曲每曲均分若干“解”的情況相類似。(3)其二,《真人代歌》是“絲竹合奏”的表演形式,與“絲竹更相和”的清商大曲表演也頗為相似。(4)
當然,說《真人代歌》是大曲,還有其他一些參考證據,而且與鮮卑慕容部的《阿干之歌》有著密切聯系,據《舊唐書?音樂志》記載:
《北狄樂》,其可知者鮮卑、吐谷渾、部落稽三國,皆馬上樂也。鼓吹本軍旅之音,馬上奏之,故自漢以來,《北狄樂》總歸鼓吹署。后魏樂府始有北歌,即《魏史》所謂《真人代歌》是也。代都時,命掖庭宮女晨夕歌之。周、隋世,與西涼樂雜奏。今存者五十三章,其名可解者六章:《慕容可汗》、《吐谷渾》、《部落稽》、《鉅鹿公主》、《白凈王太子》、《企喻》是也。其不可解者,咸多可汗之辭。吐谷渾又慕容別種,知此歌是燕、魏之際鮮卑歌,歌辭虜音,竟不可曉。[11]1071-1072
由此可見,《真人代歌》屬于“鼓吹樂”的范疇。前文已述,慕容氏改編《阿干之歌》為“輦后鼓吹大曲”,恰好也在鼓吹樂的范疇內,可見二者表演形式的相近。另外,在唐代仍然保存的《真人代歌》“五十三章”中,赫然有《吐谷渾》的名目,此《吐谷渾》應即《阿干之歌》,因為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燕錄》曾記載:“廆以孔懷之思,作《吐谷渾阿干歌》。”[12]323由此可見,《吐谷渾》其實是《阿干之歌》的別稱。據此可以判斷,《真人代歌》應是包括了《阿干之歌》在內的結構更為龐大的“鼓吹大曲”。
由于北魏拓跋氏也是鮮卑族的一支,與吐谷渾有親緣關系,所以在其民族史詩中加入吐谷渾的史事,本不足為奇。而這一加入,則反映出《阿干之歌》輦后大曲的形式在一定程度上曾影響過《真人代歌》的創作。不過,更重要的影響還不止于此,據《魏書?樂志》記載:
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音伎;穆帝為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弦管具矣。逮太祖(即道武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既初撥亂,未遑創改,因時所行而用之。[8]2827
引文的前面六句尤其值得注意,所謂“始祖”即拓跋力微,“二代”則指魏晉兩朝,據《魏書?序紀》記載:
四十二年,(始祖)遣子文帝如魏,且觀風土。魏景元二年(261)也。
文皇帝諱沙漠汗,以國太子留洛陽,為魏賓之冠。聘問交市,往來不絕,魏人奉遺金帛繒絮,歲以萬計。……魏晉禪代,和好仍密。……五十六年,帝復如晉,其年冬,還國。晉遺帝錦、罽、繒、采、綿、絹、諸物,咸出豐厚,車牛百乘。[8]4
自上引可知,拓跋力微與魏晉的關系比較融洽,所以得到過兩朝很多的饋贈,據此,“二代更致”拓跋氏“音伎”的記載應是可信的,這也足以說明代魏的音樂很早就受到了魏晉樂舞藝術的直接影響。不過,曹魏所致的音伎中不可能包括清商署內演奏清商大曲的內官女樂,這種當時只供皇族享受的東西不會隨便賜給一個尚不甚起眼的部落。
及至“穆帝”拓跋猗盧時,西晉“愍帝(313-316)又進以樂物”,于是代國“弦管具矣”。(5)這在代魏音樂發展史上是更加重要的一件事情,因為弦管就是絲竹,而《真人代歌》正好采用了“絲竹合奏”的表演形式。有理由相信,《真人代歌》主要是在西晉末年愍帝所致“音伎”、“弦管”(樂物)的影響下,再結合《阿
干之歌》等音樂形態而創作出來的“大曲”形式。由于當時清商大曲已在西晉宮廷和社會上廣泛流行,所以也成了朝廷饋贈的佳品,但這一切在曹魏時期是難以發生的。
代魏樂舞受西晉音伎、樂器影響很深,還可以舉出一些例子,如《魏書?樂志》載道武帝天興六年(403)冬時詔云:
引文中提到“如漢晉之舊也”,既然漢晉并稱,可見此晉是西晉而非東晉。而“太宗初,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鐘鼓之節”一句當然更加重要,一則它說明北魏早期確有“大曲”形式的存在,《真人代歌》之屬大曲必與事實相去不遠;二則它緊接“漢晉之舊”而言,表明北魏大曲在西晉音伎、弦管影響下“撰合”而成的可能性極大;三則這種大曲又合于“鐘鼓之節”,這顯然是在道武帝“定中山”并得到西晉“樂懸”(見前引《魏書?樂志》)以后才有可能出現的,西晉伶官樂器的重要性再一次被突顯。
以上各種情況說明,無論慕容鮮卑的《阿干之歌》輦后鼓吹大曲,抑或拓跋鮮卑史詩式的《真人代歌》,都屬于大曲表演形式,而且都是在西晉大曲、音伎、樂物的影響下產生的,它們為《宋書?樂志》十五大曲流行于西晉時期提供了兩個重要佐證。亦復因此,這兩首民族歌曲在文學史、音樂史上的價值也再次獲得了肯定。
三
通過以上的論述可知,《宋書?樂志》所載十五大曲的產生和流行年代,學界主要有三種說法,本文傾向于王小盾先生所提出的“成立在魏,而行于西晉”說。但在十五大曲“流行年代”的問題上,王氏卻沒有作出合理解釋,所以有必要作更深入的探討。通過對曹魏和西晉兩朝清商署的設置、性質和功能的比較發現,西晉清商署是一個更為專業、更為純粹的樂官機構,對于清商瑟調十五大曲在朝廷上和社會上的流行顯然有更大的推動作用,所以將這批大曲的流行年代定在西晉而非曹魏會更加合理。
為了進一步證明上述說法,本文還提供了鮮卑慕容氏的《阿干之歌》和鮮卑拓跋氏的《真人代歌》作為佐證。從歷史記載、體式結構和藝術特點分析,這兩首歌曲都與西晉大曲存在密切聯系,因為用于追思吐谷渾的《阿干之歌》后來被改編成為“輦后鼓吹大曲”,用于紀述先人豐功偉績的史詩式作品《真人代歌》也是一種分有多解、絲竹相和的大曲。再從二曲的產生年代,以及西晉樂器、伶官的流傳情況來看,二曲顯然是在西晉大曲、音伎、樂物等影響下產生的,這就反過來說明了十五大曲在西晉時代確實頗為流行。
以上探討的意義尚不僅僅局限于魏晉大曲的范圍。一般來說,魏晉大曲和唐代大曲是古代大曲發展史上的兩個高峰,但兩者之間有何聯系,目前尚未理清,因為時間相隔較遠,能夠提供其聯系之證據少之又少。但通過《阿干之歌》和《真人代歌》的探討,我們還是看到了從十五大曲發展為唐大曲的部分過程和脈絡。因據前引《舊唐書?音樂志》可知,《阿干之歌》和《真人代歌》其實均流傳到唐代的鼓吹署,即使這種“北狄樂”歌辭不可曉,但其音樂演奏形式卻含有魏晉大曲的諸多因素,這種形式足以對唐大曲產生影響。當然,這一問題過于復雜,只能另文再述了。
注釋:
(1)案,筆者的博士學位論文《古代樂官與古代戲劇》(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2011年增訂版)和博士后出站報告《先秦至兩宋樂官制度研究》(廣東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均為專門研究古代樂官制度之作,茲不贅。
(2)筆者案,較重要者如阿爾丁夫先生的《關于慕容鮮卑<阿干之歌>的真偽及其他》(載《青海社會科學》1987年1期)、周建江先生的《關于<阿干之歌>的若干問題》(載《青海師范大學學報》社科版1995年1期)、黎虎先生的《慕容鮮卑音樂論略》(載《中國史研究》2000年第2期)等。
(3)筆者案,“章”就是“解”,南朝王僧虔說:“古曰章,今曰解,解有多、少。……是以作詩有豐約,制解有多少。”(《樂府詩集》卷二十六《相和歌辭一》引,第376頁)
(4)有《樂府詩集?相和歌辭一》“解題”為證:“《宋書?樂志》曰:‘相和,漢舊曲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其后晉荀勖又采舊辭施用于世,謂之‘清商三調歌詩’。”(卷二十六,第376頁)
(5)筆者案,據《魏書?序紀》稱:“(穆帝)八年(315),晉愍帝進帝(猗盧)為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卷一,第9頁)則西晉“樂物”之進,當在是年。
[1]王小盾.論《宋書?樂志》所載十五大曲[J].中國文化,1990(3).
[2]沈約.宋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3]郭茂倩.樂府詩集[M].北京:中華書局,1979.
[4]陳壽.三國志[M].裴松之,注.北京:中華書局,1982.
[5]房玄齡等:晉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6]杜佑.通典[M].王文錦,等,點校.北京:中華書局,1988.
[7]黎國韜.漢唐鼓吹制度沿革考[J].音樂研究,2009(5).
[8]魏收.魏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4.
[9]司馬光.資治通鑒[M]. 胡三省,注.北京:中華書局,1956.
[10]王仲犖.魏晉南北朝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11]劉昫,等.舊唐書[M].北京:中華書局,1975.
[12]李昉,等.太平御覽[M]//文淵閣四庫全書(898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
J60
A
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漢唐戲劇新考”(批號:12CZW045)。
黎國韜,文學博士,歷史學博士后,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華南師范大學嶺南學研究中心兼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