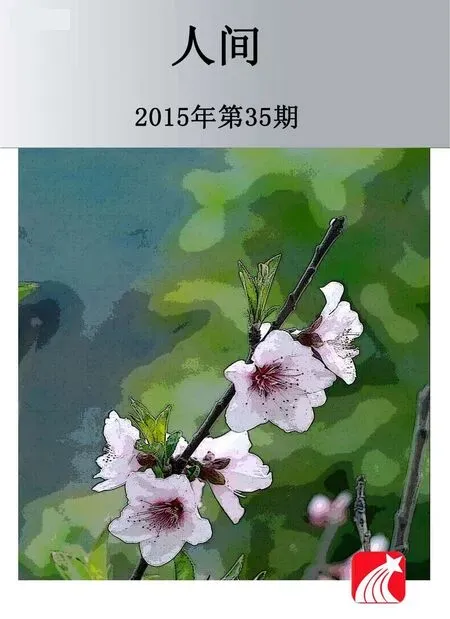勞動三權對集體談判制度的影響
——以德國為例
高盼盼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北京 100000)
勞動三權對集體談判制度的影響
——以德國為例
高盼盼
(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北京 100000)
本文首先闡述了勞動三權的概念及三者的關系,進而介紹了集體談判的定義和功能,重點是以德國為例闡述了勞動三權對集體談判制度的影響,最后加上了自己去廣州調研的一點小感悟。
勞動三權、集體談判、德國
一、勞動三權的概念界定及三者的關系
集體勞權又稱勞動基本權,是由勞動三權,即團結權、集體爭議權和集體談判權為基本內容構成的。
關于三者的關系,不同的學者的觀點也不盡相同。常凱老師認為團結權是集體勞權最基礎、最核心的權利。談判權是集體勞權最主要的內容,是工會的基本的活動方式和手段。罷工權的作用則在于保障團結權和談判權的行使。
程延園老師認為“勞動三權”的核心是集體談判權,團結權和爭議權的目的均是為了集體談判。團結權是集體談判權的前提和基礎,是進行集體談判的“先行行為”。爭議權則是實現集體談判權的輔助性權利,是保障集體談判得以開展的壓力手段。
王晶老師認為三種權利的核心權利或目的是談判。前提是團結權,集體爭議權是保障
手段和壓力系統。并且在課上王晶老師強調三者的順序不能變,依次是團結權、爭議權、談判權。如果爭議權沒有在談判權之前,就不能有真正意義上的談判權。西方發達國家勞動三權的實現過程表明歷史是不能逆轉的,中國同樣不能例外,不可以先談判再爭議。客觀規律是不可被破壞的。
盡管不同的老師對于勞動三權關系的理解不盡相同,但是有一點是肯定的,他們都認同勞動三權在保證勞動者權益上的積極意義,并且都認為集體談判權是勞工集體權利中很重要的內容。
二、集體談判制度的定義及功能
集體協商談判制度作為一種法律制度,其核心是集體談判權。集體談判權是指勞動者集體為保障自己的利益,通過工會或其代表與雇主就勞動條件和就業條件進行協商談判,并簽訂集體合同的權利。集體談判權是勞動者集體權利的中心權利,集體談判的目的是簽訂集體合同。
集體談判有很多功能。從經濟功能上看,集體談判決定勞動者被雇傭的具體待遇和條款;從管理功能上看,集體談判建立在談判雙方相互依賴、互有否決權基礎上的政治過程;從決策功能上看,集體談判使工人通過他們的工會代表,參與到指導和規范他們工作生活的政策的制定過程之中,這是對資方單方面行動自主權的一種限制。
三、勞動三權對德國集體談判制度的影響
德國作為社會市場經濟的法治國家,戰后一直奉行社會市場經濟原則,逐步形成了雙軌并行的德國雇員利益代表機制和“勞資自治”的勞動關系調節模式。雙軌并行的德國雇員利益代表機制主要體現在: 企業職工委員會的企業內部利益代表,即職工委員會與企業管理層一同協商探討與雇員密切相關的勞動權益問題;和行業層面的外部利益代表,即工會與雇主協會在跨企業層面進行的勞資談判。在德國,雇主和雇員都有各自強大的組織為利益代表,勞資雙方集體談判和簽訂集體合同成為協調勞資關系的基本形式。而德國的勞資集體談判一般都在產業層次進行。德國是推行集體談判制度既早又好的國家之一。
勞動三權是德國集體談判制度的基礎和保障。
(一)團結權是德國集體談判的前提和基礎。
團結權是集體談判的前提和基礎,沒有團結權,德國的勞動者就無法行使團體交涉權。集體談判以勞動者團結起來組成工會為前提和基礎。力量分散的單個勞動者是無法進行集體談判的。德國不僅在憲法上規定了團結權,而且還將“一般結社權”與“勞動團結權”做了明確區分。德國對結社權的保護始于《魏瑪憲法》。《魏瑪憲法》第159條規定:無論何人及何種職業,為保護和增進勞工條件及經濟條件的結社自由,均應予以保障。限制或妨礙此項自由的法規及契約,均屬違法。1949年5月制定的《基本法》也明確規定保障勞動者的團結權。勞動團結權是勞資雙方協約自治制度的基礎,而爭議權一向被認為是協約自治原則的核心內容。
勞動團結權具有生存權、勞動權的意義,它不以追求政治、經濟、文化上的遠大目標為目的。團結權屬于勞動法的范疇,是勞動者為了維護或改善勞動條件,保護工作安全而組織和參加工會的權利。沒有團結權,就不會有勞動三權中的其他兩種權利,團結權是德國集體談判的前提和基礎。
(二)集體爭議權是德國集體談判的保障和壓力手段。
德國學者說過:“如果用和平、妥協、調解、仲裁等達成協議的所有可能被排除和所有手段都用盡之后,罷工和關閉工廠是迫使對方在談判上讓步的‘最后的武器’。”當集體談判或團體協商陷入僵局或破裂,或資方拒絕談判時,為實現勞資協約自治原則,工會可以行使爭議權向資方施壓,促使其重新回到談判桌前;或在無法達成協議時,通過仲裁程序實現勞資協約自治的最終目標。但是罷工和關閉工廠畢竟是一種經濟戰,除了會給勞資雙方帶來巨大損失之外,還會給社會公眾或第三方帶來不便,甚至還會影響有關公眾健康安全的商品和服務的供給。因此,勞動法在規定勞資雙方享有爭議權的同時,也對爭議權的行使進行了限制。
德國的罷工權也經歷了一個漫長的過程。德國俾斯麥政府曾以鎮壓社會民主黨的名義于1878年通過《反社會黨人非常法》,將工會組織和工人運動置于非法地位。1890年德國廢除《反社會黨人非常法》,但是關于組織工會和罷工斗爭的不合理限制仍大量存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后,罷工權才逐步成為德國立法承認乃至保護的法律權利。根據德國基本法和結盟自由這一神圣原則,罷工和停工在勞資沖突中是合法的手段。當德國工會組織一次罷工時,它們會進行全體成員投票來獲得集體行動的必要支持。德國的勞資糾紛相對于其他國家還是比較少的。
集體爭議權是德國集體談判的保障和壓力手段。
(三)集體談判權是集體談判的核心。
我也認同王晶老師和程延園老師的觀點,認為勞動三權中以集體談判權為核心。團結權和爭議權的目的均是為了集體談判,集體談判權是“勞動三權”的核心。團結權使單個力量薄弱的工人可以組成一個團體來尋去自己合理的訴求;工人要求的利益其實是對雇主財產權的限制,雇主不會心甘情愿去做的,這就需要爭議權,爭議權尤其是罷工權給雇主一種外在的壓力,使得雇主不得不與工人談判,從而確保集體談判權的實現。團結權和爭議權都是為了保證集體談判權的實現。
四、實際調研中自己對勞動三權的體會
五月底跟著老師去廣州深圳調研,體會頗多。印象最深的是對兩個工會主席的訪談。一個工會主席是一家傳統的汽車配件生產廠的,跟我們訪談時他剛剛結束第二輪的集體談判,談判結果很令他不滿意,雇主相當不配合而且很強硬,他說“罷工”對于雇主已經不管用了,第一次的罷工已經使得雇主做好了各種應對工人再次罷工的準備,包括備好庫存,雇傭臨時工等,他的整個談話都顯得很無奈。當爭議權作為最后的武器都沒有用的話,集體談判權還能實現嗎?當罷工這一壓力機制都不能發揮作用了,勞動三權還能真正的實現嗎?如何來保證中國工人的勞動基本權,我想這需要我好好的思考。另一個工會主席是一家做港口的公司,企業很有錢,他們最近的一次罷工取得了很好的成績,每年工資都有不同幅度的提高,哪怕是在金融危機時期。相比之前的工會主席,這個主席顯得很“霸氣”,他們的工會有專門的辦公區,就在人力資源部對面,在這家企業,罷工作為一種壓力機制很有效。兩家企業截然不同的狀況使得我在反思是什么原因導致的?我覺得跟企業的盈利狀況和員工的“獨特性”有一定的關系。不論正面還是反面,我都從中體會到爭議權在保證集體談判權中的重要作用。勞動三權作為一個整體才能真正發揮作用,缺少任何一個或者將其割裂開來都無法真正實現勞動的基本權。下來我會好好整理這次訪談,希望可以對勞動三權再做進一步分析和探討。
[1]王晶.集體談判制度建構與勞動三權[N].工人日報.2011(4).
[2]王晶.集體協商談判制度須以勞工三權為基礎[J].中國人力資源開發.2012(7).
[3]程延園. “勞動三權”:構筑現代勞動法律的基礎[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5(3).
[4]橋潔洋三.勞動基本權的理念上法解釋學.[M]1984.10.
[5]常凱.勞動關系學 [M].北京:中國勞動社會保障出版社,2005.9.
[6]石美遐.市場中的勞資關系:德、美的集體談判[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6.
[7]王慧. 德國的集體談判[J].工會理論與實踐.中國工運學院學報.1996(10).
[8]王福東,于安義.德國企業的集體談判制度[J].外國經濟與管理,1997(4).
D92
A
1671-864X(2015)12-0071-02
高盼盼,女,漢,河北邯鄲,碩士在讀,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