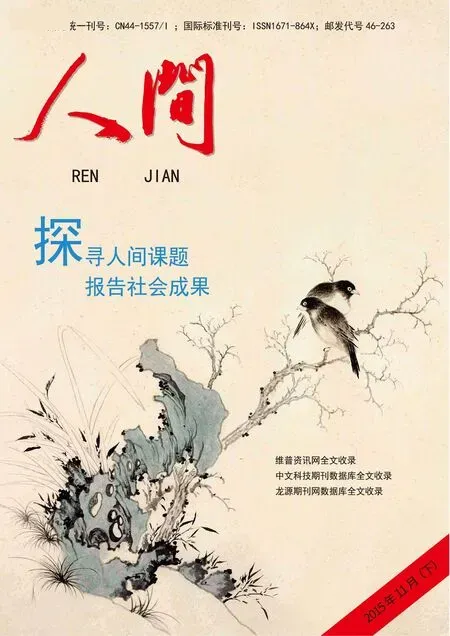西方制度“善”與道德“善”的研究路徑分析
宣杰
(貴州財經大學馬克思義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0)
西方制度“善”與道德“善”的研究路徑分析
宣杰
(貴州財經大學馬克思義學院,貴州 貴陽 550000)
制度倫理的思想源自于規范倫理學,歐洲文藝復興以后,契約論的產生以政治哲學的形式對制度倫理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提升,制度倫理作為學說,則成于羅爾斯。在制度倫理與人的道德發展的關系上,羅爾斯認為:對于社會來說,制度的價值選擇原則處于優先地位,個體的道德處在從屬地位。
西方;制度正義;道德發展
《倫語》里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后人經常把這句話當作“德為先”的依據,形成了重德輕制的傳統,但制度倫理與道德哲學的研究發展預示:正如博弈雙方可以實現“共贏”那樣,制度與道德的“共善”是可能而且必要的。本文僅從制度“善”與道德“善”的中西方視野作一個文獻路徑分析。
制度倫理的研究。制度倫理的思想源自于規范倫理學,最早的研究始肇于古希臘斯多葛學派的自然法理論,歐洲文藝復興以后,契約論的產生以政治哲學的形式對制度倫理思想作了進一步的提升,制度倫理作為學說,則成于羅爾斯的《正義論》。
在斯多葛學派那里,自然生活就是理性生活,自然法就是理性法,原因是:上帝是有理性的,人也是有理性的,理性是統治整個世界及人類社會的法則,在這個法則下,各邦人民可以平等,在理性的指引下判別善惡,過上一種融合著人性與自然性的和諧生活。斯多葛學派的哲學立場是:道德的高尚性是惟一的善,因為惡行不道德,作惡是不利的;而善行是有道德的,行善是有利的。這一思想在古羅馬的西塞羅那里有了新的討論,西塞羅在《論義務》中說,“有德”與“有利”并不是對所有人的來說都一致的關系,事實上不少人認為,高尚的行為并不一定對自己有利,對自己有利的事情也不一定高尚,這種觀點甚至被當作“智慧”,為此需要一種把“有德”和“有利”統一起來的規范,以確保人們不會偏離義務,也即以規范來保護義務和正義。
這一思想在社會契約論那里有了極大的發展。霍布斯認為,人們在自然狀態下無法遏止由生存競爭帶來的戰亂與殺戮,為了類的存續,人們必然訂立契約,讓渡出部分權利,形成公權,這就是國家的最初來源,但是國家主導了契約帶來的公權之后,也有可能把公器用于正義的反面,使民眾受害,在這種情況下,民眾有權重訂契約,恢復正義。洛克認為,人有三大基本權利——生命、自由與財產權,這是自然法賦予的三大權利,國家制度的合理性根據就是在于能否維護公民的這些基本權利,如果不能,那么制度就不符合倫理原則,不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盧梭進一步認為,個人的自由權利是社會契約的產物,一切的權利非來自于自然,而是以契約為基礎,建立在約定之上。分散的個人力量應該通過契約組成一個聯合體(這一思想后來對馬克思的影響很大),使得人們既可以實現個人的基本權利,又可以享受自然狀態下的自由,倘若契約可以達到這個程度,那么它就以公共利益為依歸,就體現了公意,公意是人民最大的幸福。羅爾斯基本沿襲了社會契約論的思路,并在這一基礎上構筑了宏大的制度倫理學說。在1971年出版的《正義論》中,羅爾斯從政治學、法理學、社會學、經濟學等多學科的交叉中考察了制度的社會正義問題。他把研究的焦點投射到社會制度安排的正義與合理性上來,主張通過社會制度的倫理分析剖開由此形成的社會基本結構,審察與判斷由制度帶來的權利與義務分派、社會利益劃分的公正問題。羅爾斯的突出貢獻在于他提出了制度的倫理價值原則,提出其邏輯根據,并試圖打通制度倫理與個體道德之間的關系,使得斯多葛學派的利益與理性法則、西塞羅關天“有利”與“有德”的規范、社會契約論的權利與契約等等關系通過一個制度評價的理論平臺連接起來。《正義論》發表之后,制度倫理思想在西方影響很大,一度被推崇為政治哲學、道德哲學、法律哲學、社會哲學的最偉大的成就。
除了羅爾斯以外,比較有影響的研究制度正義的西方學者還有諾齊克(代表作為《無政府、國家與烏托邦》)和巴利(又譯為巴里,代表作有《社會正義論》、《正義諸論》和《作為公道的正義》)。諾齊克與羅爾斯同為哈佛的哲學家,兩人來往甚密,但在學術觀點上有分歧。兩人的學術興趣都在于社會正義問題,羅爾斯傾向于強調社會平等,是社會正義論的突出代表;諾齊克則側重于個人自由(集體福利與個人權利),是程序正義論的代表。兩人的思想分別沿襲著近代以來西方社會思潮形成的所謂自由民主傳統最重要的兩翼。巴利的《作為公道的正義》則提出,正義有三種模式,分別是“作為互利的正義”,作為“相互性的正義”和“作為公道的正義”,他認為“作為公道的正義”是更完善和更有吸引力的正義觀念。
從國外關于倫理學與道德發展理論研究的趨向來看,有兩個特點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倫理學的研究范式從德性倫理向規范倫理偏移;二是道德發展研究從哲學思辨走向實證研究。在羅爾斯這里,制度倫理研究終于與人的道德發展理論連接起來了。羅爾斯認為,功利主義將德性倫理推廣到社會中去,直接應用于制度本身,但是,規范倫理的原則與德性倫理的原則之主體和對象截然不同,個體可以在道德選擇上為了全局利益、長遠利益放棄自己的當前利益,這是一種道德自由,但是,在制度安排上不能因為這理由要求個體為了大部分人的利益或長遠利益而放棄私利,就算在事實上有這樣的必要性或可能性,也不能通過制度的強制性來完成。羅爾斯的研究表明,社會基本結構中有不同的社會成員,各自有不同的社會地位與利益訴求及前景,這些都是由政治體制、經濟體制和社會條件的合力決定的,所以,社會結構的制度安排成了正義的主題。在制度倫理與人的道德發展的關系上,羅爾斯更注意前者的作用——對于社會來說,制度的價值選擇原則處于優先地位,個體的道德處在從屬地位。
從西方倫理學與道德發展理論學說的演進來看,最終在羅爾斯這里有一個交叉,雖然這個交叉點在《正義論》中還未有它應有的光亮,但這并不能降低它的理論價值。我相信,這兩種理論的交匯必將給世界提供一個廣闊的學術視野,使我們可以將制度倫理作為維度,把人與人的關系、人與社會、國家的關系更明晰的方式呈現出來,從制度的向善發展中尋求人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之路,使人在道德發展中通向幸福生活。
[1]方軍:制度倫理與制度創新[J].中國社會科學,1997(3)
[2]萬俊人:制度倫理與當代倫理學范式轉移[J].浙江學刊,2002(4)
D503
A
1671-864X(2015)11-0114-01
宣杰(1975-),男,漢族,廣東廉江人,副教授,法學博士,貴州財經大學馬克思義學院,研究方向:制度倫理,德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