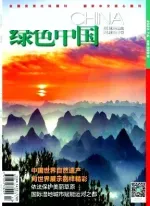十年博弈 怎一個“難”字了得!
文 段梅紅

2005年2月,《煙草控制框架公約》(以下簡稱《公約》)正式生效,成為世界衛生組織(WHO)主持下達成的第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國際公共衛生公約。2003年11月,中國成為該公約的第77 個簽約國。2006年1月9 日,《公約》在中國正式生效。
到2016年1月9 日,《公約》在我國已經生效十年……
2015年,中國控煙事業上的一大亮點無疑是6月1 日正式施行的《北京市控制吸煙條例》。實施半年來,公眾對控煙的滿意度由原來的42.26%提高到81.3%,它為北京贏得了WHO特別授予的“世界無煙日獎”,也被國際控煙高級會議譽為“北京經驗”。
成果喜人,但眺望中國的控煙之路,更多的可能還是或只能是兩個字:艱難!
難在解不開的死結:賣煙控煙一家親
一位控煙專家說:煙草控制的領導權掌握在煙草業手里,這就決定了中國控煙是艱難的過程。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煙草制品生產國,也是最大的煙草制品消費國。在控煙成為全世界共識的今天,中國的煙草消費量和煙草生產量卻一直呈上升趨勢。
這似乎讓人難以理解。但在全球控煙研究所中國分中心主任楊功煥看來,我國控煙不力的根本原因就是政企不分,履約進程遭到了煙草行業的大力阻撓。
加入《公約》之后,為了履約,我國成立了由工業和信息化部、衛生部、外交部等8 個部委組成的履約工作部際領導小組,工信部為組長單位,而工信部同時又是煙草專賣局的主管。正因如此,工信部被指一手控煙一手賣煙,所做出決定難辨是企業決策還是政府決策。而其下屬的煙草專賣局與中國煙草總公司則實為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由于政企不分,煙草專賣局成為一體兩面的企業,可以根據不同場合不同內容的需要自如自由地切換角色。
2010年11月,《公約》締約方第四次會議在烏拉圭舉行,會議旨在探討《公約》中對涉及“煙草制品成分管制和煙草制品披露的規定方面”的實施準則。但由于以工信部和煙草專賣局人員為首的中國代表團多次提出反對意見,并強調煙草是中國重要的支柱產業,中國多次被提名獲得“臟煙灰缸”獎。
“你們要控煙?告訴你們,這是在賣國!”這是發生在《公約》中國談判團內的一幕。代表煙草行業的國家煙草專賣局與作為控煙主體的衛生部經常吵來吵去,在履約談判團內早已是公開的秘密。“控煙就是賣國!”這句名言即出于此。
其實,當《公約》還在談判過程中時,我國煙草業就已經介入控煙了。被控煙專家們稱為“雙對”的《WHO〈煙草控制框架公約〉的對案及其對中國煙草影響對策研究》一書就是由國家煙草專賣局組織編寫的,該書對《公約》中的每一條款都提出了應對策略,被煙企視為“營銷寶典”。中國社會科學院國際法研究所研究員趙建文直言:“雙對”的性質就是中國煙草業抵制《公約》、阻撓控煙的“策略總匯”,其出臺有損國家形象和信譽,更像是政府部門為企業代言。
在一次全國煙草工作會議上,工信部負責人表示,“要把控制煙葉生產規模作為行業工作的中心任務”,但在談到煙草產業工作時又要求煙草產業要“切實提高運行質量和效益,努力實現又好又快發展”。兩段陳述前后矛盾卻也“正常”因為作為中國履約的主導部門,工信部本來就是集兩個對立角色于一身。

所以,我國控煙機構和控煙專家們提議,控煙工作應從國務院層面來組織,將煙草專賣局從控煙領導小組中分離出來。遺憾的是,這項提議一直未得到積極回應。
難在無稽:“慈善”拒煙竟是個事兒——煙草利益集團遠比我們想象的要強大
北京控煙協會會長張建樞說:“慈善事業應有利于人民健康、社會文明和環境保護,而煙草則有悖于健康宗旨、社會文明,有悖于國際公約。”
2015年10月31 日,中國首部《慈善法》(草案)在中國人大網公示,征求社會意見。草案中新增了一條關于限制煙草企業利用慈善捐贈宣傳煙草制品的規定,即第四章第四十三條:“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利用慈善捐贈,宣傳煙草制品及其生產者、銷售者等法律法規禁止宣傳的事項。”
然而,這一條款卻遭到部分網友反對,引發了“該不該一刀切”的公眾熱議。一些網民認為,慈善作為一項全民參與的社會化和公益性事業,沒有理由拒絕一個合法企業的慈善捐贈。審視煙草企業捐贈行為,必須厘清“慈善”和“營銷”的是非邊界。一時間,不應一棒子打死、不妨試之禁之、不必矯枉過正、為煙企預留一份權利空間的說法甚囂塵上。
在中國政法大學衛生法研究中心舉辦的“控煙與慈善捐贈”研討會上,該中心特邀研究員于秀艷說:“通過慈善活動,企業一般可以獲得雙贏。一方面對社會作出貢獻,另一方面也使企業及品牌得到社會認同,獲得商業利益。”但“煙草商做慈善卻只有單贏,因為社會對于煙草企業及其產品、品牌的認同度越高,意味著人們越愿意接納煙草制品和吸煙行為,從而更多地消費煙草制品,導致社會危害的增大,最終獲益的只有煙草企業單方。”她強調,慈善活動不得損害社會公共利益,這是慈善法的基本原則。
事實上,煙草業早已開始侵入慈善業。中國控煙協會2015年4月發布信息稱,通過該協會連續三年的監測結果可以看出,捐資助學與扶貧助困救災仍然是煙草業進行煙草贊助采取的主要方式,占58%。控煙專家、新探健康研究發展中心副主任吳宜群指出,該中心一項調查顯示,通過公益形式捐贈中小學并借此進行宣傳的煙草公司比例已由2013年的16%提高到2015年的31%。所以,“如果不禁止煙草企業捐贈,無疑會給煙草企業通過慈善捐贈留名達到營銷之實提供更多的機會。”
其實,慈善組織不得接受煙草企業的捐贈是一種國際慣例,“金磚五國”中,除了中國,其他國家都有禁止煙草贊助包括煙草捐贈行為的明確規定,國際上還有29 個國家禁止煙草企業的所謂承擔企業社會責任的行為。而在我國慈善領域中的最基本大法——《慈善法》的立法過程中,這居然成了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
難道還要把“天才出于勤奮,煙草助你成才”的標語寫上學校的墻壁?還要用“金葉基金”去支持“母親水窖”?國家級的立法成了控煙與反控煙力量博弈的一個平臺。這至少說明一點:煙草利益集團遠比我們想象得要強大。
如此無稽的事不止慈善遭遇煙草的“糾結”,還有“煙草院士”,還有以煙草冠名的“青年領袖”……
難在缺乏約束力——還差一部國家層面的《公共場所禁止吸煙法》
10年間,德國從“歐洲青少年吸煙大國”下降為吸煙率最低的國家之一。取得這樣的成果,公共場所禁煙是這一成果最重要、最有效的舉措。
還在2014年,筆者就控煙問題采訪吳宜群時,她就提到應該加快制定國家層面的《公共場所禁止吸煙法》。因為“沒有國家層面的立法,就不可能全面、有效地保護所有民眾不受煙草煙霧危害。”
2014年11月24 日,國務院法制辦公室發布了《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條例(送審稿)》,其中第二十五條明確提出,全面禁止所有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對此《條例》,社會輿論普遍點贊,并期待它審議通過,從而成為我國“史上最嚴”的禁煙令。
為什么“史上最嚴”之后,還要有一部國家層面的禁煙法呢?
目前,已有100 多個簽約國制定了公共場所控制吸煙法,其中44 個簽約國施行了全面無煙法律。但在我國,《公約》生效已經10年,控煙法律法規的制定始終沒有列入國家立法規劃。
其實,《公約》雖是一個具有法律效力的公共衛生公約,但它是一部國際性公約,不能直接約束地方政府。只有單獨立法,將其轉化為國內法,才能成為法律依據,才能具有約束力。盡管上海、杭州、哈爾濱、天津、廣州、蘭州、青島、深圳等多個城市都出臺地方條例,但由于時至今日我國仍無一部專門針對公共場所禁煙的法律,各大城市禁煙令有規難行,以致多年來“無一罰單出現”,各項禁令形同擺設。
按照《公約》要求,我國應在5年前的2011年1月9 日即在室內公共場所和室內工作場所實現100%禁煙。而當時我們的控煙履約成績只有百分制的37.3 分,離及格線還差很遠,履約情況處于100 多個公約締約國的最末幾名。
2012年《WHO 煙草控制框架公約進展報告》中指出,全球《公約》履約滿5年的國家,40%以上對16 類公共場所和工作場所都有全面禁煙規定,90%以上國家均在6 類以上場所,包括公共交通工具、政府辦公大樓等有全面無煙政策。而中國僅在醫療和教育系統兩類場所有全面無煙政策規定,故只得了2 分;而在禁止煙草廣告、促銷和贊助方面,中國為0 分!
2013年5月,WHO 在最新出爐的針對14個發展中國家進行的履約排名中,中國僅排第13名,得分為44.6 分。僅僅高于俄羅斯。而這14個國家多數都是和我國一樣從2006年開始正式履行《公約》的。就在這一年,排名墊底的俄羅斯也出臺了《保護公眾健康免受煙草危害法》,公共場所全部禁煙,提高卷煙消費稅率,購買煙草合法年齡提高至21 歲。一系列控煙措施實施后,俄羅斯的吸煙率下降了6 個百分點。
記得當年召開新聞發布會時,楊功煥憂心忡忡地說,如果我們的現狀得不到改觀,下次再評怕就是倒數第一了!
其實,就從立法本身而言,制定一部全國性控煙法律沒有任何技術難度。在全球控煙的大背景下,許多國家的吸煙人數尤其是青少年吸煙人數都在下降,只有我國不降反升,這與我國對煙草產業過于寬松的法律環境有很大關系。同時也不得不讓人再次感嘆來自煙草利益集團的阻力。
難在對未來悲情的漠視——然而,煙草業造就的經濟效益該還債了!
世界衛生組的研究表明:若一個國家當年的煙草稅是若干億美元,20年后,這個國家將不得不用當年所征收煙草稅的2.8 倍支付因吸煙帶來的健康危害,且不包括由吸煙導致的其他損失。
2015年國慶七天長假剛過,人們就從網上讀到了來自英國世界權威醫學雜志《柳葉刀》的一條消息:中國1/3 的年輕男性將死于煙草。這項由英國牛津大學、中國醫學科學院和中國CDC共同領導的研究警告:到2030年中國每年因吸煙死亡的人數將達到200 萬。所以,“對中國來說,大規模禁煙是未來數十年內防止殘疾和過早死亡最有效和最劃算的辦法。”
然而,我們卻不能不面對一個殘酷而又尷尬的現實。
雖然“吸煙有害健康”早已成為常識,雖然加入《公約》已經10年,但我國的煙草生產量和消費量卻逐年攀升。2002年,我國的煙草產量為1.75 萬億支,控煙10年的2012年,煙草產量卻上升至2.58 萬億支,增加了近50%,占全球產量的43 %。
楊功煥認為,這與煙草關乎稅收是分不開的。據了解,2009年煙草行業工商稅利為5131.1億元,2014年則高達10517.6 億元,約占全國財政收入的7%。

但煙草也讓我國付出了巨大的健康成本。據2015年7月由WHO、美國CDC 和中國CDC 此前聯合發布的首次“全球成人煙草調查-中國部分”調查結果顯示,目前,我國吸煙人數超過3 億,其中男性吸煙率為52.9%;72.4%的非吸煙者遭受二手煙的危害,為全球之冠,其中38.0%的人每天受到暴露;我國因吸煙相關疾病死亡的人數,每年在140 萬人左右,約占全球總數的1/3。
吸煙是罹患肺癌的第一致病因素。不久前結束的《第七屆中國肺癌南北高峰論壇暨2015年中國肺癌防治聯盟年會》披露,預計到2020年,我國肺癌發病人數將突破80 萬,死亡人數將接近70 萬。
不僅如此,煙草還讓我國付出了巨大的社會成本。
1998年,我國煙草業所做出的綜合社會經濟貢獻(含就業貢獻)仍大于其所導致的總社會成本,但從1999年開始,煙草業的綜合收益已經開始低于其帶來的綜合成本,而且這一差距越來越大。
以2005年為例,因吸煙而造成的直接和間接成本高達2526 億元,相當于GDP 的1.4%,而當年,煙草業上交的利稅總額只有2400 億元。2008年可歸因于煙草使用的總社會成本為289 億美元,是2000年的4 倍。2010年,煙草業的總經濟效益約為2379 億元,而煙草業造成的社會成本卻高達2997 億元。
“還債”的日子,或許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