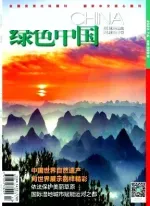花朵般綻放的土豆
文 張明

隴中高原深秋的鄉村,隨處能看到這樣的景象,莊戶人家灶頭高巍巍捂蓋蒸煮著一鍋東西,呼呼白汽從鍋蓋頂蒸騰,翻卷而上,直沖屋梁,彌漫全室,滿門滿窗朝外奔涌擴散,可老奶奶或小姑娘仍毫不怠懈地朝灶塘里添加柴禾,或多或少,或緊或慢,好像在跟蒸煮的東西較勁兒似的。等火候已好,時辰既到,才小心敏捷地將鍋蓋揭除,一陣更為浩大的白汽過后,無數花朵在熱鍋里絢爛綻放,如潔白的絮團,像神圣的牡丹……這歷經千蒸萬煮之后,花朵般驚心綻放于熱鍋里的,正是隴中的土豆。
隴中的土豆品質極好,蒸煮過程中皮囊無法包裹內在的實誠,便如花般綻放了。如花綻放的土豆,咬一口,沙沙的,黏黏的,面面的,滑滑的,沒有更多土豆的“菜”味或澀麻味,幾乎跟白饅頭一樣好吃。在曾經的歲月里,據說有隴中農民煮吃土豆,擔心太過奢侈老天爺看見怪罪的,竟不敢讓兒女拿到屋子外面享用。這故事雖然不乏夸張色彩,卻反映了土豆在人們心里的分量。是啊,土豆一度是隴中人最靠得住的食物,秋天能收幾百斤藏進地窖,內心便有了底氣,日子也有了指望。
收獲土豆的季節,是隴中孩子肚子最充實的時候,遇到生產隊人手不夠,隊長會向村學告急,村學老師義不容辭地帶學生幫忙,小學生個頭小,卻腰腿靈便雙手敏捷,掇拾剛挖出泥土的土豆,比壯勞力都頂用。勞動到晌午時分,生產隊便會煮幾筐土豆,如花綻放的幾大筐,抬到田間地頭,給學生和社員當午飯。土豆掬在手中,手心綻放如花,土豆舉到嘴邊,嘴角綻放如花,土豆吃進肚里,心情綻放如花。隴中人吃土豆一度非常堅韌,“午飯囫圇煮,晚飯切破煮”;隴中人吃土豆一度也十分樂觀,“一天三頓飯,全是羊、魚、蛋”——土豆又名洋芋,“羊、魚、蛋”者,即“洋芋蛋”之謔稱也。
在中國,名稱前加了“洋”字的,多跟外國有掛葛,如“洋槍洋炮”“洋鬼子”“ 洋樓”等,土豆據說最早產于美洲,后來傳入歐洲,再輾轉引入中國的,所以被稱作“洋芋”。無意間欣賞過荷蘭印象派畫家高的名作《吃土豆的人》,被燈光籠罩下寧靜祥和的氛圍所震撼,簡陋破敗的屋子,質樸厚道的勞動者形象——粗大有力的手掌似乎沒洗凈泥土,安于天命的神情帶了某種宿命意味,熟悉得叫人心中隱隱發疼,尤其飯桌盆子里的土豆,圓圓的,熱熱的,一定散發出濃濃的香氣,竟與隴中土豆存在直接血緣……那遠涉重洋的種子,一旦扎進隴中的黃土,便相見恨晚難分難舍了。高大巍峨的六盤山橫亙于隴中東部,造就了十年九旱的嚴酷現實,也為土豆生長提供了適宜的土壤和氣候。隴中高原不遭遇土豆,是隴中高原的遺憾,土豆不落戶隴中高原,是土豆的悲哀。黃土里滾大的隴中人,對土豆有著無與倫比的感情,三天不吃便饞得不行,好像身體和日子里都缺了什么似的。當然伴隨生活的改善,土豆不再是隴中百姓飯桌上的主宰,但聰明的鄉親們在傳統烹飪的基礎上,想方設法變換廚藝,煎、炒、烹、炸、燒、煮、燉、扒、烤,十八般武藝全配上了用場,烹調出幾十種美味菜肴——土豆絲,土豆條、土豆片,土豆泥,土豆,土豆餅……每個類別又隨火候、手法及佐料的不同,風味迥然有別,比如僅土豆絲的名目下,就有醋溜、青椒、麻辣、酸辣、家常等等:隴中人吃土豆,可謂吃出了花樣,吃出了水平,吃出了境界。
高原黃土千百年不變,干旱氣候也千百年不變,隴中人只有在種植上狠下功夫,在品種培育上著意創新,并且通過最鄉土最實惠的想象,給了土豆們最詩意的命名:“黑美人”“糙西施”“藍妃子”“胖妞妞”“紅媳婦”……眼下,這些性情獨具的隴中“美人”們,早已“紅杏出墻”名滿天下,通過樸實的包裝,等于穿了素雅的嫁衣,乘坐現代化交通工具,遠嫁江南朔北,遠嫁全國各地,甚至飄洋過海衣錦還鄉,去美洲、歐洲“娘家”展示她“歷盡磨難”后獨特的隴中品質。
隴中土豆,品質花朵般綻放,盛開在百姓的飯桌上,盛開在中國的記憶中,盛開在歷史的坐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