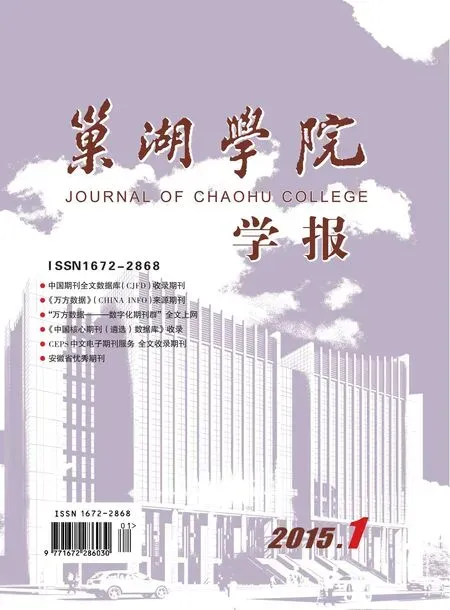安徽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實證分析:1995-2012
劉紅梅
(巢湖學院經濟管理與法學學院,安徽 巢湖 238000)
據統計資料顯示,2012年安徽省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為5685.6億元,相比1995年的586.5億元,增長了8.69倍,比2011年增長了16%。可見,安徽省的消費市場增長潛力巨大。但從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較來看,城鄉之間仍然存在很大的差距,如2012年安徽省城鄉居民消費水平比值為2.86。另外,從人口比重來看,2012年,安徽省總人口為6902萬人,其中城鎮人口比重46.5%,農村人口比重53.5%。農村人口仍然占安徽省總人口的大部分,但農村消費水平明顯低于城鎮。因此,研究安徽省城鄉居民的消費結構,提升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對于安徽省經濟增長和突破現存的城鄉二元消費結構,以及緩和城鄉差距問題都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1 城鄉居民八類消費支出分析
按照安徽省統計年鑒的分類,居民消費支出主要分為食品、衣著、居住、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雜項商品與服務,共八類。圖1、圖2分別反映的是1995-2012年期間,城鎮和農村居民各類消費品支出數額的變動狀況。
從圖1、圖2中很清晰的看出,自1995年以來,城鄉居民各項消費支出都呈現逐漸上升趨勢,尤其是近十年以來增長幅度更大。其中,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1995的3161.41元增長到2012 年的 15011.66 元,增長了 3.75 倍;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從1995的1070.64元增長到2012年的5555.99元,增長了4.19倍。城鎮居民消費水平明顯要高于農村消費水平,2012年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比值為2.7。這顯然與當前城鄉收入水平差距有關,據統計數據顯示,2012年城鎮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為21024.21元,農村居民家庭人均純收入為7160.46元,城鎮居民收入是農村居民收入的2.94倍。

圖1 1995-2012年間安徽省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圖2 1995-2012年間安徽省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

圖3 1995-2012年間安徽省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變化圖
同時,占城鄉居民消費支出中最大比重的是食品支出。食品支出總額占消費總額的比重稱之為恩格爾系數。圖3顯示的是城鄉居民恩格爾系數的比較。
從恩格爾系數來看,城鄉居民的食品支出占各自收入的比例整體呈下降趨勢。然而農村居民家庭恩格爾系數一直遠高于城鎮居民家庭,但系數的差異呈現縮小趨勢。城鎮居民家庭的恩格爾系數從1995年的53.7%下降到2012年的38.7%并從1998年開始低于50%。農村居民的恩格爾系數則從 1995年的 58.41%下降至 2012年的39.25%,并從2001年開始下降到50%以下。隨著食品消費支出的降低,城鎮居民家庭在教育文化娛樂、交通和通信、衣著、居住及醫療保健等方面均有增加,而農村居民家庭居住支出增長幅度較為突出。
2 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的實證分析——基于ELES模型
ELES模型是指擴展線性支出系統,是經濟學家Liuch于1973年提出的。ELES模型是將人們的消費需求分為基本需求和追加需求,基本需求與收入水平無關。其函數形式為:

式中,Vi為居民對第i種商品的消費支出;為第i種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是對所有商品的基本需求支出為第i種商品的邊際消費傾向。令則上述函數形式可以化為,即為一個線性方程。

將上面求得的ai、 bi*的估計值代入上式,即可求得PiXi0。[1]利用計量經濟學Eviews6.0對安徽省城鄉居民消費結構的ELES模型參數進行估算,其結果見表1和表2。根據T值檢驗,收入對八大類商品消費的影響是顯著的,由R2和F值判斷各方程的擬合度較好。

表1 安徽省農村居民ELES模型參數估計值

表2 安徽省城鎮居民ELES模型參數估計值支出項目
2.1 基本消費支出
根據表1和表2,安徽省農村居民對八類商品的基本消費支出為-517.852元,而城鎮居民對八類商品的基本消費支出為1929.733元,同時,城鎮對于每一類商品的基本消費支出都遠遠高于農村。這說明城鄉之間的消費差異巨大,存在二元消費結構,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因為城鄉收入間的差距。我們可以從樣本決定系數R2中看出,除去農村居民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樣本決定系數為0.881以外,其他城鄉居民各項消費支出的樣本決定系數都達到0.9以上,說明各項消費支出變化的90%可以由收入來解釋,收入是影響消費的重要變量。
2.2 邊際消費傾向
從邊際消費傾向來看,農村居民總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802,城鎮居民總的邊際消費傾向為0.687,這表明當收入增加時,農村居民將更多的收入用于消費支出,這符合邊際消費傾向遞減規律。而八類商品中,城鎮與農村對于食品的邊際消費傾向最大,其中,城鎮食品邊際消費傾向為0.24,農村食品邊際消費傾向為 0.285,農村要高于城鎮,這說明對于安徽省來說,尤其在物價高漲的當今社會,城鄉居民的生活成本壓力較大,在收入增加的情況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投入最多的就是食品。除了食品以為,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是教育文化娛樂服務(0.093),而農村對這一類的支出明顯低于城鎮(0.054),這充分說明了城鎮居民更重視教育和文化娛樂的投入,但城鄉居民對于交通通信的邊際消費傾向是相同的。在居住方面,農村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0.175)僅次于食品,而且這一邊際消費傾向要遠遠高于城鎮(0.079),這主要是因為農村居民大多擁有宅基地,當收入增加時,農村居民在滿足食品需求之后首先改善的就是自己的居住條件,[2]自建房屋,而城鎮居民極少能有自己的土地,同時近些年來商品房價格遠遠超出很多城鎮居民的承受能力,增加住房消費的能力自然受到了限制。在衣著方面,城鎮居民的邊際消費傾向也高于農村,這說明城鎮居民更重視衣著的品牌,以及服裝本身的品質和款式,而農村居民大多數仍停留在穿暖的層次上,對于衣著的品牌和款式沒有更多的要求。同時,由于農村醫療條件落后,沒有相應的醫療保障措施,農村居民基于預防動機,其醫療保健的邊際消費傾向(0.079)要高于城鎮(0.059)。另外,由于近年來國家出臺家電下鄉政策以刺激農村的消費市場,農村居民家庭基本上普及了各類家用電器,相比農村,城鎮居民在這一方面已經基本滿足了需求,這就是農村居民家庭設備的邊際消費傾向 (0.053)高于城鎮(0.036)的原因。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很清晰的看出,城鎮居民更重視享受型和發展型的消費,而農村居民相比還存在不少差距。
2.3 需求的收入彈性
需求收入彈性是用來表示消費者對某種商品需求量的變動對收入變動的反應程度。下面我們以2012年為例,計算安徽省2012年城鄉居民各項消費品的需求收入彈性(見表3)。

表3 2012年安徽省城鄉居民各項消費品的需求收入彈性
從表3中可以看出,城鄉居民的各項商品的需求收入彈性均大于0,說明隨著收入的增加,居民對各項消費品的支出也是增加的。其中,農村居民除了醫療保健以及教育文化娛樂服務的需求收入彈性低于城鎮以外,其他各項都高于城鎮,這說明收入變動對農村居民各項消費需求的影響較大,也證明了農村消費市場具有較大的潛力。農村居民八類消費品中,交通和通信、醫療保健、雜項商品與服務、居住以及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說明這幾類消費品支出的增長速度高于收入的增長速度,這也是未來農村消費市場的熱點。與農村消費市場不同,城鎮居民在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以及居住的需求收入彈性大于1,這也是未來城鎮居民在消費市場所關注的熱點。
3 研究結論與政策建議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安徽省城鎮居民對每一類商品的基本消費支出都遠遠高于農村居民。城鄉居民邊際消費傾向最高的支出項是食品,除食品以外,城鎮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支出項為教育文化娛樂服務、交通和通信、居住、衣著、醫療保健;農村居民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支出項為居住、交通和通信、醫療保健、教育文化娛樂服務、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從需求的收入彈性來看,城鎮居民消費增長高于收入增長的支出項有醫療保健、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娛樂服務以及居住;農村居民消費增長高于收入增長的支出項有別于城鎮,分別為交通和通信、醫療保健、雜項商品與服務、居住以及家庭設備用品及服務。我們從中可以看出,城鎮居民的消費水平和質量普遍高于農村,城鎮居民的消費結構也較農村更為合理。依據以上得出的結論,我們可以采取以下措施來提高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改善其消費結構。
第一,增加農民收入,減少城鄉收入差距。這是提高農村居民消費水平和消費質量的主要途徑。[2]要轉變農業增長方式,促進農業生產發展,積極發展非農產業,拓寬農民增收渠道,繼續加大財政支農的力度,增大對農村農田水利等的投入,加快城鄉一體化進程,減少與城鎮居民消費水平和質量的差距。
第二,繼續增加對農村基礎設施的投入。如改善農村的路、水、電等基礎設施的建設,以及農村廣播電視網、郵電、通信通訊網絡的建設,[3]為農村居民提高消費水平和質量創造良好的環境。
第三,完善社會保障制度。目前主要集中在醫療、教育和住房三個方面,減少居民因大額消費而對現期消費能力的透支[2],提高居民對未來生活方面的安全感。在財政支出方面,應向農村居民傾斜,如進一步促進農村醫療改革,要持續增大投入力度,逐步實現城鄉醫療一體化。同時,要逐步改善農村教育落后的現狀,加大對農村義務教育的投資力度,以減輕目前城鎮與農村在社會保障方面的巨大差距。
第四,積極轉變居民傳統的消費觀念。要加強消費教育,引導居民改善“勤儉持家”的消費觀念[3],開拓新型消費領域,引導居民由傳統的食品、居住等物質消費領域向教育、娛樂、衛生、交通通訊、旅游等精神消費領域轉變,促進農村居民消費結構的升級換代,縮小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異。
[1]張保法.經濟計量學[M].北京:經濟科學出版社,2000:267-268.
[2]趙金蕊.中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變動實證研究:1995-2010[J].廣西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3,(7):24、25、27.
[3]周發明,楊婧.基于ELES模型的中國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實證研究[J].江西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9):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