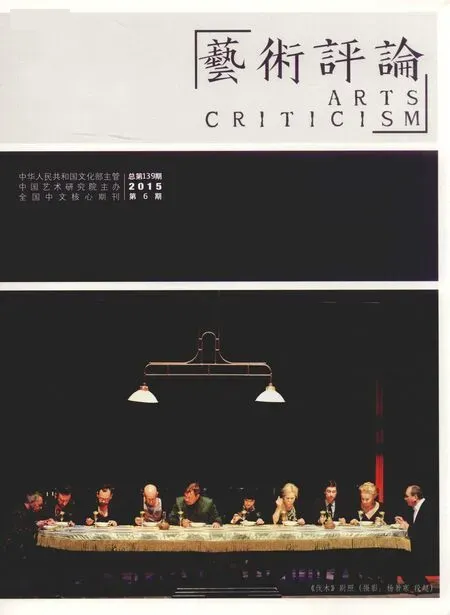吳曉邦與中國現代舞
于 平
吳曉邦與中國現代舞
于 平
一、吳曉邦作為“中國現代舞第一人”
今年7月8日,是曉邦先生仙逝20周年的忌辰。20年來,這是我第一次提筆追憶先師曉邦先生——追憶曉邦先生與中國現代舞的生命關聯。吳曉邦作為“中國現代舞第一人”,其實是有著豐富思想內涵和深刻價值取向的。
二、“代表大多數人利益”的創作取向
在曉邦先生《我的舞蹈藝術生涯》(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9月出版)這一“交待式的自傳”(曉邦先生語)中,有專節寫“學習現代舞蹈的開端”。文中寫道:“(1935年9月)我在上海舉行了第一次舞蹈作品發表會后,感到自己從事舞蹈事業除少數知己外,當時上海的觀眾對我十分不了解。怎么辦?我應怎樣為自己辯護呢?最好的辦法就是必須創作出好的、能鼓動人心、又能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為大多數人說話的節目。在第一次作品發表會上,觀眾喜歡的舞蹈只有兩個:一個是根據《送葬曲》編制的反映葬禮上的舞蹈《送葬》,另一個是根據肖邦《夜曲》編制的《黃浦江邊》。這兩個舞蹈作品正好能結合上海當時社會上的一種苦難氣氛,因而受到了群眾的注意。”曉邦先生又說:“當時《送葬》和《黃浦江邊》之所以比較能吸引人,主要是表現了對窮苦人的同情。《傀儡》這一個諷刺性的節目,由于影射了滿洲國的傀儡,所以也得到了歡迎。這是我在學習期間,第一次把外國舞蹈形式引進中國來的最初嘗試。”可以看到,曉邦先生從“作品發表”伊始,就自省出未來創作的取向——鼓動(大多數人的)人心、代表大多數人的利益和為大多數人說話。而《送葬》和《黃浦江邊》的相對成功,一是貼近現實的“苦難氣氛”,二是“同情窮人”的情感表現。
三、現代舞“使我的藝術思想得到解放”
曉邦先生正式接觸并大致掌握“現代舞”,是在1936年7月。他所師從的日本舞蹈家江口隆哉和宮操子,曾是曉邦先生1930年在日本學習舞蹈時的老同學。這之后,江口隆哉、宮操子赴德留學,1936年回東京開設現代舞踴研究所,傳習魏格曼的現代舞蹈。曉邦先生在《我的舞蹈藝術生涯》中回憶道:“我接觸現代舞只有短暫的3個星期,但它對我的思想卻產生了巨大的影響。它使我的藝術思想第一次得到解放,朦朦朧朧地感受到20世紀舞蹈藝術的科學方法及其發展遠景……1936年10月,我在韋布邀請下參加了東京留學生舉行的魯迅先生逝世紀念會,會后我就趕回上海去提倡現代舞蹈。”回到上海后,曉邦先生一邊傳授現代舞蹈,一邊準備自己的“第二次舞蹈作品發表會”。這次作品發表會于1937年4月發表,曉邦先生回憶道:“我由于受現代舞蹈的影響,初步嘗試創作了3個現代舞作品(即《懊惱解除》《奇夢》《拜金主義》)……我覺得現代舞在要求反映現實生活、擴大創作題材的范圍、追求表現人物的內心世界上,它敢于沖破古典芭蕾舞中那些不能適應表現現代生活的種種束縛;無論是在訓練方法上,在表現方法的靈活性和自由性上,都是具有生命力的。”
四、“與偉大時代的斗爭相融合”
1937年“8·13”后,曉邦先生像許多不甘屈服的革命文藝工作者一樣,參加了抗日救亡演劇隊的工作。這時的曉邦先生認識到:“我感覺到自己的思想感情正在與偉大時代的斗爭相融合著。我在這時的創作活動,是我從現實生活中找到的一條新的道路。它擺脫了舊舞蹈形式的束縛,表現了時代的特點;使舞蹈不再像過去那樣只為迎合有閑階層的需要,而是成了打擊敵人、鼓舞人民斗志的精神力量。這確實是我的藝術生活邁向現實主義的一個發展。”學習現代舞蹈,并非要有意識表演現代舞蹈。那一時期,曉邦先生主要結合群眾歌曲來編排舞蹈,主要有《大刀進行曲》《流亡三部曲》《游擊隊員之歌》等。曉邦先生說:“歌曲感動著我,我的舞蹈又鼓動了觀眾。我為這些節目設計的動作和姿態,完全出自對當時生活環境的感受……只有一種思想在支配著我,那就是要用我的舞蹈去為中國民族求生存效力……我將國外現代舞蹈的表現技法與中國的現實生活相結合,因而才能在舞臺上出現從來未有的舞蹈作品。我是在時代的脈搏上舞蹈的!抗日戰爭的生活給了我甘露與營養,將我造就成‘為人民而舞蹈’的一員。”
五、“對開展新舞蹈運動更加充滿信心”
1939年初,曉邦先生還是在上海舉辦了他的“第三次舞蹈作品發表會”,發表了《丑表功》《傳遞情報者》和《徘徊》3個新作。這其中《丑表功》特別受觀眾歡迎。曉邦先生說:“《丑表功》創作的動機,是汪精衛在河內發表了向日本帝國主義獻媚取寵的電文,他變成了日本帝國主義豢養的走狗,我要淋漓盡致地揭露鞭撻這個漢奸。所以,在人物的設計上,我運用了面具人物的表現方法……服裝的涉及則選用了戲曲里丑官式樣的袍子,在胸口上畫一個太極圖,腳上穿雙一紅一綠的鞋……在動作上,我極力把這個丑官塑成一個善于吹牛拍馬之能事的形象,他無時不在賣弄著欺壓百姓、糾集狐群狗黨的丑惡伎倆……受到主子賞識時,就得意忘形地自以為不可一世,而最后只落得個喪家犬命運的可恥下場。”也就是說,這時的曉邦先生要讓現代舞在宣傳抗日救亡的活動中發揮作用,要運用現代舞的表現手法、從生活出發去宣傳抗日,用曉邦先生自己的話來說:“踏上抗日征途后,我的舞蹈更是受到了群眾的歡迎,使我對開展新舞蹈運動更加充滿信心。”
六、真正確立“新舞蹈”的藝術理念
好了,我們不要這樣一段一段敘述曉邦先生如何去了革命圣地延安,又如何輾轉到東北解放區……當他為東北民主聯政宣傳隊創排《進軍曲》之時,他已經真正確立了自己的“新舞蹈”藝術理念。曉邦先生說:“解放后不久,有一位領導同志問過我,為什么叫‘新舞蹈藝術’?……我認為,所謂‘新’,就是因為它是從反封建、反壓迫、反剝削的藝術活動中脫胎出來的,是通過一些舞蹈家們反抗舊社會、舊意識的革命意識實踐中成長起來的……延安秧歌舞蹈運動中,不是也有‘新秧歌舞蹈’嗎?‘新’是意味著與‘舊’的區別,與‘舊’的決裂。”1956年,黨在科學和文藝方面提出了“雙百”方針,曉邦先生提出創辦“天馬舞蹈藝術工作室”的請求得到了周恩來的同意。曉邦先生說:“我的作品都是在人民生活的哺育下創作出來的,如《義勇軍進行曲》、《游擊隊員之歌》、《饑火》、《思凡》等。這些作品已形成了我舞蹈創作上的獨特風格。在教學中,多年來也積累了一套舞蹈訓練的科學方法——自然法則運動和同時發展舞蹈學生創造性的教學法……我的創作風格和教學法將作為我創建‘天馬’的前提和特點。”此外,曉邦先生還認為新中國建國以來的幾年間接觸了許多中國古典音樂,這些“清雅、典美的古曲”,向曉邦先生“展示了舞蹈上的新意象”,使曉邦先生產生了“賦之以舞蹈生命的愿望”。于是,曉邦先生陸續創編了雙人舞《平沙落雁》(古琴曲)、獨舞《陽春白雪》(琵琶曲)、獨舞《北國風光》(南曲)、以及《十面埋伏》(琵琶曲)、《春江花月夜》(琵琶曲)、《梅花三弄》(古琴曲)、《梅花操》(南曲)等等。
七、借古曲展示舞蹈的“新意象”和“新生命”
主張與“舊”的區別、與“舊”的決裂并倡導“新舞蹈”的曉邦先生,為何此時沉迷于“古曲”的清雅、典美呢?許多人往往從當時的政治生態來暗示曉邦先生的無奈,但我卻從作品的藝術象征看到了曉邦先生“反抗舊意識”的“新舞蹈”——這便是借“古曲”的清新、典美,展示舞蹈的“新意象”和“新生命”:比如《平沙落雁》,曉邦先生說:“我在這首樂曲里似乎看到了那南歸的雁,歷盡千辛萬苦,而一旦迫落在平沙之上的哀婉、凄慘的情景。于是我編這舞時即從落雁開始。描寫一對掉離雁群的大雁,落在沙灘上。他們飲水、休息找尋事物、相依為命,隨時警惕著敵人的襲擊……直到天空開始發白,它們才找到自己的隊伍,飛到遙遠的南方去。”(第136頁)又比如《梅花三弄》,曉邦先生說是他“1959年的一個重點創作節目”。這個節目“描寫了在遙遠的古代,某個客店里曾有一位名叫梅花的侍女,生前對旅客十分溫柔、體貼,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某晚,一位窮書生來店里投宿,在秉燭夜讀時,數次受到梅花陰魂多情溫存的關懷……他開始詫異不解,是何人給以他善良的幫助?后來終于發現是隱藏在繪有梅花的屏風后一位美麗少女的陰魂……”聯想到曉邦先生當時的境遇,這些古曲的新意象、新生命的確有借古喻今、托物言情、藉死勸生的意味!這是曉邦先生“新舞蹈”創作的一次重大、也是終結的轉型!
八、為什么要學習現代舞蹈基本技術
為著培養更多的從事“新舞蹈”的“新舞者”,曉邦先生將自己多年來積累的舞蹈訓練的科學方法結集出版,這便是最早由上海三聯書店在1950年出版的《新舞蹈藝術概論》。它的核心內容便是曉邦先生前述“自然法則運動和同時發展舞蹈學生創造的教學法”。筆者最初的讀本,是曉邦先生多次修訂后由中國戲劇出版社1982年11月出版的。在該書的第七章《現代舞蹈的基本技術和理論》中,曉邦先生寫了一節“為什么要學習現代舞蹈的基本技術”。他說:“過去學習舞蹈,一般都是由老師一套套傳授下來,如大家常說的‘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因此會留有老師的許多痕跡。現在舞蹈的科學法則的基本訓練,不強調‘領進門’,而是老師舉著手中的鑰匙,向大家指出舞蹈之門的位置,然后把這把鑰匙交給學生,讓他自己去打開舞蹈之門,去發現舞蹈藝術中的秘密。這種基本技術既有助于我們進行舞蹈的學科研究,也可以把它作為我們反映現實生活的創作手段。”也就是說,曉邦先生把現代舞蹈的基本技術當做打開舞蹈之門的鑰匙;我們的打開“舞蹈之門”,意味著創作“用現代人的動作和表情去反映現實生活的舞蹈”。
九、注意“創作實習課”十大毛病
曉邦先生寫作《新舞蹈藝術概論》,最重要的意圖就是教會舞者去創造“新舞蹈”。曉邦先生在“緒論”中就談到了“組織創作”的問題。他指出:“第一,我們要使大家正確認識生活和舞蹈的關系,只有生活才是舞蹈藝術創作的源泉……只有跨進生活的大門,面向生活、捕捉情感和集中情感,我們的情感、想象就會從生活中激發出來。第二,舞蹈創作的組織者必須解除大家學習舞蹈技術上所帶來的限制,同時要克服照搬基訓課上的條條框框,要放開思想,把動作的思路有條不紊地組織起來,使其適合塑造舞蹈形象的需要……如果不是這樣,我們的舞蹈就不能讓大家看懂,看不到人物動的主題、主題發展及主題的重復和變化的關系……”該書中與舞蹈創作直接相關的有兩章,即第六章《論發展舞蹈的創造性》和第八章《組織舞蹈創作實習課的經驗》。在第八章他特別要求創作者注意“創作實習中的十大毛病”,即:1.表演雜亂瑣碎。不會捕捉情感、凝聚情感和概括情感,容易陷入雜亂瑣碎的表演中去。2.動作空洞無物。動作不統一且無目的性,容易搬弄步法和技術,因忽略應具有的情感、想象過程而成為空洞無物的“舞蹈八股”。3.主題不突出。不懂得舞蹈的表情必須圍繞人物和主題來表演,不懂得人體運動中色、線、形必須表現作品的主題。4.不肯割愛。不會集中,喧賓奪主,動作設計缺乏邏輯性,形成堆砌。5.忽略主題的變化和發展。陷入多余的對稱動作和不必要的雷同動作,毫無生動感。6.動作上風格特色模糊。原因一是缺少民族精神生活上大眾的因素,即形式上特有的舞蹈用語;二是缺少現實生活規律的因素,即“動”的一般用語。要使二者結合起來去形成鮮明的風格。7.缺乏節奏上的各種對比。8.情緒組織的濫用。9.思想傾向過于自我。10.藝術性和思想性不統一。最后兩點已經不只是藝術觀更是人生觀方面的問題了。
十、要尊重中國傳統的藝術習慣
進入改革開放的新時期以來,曉邦先生以領導者的身份帶領中國舞蹈界開始了思想解放的“破冰”之旅。1980年第一屆全國舞蹈比賽之后,曉邦先生經過深思熟慮,發表了《新情況,新問題——兼論現代舞對中國新舞蹈藝術的影響》(載《舞蹈》1982年第1期)。他說:“對待現代舞的態度,我同意有的同志所做的比喻:聰明的人重視現代舞,驕傲的人輕視現代舞,愚蠢的人照搬現代舞……站在建設中國新舞蹈藝術視野的立場上去借鑒外來的舞蹈藝術,照搬和輕視都是不對的。作為中國的新舞蹈藝術,毫無疑問首先就要有中國的氣派和中國的民族特征,表現出中國人民的美學思想和審美要求。因此在創作問題上,既要打破保守思想,亦要尊重中國傳統的藝術習慣——中國傳統的藝術習慣就是‘形神兼備’……這是一條普遍的法則,也是我們的舞蹈思想與美國現代舞中新的流派的區別。中國的新舞蹈藝術從30年代開始,就遵循著我國現實主義傳統的藝術習慣;因此盡管借鑒和運用了美國前期現代舞的許多表現手法,但仍然是在中國傳統的反映論這一基礎上加以吸收,因此也摸索、創造出具有中國氣派的新舞蹈藝術風格……”
十一、現實主義:是手法問題也是方向問題
對于中國現代舞或者如曉邦先生所說“新舞蹈”,先生在1987、1988兩年間密集發表了自己的主張。筆者1985年9月至1988年7月,在曉邦先生指導下攻讀“舞蹈歷史與理論”的碩士學位,成為曉邦先生的“關門弟子”,對曉邦先生諸多教誨刻骨銘心。曉邦先生在《現實主義與新舞蹈道路》(載《舞蹈》1988年第4期)一文中說:“在現實主義舞蹈創作中,手法問題實際上也是個方向問題。有些舞蹈的題材也是現實生活的,而且作者在創作過程中思考得也很深,但在作品上臺后卻陷入了形式主義的泥坑難以自拔。作品要表現的主題很深,可是觀眾看不懂;這里恐怕不是觀眾的水平問題,而是我們的作者在主題上能‘深入’,在形式上卻‘淺出’不了……我認為這個問題的解決一方面固然要靠藝術家提高自己的文化修養,豐富自己的藝術語匯;另一方面則要教育他們更牢固地樹立藝術為人民大眾服務的觀念……”
十二、個性的創造與具有普遍意義的理性認識
我們知道,自新時期以來,曉邦先生以“伏櫪老驥”(先生生于1906年,生肖屬馬)的意志,繼續著當年“天馬行空”的精神,不斷通過寫作、講學來播撒中國現代舞——“新舞蹈”的精神良種。在我的印象中,自1979年至1988年的10年間,曉邦先生公開發表和內部結集的文章總該有百余篇之多。先生在《舞蹈》雜志最后發表的文章,題為《個性、邏輯、格調——獻給中國現代舞蹈家們》(載《舞蹈》1988年第12期)。他以“獻”的態度勸諭我們的現代舞者:“舞蹈創作需要突出人物形象的個性,同時又要通過個性的創造達到具有普遍意義的理性認識……每個形象都應是獨特的、個性化的。但如果這個個性化的形象缺少普遍的可理解性,觀眾看不懂,不能與之產生共鳴,這形象的意義又何在呢?……動作造型作為創造舞蹈形象最基本的手段,它應是溝通作者與觀眾的橋梁。只有當它傳達的意義、情感是作者和觀眾皆能共同理解時,形象對觀眾才是清晰的、有魅力的。”我們注意到,曉邦先生無論講“現實主義”還是講“個性、邏輯、格調”,都一再強調不能讓“觀眾看不懂”。這說明,“觀眾看不懂”的確是許多“現代舞”作品面對接受者時呈現的狀態,以至于有人甚至誤以為“看不懂”是“現代舞”的特質,“看得懂”的反倒不是現代舞了!
十三、吳曉邦現實主義舞蹈最基本的規定
我的同門師友張華在曉邦先生擱筆(1989年)后,寫了一篇極為客觀、準確地評價曉邦先生的文章,題為《中國現代舞先驅之路——現實主義舞蹈論》(載《舞蹈》1989年第10期)。張華寫道:“……近十年的奮斗,近十年的探索,中國現代舞已成一股不容忽視的浪潮,在日益開放日益廣泛的信息交往中,已變得復雜起來。歧途足以亡羊,千年古訓,不知是否確然?總之,眾說紛紜下,的確有了憂心、焦慮的人。中國現代舞蹈藝術的拓荒者吳曉邦,同時也是中國現代舞最早的踐行者,以他皤然白發下的權威、經驗和思索,孕育了他的那份憂心與焦慮。他似乎是從作品表達得明晰不明晰、觀眾看不看得懂這樣一些藝術上最淺近、卻又是中國現代舞最壓頭的問題發出疑問的……”為什么“看不看得懂”會成為中國現代舞“最壓頭的問題”,說明舞者的表達與觀眾的接受之間出現了“短路”,甚至說明舞者在無的放矢、在無病呻吟、在故作高深、在故弄玄虛……那么,怎么解決這個“最壓頭的問題”呢?張華指出:“從反復的藝術實踐中,吳曉邦現實主義新舞蹈的方法逐步豐滿起來,形成了一系列自己獨到的規定。既然要為人生而舞蹈,為人民而舞蹈,自然而然,內容決定形式,作品服從觀眾,這兩條規定就成了吳曉邦現實主義舞蹈最基本的規定……”
十四、中國現代舞嚴肅而堅實的起點
關于這一點,不僅置身“現代舞”圈中并且至少堪稱“大姐大”的王玫悟覺得十分到位。她在《編舞的價值不只是“編舞”——由吳曉邦的一堂編導課引發的聯想》(載《舞蹈》2007年第10期)中說:“什么是編導課,當時的我們完全不懂。吳曉邦老師的課也基本聽不懂。表面上是聽不懂他的南方話,實際上是聽不懂那些涉及編舞的文化和精神層面的話題……今天想來,以當年的自己,聽不懂吳曉邦老師當年上課的內容毫不奇怪,但是,吳曉邦老師提供給自己的編舞機會卻結結實實地改變了自己。這個改變包括生活方式,更包括由生活方式而引發的思想方式的改變……”自去廣東舞蹈學校實驗現代舞班學習3年后,王玫似乎接通了曉邦先生當年“涉及編舞的文化和精神層面”的話題。王玫認識到:“回想當年,自己這個不是編導專業的學生能夠學習編舞,原因就在于吳曉邦老師早早于我們今天而看到了現代舞之于整體舞蹈教育的意義。如今社會的人文環境和當年吳曉邦老師的不可同日而語,可我們遠遠不及當年吳曉邦老師對現代舞的認識,對編舞的認識,以及對舞蹈教育的認識……現在才明白,吳曉邦老師一貫提倡的服務社會、貼近生活、個人編創的藝術方向,實際上就是開啟舞蹈人心智的一種最高級別的技術技法……”讀到這兒,我們對曉邦先生作為“中國現代舞第一人”或“中國現代舞先驅者”還會心存疑慮嗎?還是我的學友張華說得好:“吳曉邦的歷史功績,在于他第一個真正使中國有了現代舞蹈藝術,更在于他開拓了現實主義舞蹈的道路,使中國現代舞蹈藝術一開始就有了一個嚴肅而堅實的起點。也許他的作品還太過于質實,太過于樸素,然而,他開拓的道路,必定會隨著我們事業的發展,愈來愈顯示出可貴的意義和強大的力量。這個價值必定要比他的具體作品更巨大得多!”我真誠地、由衷地為王玫的悟覺點贊!也同樣為張華的洞悉點贊!更為曉邦先生開拓的現實主義舞蹈道路的恒遠價值點贊!
于 平:文化部文化科技司司長
責任編輯:楊明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