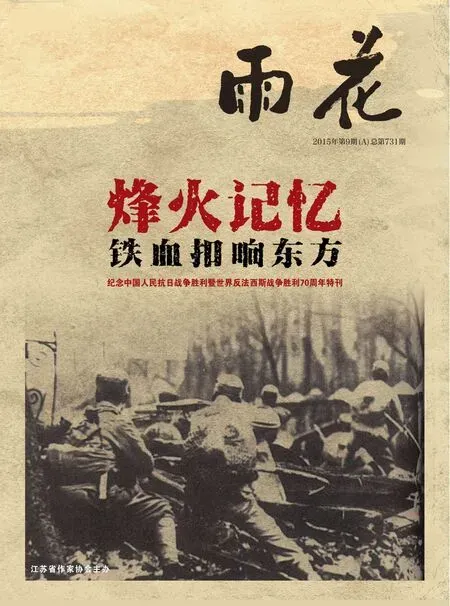抗戰歲月(組詩)
◎ 石 英
抗戰歲月(組詩)
◎ 石 英
延安
寶塔山登高一望:好大雪!
覆蓋了西安、北平、南京、重慶
但當暖陽在楊家嶺東山升起
雪融后清晰地分出紅綠灰黃
穿草鞋的人轉了大半個中國
終于在中國貧瘠的一方土地落腳
選擇是由于天時、地利、人和
人據地而起,地因人生輝
窯洞窗前移動著一支毛筆
促成中國現實與未來的精彩對話
炊事班屋頂上的炊煙裊裊
與新華廣播電臺的天線并立十三年
延河水蒸熟的陜北小米
把革命養足了,然后東渡黃河
去收獲最具歷史意義的年份
船工解開白頭巾,張揚成鼓蕩的風帆
首戰平型關
東渡黃河
向同胞和敵人亮相
憤怒的黃河在血管里流淌
中國的土地不是無人之境
這是個緊張而嚴酷的時刻
設伏的指戰員將時間咬在牙縫
使勝利消息暫時埋藏
那些嗜血成性的東洋鬼子
正得意地拭著指揮刀的血溝
驕橫堵塞了他們的耳朵
哪里聽得見就在百里開外
那代表四億五千萬同胞的心聲
正從十五歲的小號手胸中呼出!
就在這沖鋒號聲中
灰色的山洪壓向敵群
何止是設伏等待了一天
而是壓抑了近百年
沖鋒的戰士也許沒有想到
此時注視他們的有鄧世昌
還有佟麟閣和趙登禹
看他們將百年的恥辱
第一次痛快淋漓地
洗雪和傾瀉
以意志對武士道
以正氣對邪惡
以血刃對血刃
以火舌對火舌
以迸濺的血花
燒毀了淚水浸泡的歲月
在中國晉東北的山溝里
“皇軍”軍旗在余燼中蜷縮
從此,東山上
升起的還是中國的太陽!
臺兒莊街樹上的彈孔
斑斑駁駁的彈孔
與太陽對視了七十多年
子彈頭至今沒有摳出
槐樹枝葉卻比那時更繁茂
彈孔雖小 裝得下
七十多年難忘的歷史
不知在陰雨天里 曾受過傷的
槐樹會不會感到隱痛?
這彈孔舉目千里
遠望著南京大屠殺紀念地
既然那邊秀英大媽死不瞑目
這邊的彈孔就將永遠睜大眼睛
淞滬抗戰
“冒險家的樂園”,十里洋場
一變而為中國最火熾的戰場
靡靡之音 燈影下神女的血紅小口
轉換為噴吐的火舌,冒煙的槍口
整條長江都煮沸了
整個中國都投入了
東方世界都震顫了
西方世界都驚呼了
火線上不僅有將軍和士兵
還有作家、藝術家和演員
宋慶齡、何香凝也到前沿慰問
“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
“四行倉庫”生命堡壘不可逾越
以血肉為“東亞病夫”“一盤散沙”昭雪
此時延安也不遙遠,飛兵長城關埡
八路軍、新四軍揪住了新倭寇的尾巴
雖然,烈火耗干了江水
外灘的海關大鐘黯然止步
時光隨夏天的轉換而冷卻
數十萬“國軍”在秋涼中轉移……
淞滬的每一天凝成結論的每個字——
抗戰不能速勝,中國絕不會亡
愛國者的意志在戰火中鍛得更強
叛賣者決意將最后的良知喂給虎狼
刪不去的“狼牙山五壯士”
那一躍而下的悲壯身影
永遠也不會從我心目中刪去
軀體躍進深山谷底
整個民氣卻隨之升華
空谷回音:人死了,中國不死
槍折了,氣節不折!
五個人對五萬萬人是最小數
五萬萬有了五個才是真正的大數
假如沒有寧死不屈的烈士
我們看到的將全是群體就戮的慘象
同是死字,有的死得憋氣
有的死得連后人也揚眉吐氣
有一句民間俗語由此延伸
人活一口氣;那死呢?……
今年五月我專程去狼牙山
夕暉如山坡上的野花一般清寂
一個放羊娃由山上下來 揮鞭驅羊
想必是勿使它們傷食野花,不忍
那一躍而下的悲壯身影
永遠也不會從我們心目中抹去!
仰視楊靖宇烈士雕像
他是最孤單的人 當時
仗打得只剩下一人一槍
只有白雪和紅松相伴
但這只是時空的錯覺 其實
東三省三千萬同胞 還有
全中國四億五千萬同胞 都和他
在一起 只不過在此時此地
他作為他們意志的代表 一個人
寧愿將漫天風雪披在身上 一個人
將白山黑水的苦難嚼在口里
他是二十世紀四十年代初最富有的人
——擁有一切不屈人民的心聲!
他是最饑餓的人 當時
草根和樹皮都已吃光 肚里
只有棉襖里的爛棉絮 逼迫他
創造出超極限紀錄的是萬惡的敵人
他們將全東北的大豆高粱都搜刮
到日本
去加速法西斯軍事機器的運轉
他是用一個人的絕對饑餓
以減輕相識和不相識的戰友饑餓之痛
更是為了將來永遠不再饑餓
他只有普通男人的身高 如果
他走在哈爾濱或沈陽的鬧市里
除了敵人的密探 一般人不會認出——
他就是日寇懸賞抓捕的楊司令
可是,他身軀的光影直薄云霄
連星月都會因之而增輝 雖然
真正的共產黨員不會自我擴張 更不會
為自己打造虛飾的光環 但正義
與真理的光輝本來就是孿生兄弟
往往會對歷史進行隆重的追認
也許當事人聞不到鮮花的香味
但人間正氣最喜與他合影 這時
誰又能測量出他的真正身高?
仰視楊靖宇的塑像 我看見
四面八方的新鮮空氣都向他涌來!
重讀趙一曼示兒信
明知已到了最后時刻
僅有的時間應以秒來計算
沒有什么放不下的心事
只要求留下一封家信
這是特殊的母愛表達方式
對兒子一次性的終生關懷
筆體從容不迫,足見當事人
彼時的神情像出遠門那么平靜
是在雪天里寫的這信
雪封的大地就是整張信紙
信剛寫罷,敵寇的槍聲就響了
雪上的血滴凝成一行行文字
任狂風勁吹也揭不走
揭不走那對后世的警示和期待
幾經輾轉,到開春時節
這封信所幸終于到達
不只是烈士的遺孤
許許多多的有心人都讀了
他們每個人傾灑的眼淚
都綻成了三月桃花
整個雪地濃縮成的信紙
點點血滴凝成的文字
至今讀起來 字字句句
仿佛還透著當年的槍聲
遠征軍——出擊
一條公路
挾風帶雨
跨越過瀾滄江、怒江
密藏龍的不屈傳統的精髓
去尋找通向勝利的出路
與世界反法西斯末梢神經接軌
云南不甘做避難所
更是前進基地
向外出擊
只要有敵人的地方
勇士的刺刀就要見血
悄然出動的行軍隊伍
將夕陽一分為二
一半在緬甸密支那
一半在中國騰沖
再向前
在熱帶叢林里
牛虻和毒蟲
與日寇機槍子彈合流
噬吸遠征軍的鮮血
戴安瀾
還有多少有名和無名者
沒有回來
鮮血滋養著烈日灼干的生命之路
公路至今還在運行
卻很少有人熟悉它的經歷
我總覺得這條不平常的路
曾是一只巨大的手臂
托舉著南天一角
大震未傾
至今車行云起處
壯烈之氣沖騰
(作者原系八路軍膠東軍區機要科譯電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