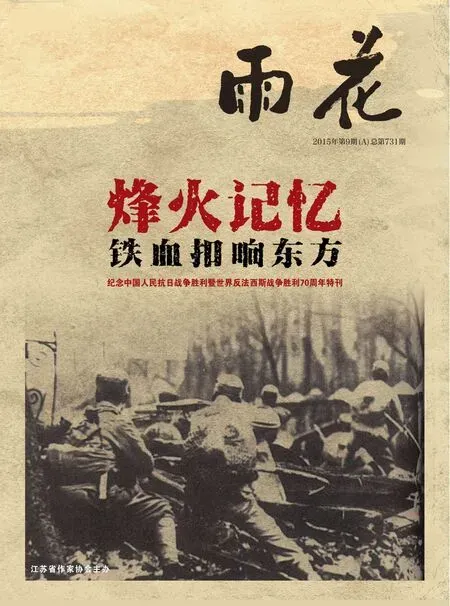神頭嶺伏擊戰(zhàn)
◎ 向守志
神頭嶺伏擊戰(zhàn)
◎ 向守志
彈指間,歲月匆匆,中國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戰(zhàn)爭勝利已70年了。我也由當年生龍活虎的青年變成了耄耋老人。回首八年的浴血抗戰(zhàn),中國人民以鋼鐵般的意志,以一往無前、視死如歸的精神,以血肉之軀前仆后繼,同武器裝備、作戰(zhàn)素養(yǎng)高于我軍數(shù)倍的日軍進行殊死搏斗,直至最后取得勝利,挽救了中華民族的危亡。尤其是在中國共產(chǎn)黨領導下的八路軍、新四軍和抗日游擊隊在裝備簡陋的情況下,以游擊戰(zhàn)術,在敵后不斷地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贏得了不少典型的戰(zhàn)役,也創(chuàng)造了不少的適合于當時的新戰(zhàn)法,發(fā)生在山西的神頭嶺伏擊戰(zhàn),就是著名的戰(zhàn)役之一。我也參加了這次著名的伏擊戰(zhàn)。
神頭嶺位于山西的黎城、潞城之間,是一座長不過幾里,寬度在一二百米之間的光禿禿的山梁,不適合于伏擊戰(zhàn)。八路軍129師386旅在陳賡旅長的指揮下,在這不宜于開展伏擊戰(zhàn)的地方,以出其不意的膽略,以狹路相逢勇者勝的氣概創(chuàng)造了八路軍抗戰(zhàn)史上打伏擊戰(zhàn)的一個“神話”。
八路軍129師是在1937年8月由中國工農(nóng)紅軍第四方面軍第4、第31軍,西北紅軍第29、第30軍和獨立第1至第4團以及第15軍團的騎兵團等改編的,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任副師長,倪志亮任參謀長,張浩任政訓處主任,宋任窮任副主任,下轄第385旅、386旅。第385旅下轄第769、第770團,旅長是王宏坤、副旅長王維舟,第386旅下轄第771、第772團,旅長是陳賡,副旅長是陳再道。我當時20歲,剛從慶陽步兵學校畢業(yè),被分配到第386旅771團任機槍連副連長。我清楚地記得129師是9月6日,在陜西省三原縣石橋鎮(zhèn)附近的廣場上,在大雨中舉行抗日誓師大會,到9月底,第129師386旅的771、772團和385旅的769團以及師直屬騎兵營、干部營在劉伯承師長、張浩主任的率領下奉命從陜西省三原線出發(fā),經(jīng)富平、韓城東渡黃河,進入山西省晉東南侯馬地區(qū),包括山西省正太鐵路以南、同蒲鐵路以東、平漢鐵路以西、黃河以北的廣大地區(qū),深入敵后開展游擊戰(zhàn)。
第一次與日軍交戰(zhàn)不是伏擊戰(zhàn)而是阻擊戰(zhàn)、襲擾戰(zhàn)。我129師在1937年10月進入了太行山地區(qū),第771團根據(jù)上級的命令就在井陘以南的七亙村阻擊從井陘出發(fā)進犯太原的一個旅團的日軍,我所在的1營在一個稱之為老爺廟的后山上設防。戰(zhàn)斗一打響,一個3000多人的日軍聯(lián)隊在強大炮火下向我團陣地發(fā)起猛攻,這是我第一次與鬼子作戰(zhàn),也是129師首次與日軍作戰(zhàn),互相不知道對方的作戰(zhàn)特點,戰(zhàn)斗非常激烈,彈片橫飛。激戰(zhàn)至黃昏,日軍在步炮協(xié)同下連續(xù)多次向我們陣地發(fā)起進攻,我和戰(zhàn)友們抱起機槍向日軍猛掃,3連戰(zhàn)士在副營長徐其海的帶領下,上刺刀發(fā)起反沖鋒,把攻上的日軍壓了下去。在夜幕降臨之際,我團完成阻擊任務之后撤出陣地。此戰(zhàn),我部斃傷日軍70余人,但也付出傷亡30余人的代價。入夜,天漆黑,伸手不見五指。團首長命令我?guī)ьI第1連到敵人設防的側魚鎮(zhèn)、老爺廟一線進行夜間襲擾。我們摸到日軍陣地前,連續(xù)打槍、投彈,聲勢較大,日軍以為我主力部隊發(fā)動進攻,連忙開炮還擊,一夜不得安寧。狡猾的日軍在我們完成任務回到駐地休息時也給我們來了一次偷襲。我在睡夢中,突然聽到槍響,一骨碌從土炕上站起來,迅速穿好軍裝,抓起手槍,帶領戰(zhàn)士們集合,在警戒部隊掩護下,我們按預定方案有秩序地轉(zhuǎn)移到集合地點。
首次與日軍交戰(zhàn)前,我們不知道日軍的強點和弱點在哪里,經(jīng)過這一交戰(zhàn),我們認識到日軍與國民黨軍隊確實不同,尤其是經(jīng)過長期戰(zhàn)爭準備的頭幾批“老鬼子”,作戰(zhàn)素養(yǎng)較高,步炮協(xié)同好,輕重機槍也比國民黨軍隊多,他們的“小鋼炮”,那時我們還不知道它叫擲彈筒,打得準,近距離有較大的殺傷力。由于日軍受到“武士道”精神灌輸,作戰(zhàn)時,只許進,不準退,嗷嗷叫著往前沖,敢于拼刺刀,還擅長夜戰(zhàn)。因此,初次交戰(zhàn)時,我們還是沿用打國民黨軍隊的戰(zhàn)法,習慣于把敵人放近了再打,試圖一個沖鋒就把敵人壓下去消滅掉。事實不是這樣,這讓我們付出了血的代價。但是,這些鮮血換來的經(jīng)驗教訓在我們后來作戰(zhàn)中發(fā)揮了很大作用。
在夜擾戰(zhàn)之后,我已經(jīng)由1營調(diào)到2營任機槍連連長。在劉伯承師長的指揮下,第129師游擊戰(zhàn)術已運用得出神入化。同年11月,在不到一個星期時間內(nèi),我們先后在黃崖底、廣陽、戶封地區(qū)連續(xù)設伏給日軍以沉重的打擊。劉伯承師長把這三次伏擊戰(zhàn)稱為“重疊的設伏”。在11月末,我771團2營,面對來犯的600多名日軍,把1個連分成若干個戰(zhàn)斗小組,埋伏在日軍前進道路左側的山坡上以及村莊里,從各個側面伏擊日軍,日軍傷亡100余人后不得不撤退,而我部無一傷亡。劉伯承師長把這一戰(zhàn)法形象地比喻為“麻雀戰(zhàn)”。“麻雀戰(zhàn)”這一軍事用語就此誕生了。
到了1938年2月中旬,侵華日軍為配合其津浦線作戰(zhàn),集合3萬余人向晉南、晉西發(fā)動進攻。由于邯(鄲)長(治)公路是晉西南日軍從平漢線取得補給的主要交通線,3月上旬,第129師奉命集結在邯長公路以北的襄垣、武鄉(xiāng)地區(qū),尋機殲敵,破壞交通線。日軍深感邯長公路的重要性,日軍108師團步兵及騎兵1000余人駐守沿途各縣的據(jù)點里,其中黎城與潞城是兩個可以相呼應的最重要的據(jù)點。由于距潞城縣東北的神頭嶺一帶地形復雜,便于設伏,劉伯承師長、鄧小平政委、徐向前副師長當即決定運用“攻其所必救,殲其救者”的兵法戰(zhàn)策,擬定了“吸打敵援”的作戰(zhàn)方案,即先以一部兵力襲擊日軍占領的重鎮(zhèn)黎城,吸引潞城之敵來援,而后以主力在神頭村附近地域組織伏擊,殲滅增援日軍。
在我們制訂“吸打敵援”作戰(zhàn)計劃之前,即在同年的2月,劉伯承師長就采用攻點打援的戰(zhàn)法在井陘與舊關之間的長生口設伏,打擊從井陘援救舊關的日軍。
水無常形,兵無常勢。日軍絕對沒有想到,我129師再次使用圍城打援之計,在神頭嶺設伏。根據(jù)擬定的“吸打敵援”的作戰(zhàn)方案,以769團為左翼,派一支小部隊襲擊黎城,該團主力部隊則伏擊涉縣可能來援之敵;第386的771團、772團以及補充團為右翼,由旅長陳賡、政委王新亭指揮,在神頭村附近設伏,殲滅潞城增援之敵。
在386旅召開的戰(zhàn)前第一次準備會議上,旅長陳賡和政委王新亭介紹了劉伯承、鄧小平等師首長的戰(zhàn)略意圖,請三個團的指揮員就選擇伏擊場地問題發(fā)表意見。團首長的眼睛都盯在國民黨軍隊遺留下來的一張舊軍用地圖上。地圖上顯示神頭嶺有一條深溝,公路恰從溝底穿過,路兩旁山勢陡險,便于部隊隱蔽也易于出擊,是個理想的伏擊地。大家一致推薦在神頭嶺設伏。此刻,心思縝密的陳賡旅長發(fā)現(xiàn)大家都沒有去過神頭嶺對地形地貌進行實地考察,事前的一切都是紙上談兵。于是,立即帶領團首長實地勘察。到神頭嶺后,他們大吃一驚:公路不在山溝里,而是在一道有幾公里長的光禿禿的山梁上,兩邊的地勢略高于公路,除了距路邊20米至100米范圍內(nèi)有一些國民黨軍隊修筑的舊工事外,這里再也沒有任何隱蔽物。顯然,這樣的地形不適宜伏擊,然而除此點以外,附近再也沒有合適的伏擊地點了。因此,選擇伏擊地點由信心滿滿陷入了進退兩難的境地。
觀察地形很久的陳旅長也注意到大家臉色凝重,詼諧地說:“回去討論好啦,地形是死的,人是活的,想吃肉,還怕找不到個殺豬的地方嗎?”
討論會上,陳旅長在聽完大家的發(fā)言后,用洪亮而又堅定的聲音說:“我看,這一仗還是應該在神頭嶺打好。”
大家一臉詫異。他具體分析說:“一般地講,神頭嶺打伏擊的確是不太理想。但是,現(xiàn)在這種不理想?yún)s正是我們出其不意地打擊敵人的好地方。正因為地形不險要,敵人必然會麻痹大意,放松警惕。而且那些原有的工事離公路最遠的不過百十來米,最近的只有20來米,敵人早已司空見慣。如果我們把部隊隱蔽到工事里,隱蔽到敵人鼻子底下,切實偽裝好,敵人是很難發(fā)覺的。山梁狹窄,兵力確實不易展開,但我們是先處戰(zhàn)地,可以先敵選擇有利地形,先敵展開,這樣就更可以迫敵于不利地位,把地形上的不利統(tǒng)統(tǒng)甩給敵人。”
講到這里,陳旅長問道:“獨木橋上打架,對誰有利呢?”大家一時沒反應過來。
我團徐深吉團長笑道:“我看是誰先下手誰占便宜。”
旅長接著說:“對哇,只要我們做到突然、勇猛,這種地形上的不利條件就只是對敵人不利了,而對我們則變成有利了!”
3月15日,是預定的作戰(zhàn)時間。在夜幕慢慢降臨之際,部隊經(jīng)過周密準備,深入動員,借著黃昏就隱蔽出發(fā)了。戰(zhàn)士們情緒高漲。這一時刻,我也特別興奮,預感到要打大仗了。我率領2營機槍連隨隊急速跟進。過了申家山,就接近我們的設伏地域了。回頭一看,山間小道上,在朦朧的月光中,我們的部隊猶如一條游動的長龍,悄悄地向山岡和公路兩側急進。
部隊進入設伏位置后,根據(jù)戰(zhàn)前要求,立刻進行偽裝和戰(zhàn)斗裝備。我逐一檢查戰(zhàn)士們的偽裝,輕聲叮囑:“一定不要隨便動舊工事上的土,踩倒的舊工事近處野草,也要順風向扶好,絕對不能暴露目標。”一名戰(zhàn)士很擔心地問我:“連長,你說鬼子會不會發(fā)現(xiàn)我們?”“當然不會。可是,你們不好好偽裝,暴露了目標,那就破壞了整個作戰(zhàn)計劃。”就在此刻,從東北方向傳來了一陣沉悶的轟隆聲。我一陣興奮,知道擔負“吸敵”任務的769團已經(jīng)對黎城展開攻擊。
聽著遠處的槍炮聲愈來愈密,大家的心情也越來越緊張。我督促戰(zhàn)士們加快偽裝,迅速隱蔽起來。連隊偽裝完畢,我看了看表,正好是16日4時許。
部隊靜靜地隱藏在工事里,東方的天際也慢慢出現(xiàn)了魚肚色。黎城方向的槍炮聲時不時傳來,時緊時松,時密時疏。此時,天已大亮,神頭嶺一如往常平靜,仍不見鬼子的影子,埋伏在工事里的戰(zhàn)士已經(jīng)好幾個小時,動也不敢動,心里非常焦急,擔心鬼子不上鉤。直到陳賡旅長命令部隊準備戰(zhàn)斗,說日軍已從潞城派出了1500多人增援時,戰(zhàn)士才放心。
原來,日軍正按照我們戰(zhàn)前的設想行動。黎城襲擊戰(zhàn)打響后,涉縣的日軍以數(shù)百人乘汽車來增援。剛過東陽關,就發(fā)現(xiàn)第769團設伏部隊,雙方互擊,該部日軍比較狡猾,可能意識到我軍的目的,只稍做抵抗,即向涉縣回撤。
而潞城之敵得知黎城被襲,隨即抽調(diào)步騎兵1500余人向黎城增援。8時30分,敵先頭分隊乘汽車2輛和騎兵20余人,沿公路通過我設伏地區(qū)向黎城開去,我另一伏擊部隊將該敵放過之后,把趙店木橋焚毀,截斷日軍的退路。這一舉動,并沒有引起日軍的警覺,認為這不過是游擊隊破壞交通的伎倆,不以為然,仍趾高氣揚地往前奔去。
就在陳賡旅長通知各團準備戰(zhàn)斗時,敵主力縱隊先頭部隊已經(jīng)進入了我們的視界內(nèi):走在前面的是步兵、騎兵,中間是車隊,后面又是步兵、騎兵。我遠遠望過去,日軍就像一條巨大的“黃蚯蚓”在蠕動。不久,已接近神頭村的日軍先頭部隊突然停下來,難道日軍發(fā)現(xiàn)了我們?我緊張得屏住了呼吸。時間在一分一秒地過去,仍不見日軍向前走。此時,日軍派出了一支騎兵組成的搜索隊,沿著一條羊腸小道直奔埋伏陣地,眼看著日軍在一步步地接近我們的工事,就要踩到戰(zhàn)士們的頭了。我們感覺到陣地上的空氣就要凝固一般。好在日軍在距舊工事10米左右時仍沒有察覺就在他們眼皮底下的戰(zhàn)士,正如陳賡旅長預料的一樣,日軍只注意了遠處,注意了溝對面的申家山,對于腳下那些見慣了的工事,卻根本沒有放在眼里。看到申家山?jīng)]有動靜,發(fā)出了信號,便繼續(xù)前進了。后面的大隊,隨即沿公路跟了上來。
9時30分,當日軍主力完全進入我設伏區(qū)后,陳賡旅長發(fā)出戰(zhàn)斗的信號,我各部隊按照統(tǒng)一信號,向敵突然開火,發(fā)起攻擊。第771團攔頭,第772團第3營斷尾,第772團主力和補充團從公路兩側向敵突擊,頓時將敵截為數(shù)段。我指揮機槍連開火,日軍當即倒下一片,其他連隊的戰(zhàn)士們投出的雨一般的手榴彈在日軍中炸開,山梁頓時變成了一片火海。
隨即,戰(zhàn)士們紛紛從工事里、草叢中沖出來,高喊口號,如猛虎一般沖進敵陣,用刺刀、大刀、長矛和日軍展開肉搏。激戰(zhàn)約半小時后,我預備隊第771團第2營一部投入戰(zhàn)斗。只見長長的公路上,白光閃閃,紅纓飄飄,許多日軍在我軍突然打擊之下,驚魂未定之際便被刺死。剩下的四處潰逃,企圖組織頑抗,但在這狹窄的山梁上,無地形地物可以利用,只能在公路上來回奔竄,有的滾進工事里,有的趴在死馬旁拼命射擊,也有的端著刺刀惡狠狠地向戰(zhàn)士們撲過來。
我抓住戰(zhàn)機,迅速指揮機槍向這些頑固之敵密集掃射,幾十個撲向戰(zhàn)士的鬼子立刻就被機槍送上了西天。一名日軍中尉想負隅頑抗,向奔跑的日軍只喊了一句:“大家一塊兒死的地方就在這里,干吧!”話音未落,就被一枚迫擊炮彈炸死。
戰(zhàn)斗局面完全倒向我方,中斷的日軍完全喪失了戰(zhàn)斗力,除少數(shù)逃跑外,其余的都成了刀下鬼。
在勝利在望的時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發(fā)生了。原來,一股殘存的日軍竄到東西兩頭,東部的日軍被我部隊截擊,但西頭的300多名日軍卻乘隙占領了神頭村,企圖依據(jù)房屋、窯洞固守待援,伺機接應東頭的日軍一起向潞城逃跑。如果讓日軍在村里站穩(wěn)腳跟,就等于讓敵人占領“橋頭堡”,形勢將對我們極為不利,戰(zhàn)斗局面就有可能急轉(zhuǎn)直下!
在關鍵時刻,陳賡旅長斬釘截鐵地命令:不惜一切代價,把村子拿回來!
命令一出,戰(zhàn)士猛沖上去,同日軍英勇拼殺。一名戰(zhàn)士負傷四處,用毛巾扎住傷口止血以后再戰(zhàn),一口氣刺死六個敵人,最后壯烈犧牲;還有一名戰(zhàn)士受傷以后,用毛巾勒住傷口,一口氣向敵人叢中投出了12顆手榴彈;一名司號員赤手空拳把敵人摔倒,撿起石頭,砸向鬼子,并奪回一支槍;一名炊事員用扁擔劈死一個敵人,奪來了一支三八槍;補充團中的新戰(zhàn)士,許多沒有步槍,就拿梭鏢與日軍拼殺,勇氣使日軍膽寒。戰(zhàn)斗結束后,陳賡旅長審問俘虜時,一個日本兵說:“我什么武器都不怕,就怕你們的長劍。”
到下午4時,劉伯承師長下令各參戰(zhàn)部隊撤離。我站在神頭嶺上,眼前到處是倒地的日軍和騾馬尸體,還有成捆成箱的輜重和散落一地的文件。
此役,僅有百余名日軍突圍逃回了潞城。我部以傷亡240余人的代價,共斃傷日軍1500余人,俘虜8人,繳獲各種槍支550余支,俘獲騾馬600余匹,擊毀日軍汽車百余輛。神頭嶺成為了日軍喪魂落魄的“傷心嶺”。
神頭嶺伏擊戰(zhàn)給予入侵晉東南的日軍以沉重的打擊,對牽制日軍向晉西南、晉西北進攻起到了重要作用,極大地鼓舞了太行山抗日軍民的戰(zhàn)斗士氣,也震驚了日寇侵略者,他們不得不承認戰(zhàn)斗的指揮者有“第一流戰(zhàn)術”。一名當時從神頭嶺伏擊戰(zhàn)中僥幸脫逃的日本《東奧日報》隨軍記者,回去后寫了一篇題為《脫險記》的通訊,稱神頭嶺之戰(zhàn)是八路軍129師的“典型游擊戰(zhàn)術”。
(顧茂富/記錄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