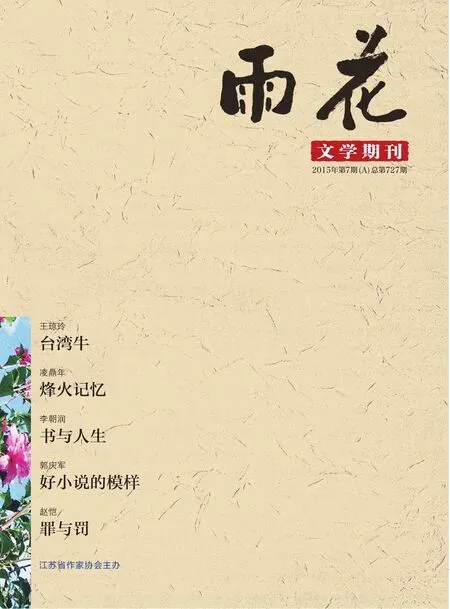和尚
■董維華
和尚
■董維華
和尚俗家名字叫明珠,是個遺腹子。
在那個兵荒馬亂的年代,朝不保夕。里下河腹地無關可守,無險可據,日本人、中央軍、新四軍、地方民團走馬燈似的,誰也留不住,成了游擊區。在一個月黑風高夜,村里好多狗在拼命地狂叫,不時傳來哭喊聲,有人來拉壯丁,他爹和幾個人一同被拉走,都不知道給誰當兵。半年后,從戰場上逃回的本村人說,這次是國民黨拉的,在鹽城卞倉與日本鬼子干了一仗,他爹被打死了。此時,他還在娘肚子里。
他出生了,依“明”字輩取名“明珠”,上面還有一個哥哥,—個姐姐,爺爺也已過世。沒有男人當家,日子過得真是艱辛,常常吃了上頓沒下頓,衣服要補了又補,被人欺負是常有的事。奶奶信佛,雖沒有文化,在家早晚念經,每逢初一和十五要到鄰村廟里去敬香,竟然還能背誦《心經》。行善的人敬香時要獻上饅頭、水果、香油、大米等物,捐的錢,稱為“功德”,饅頭水果供在佛像前,稱為“供果”。廟里的和尚見奶奶心誠,常施舍一點供果給她。她舍不得自己吃,帶回家給小孫子吃。
五歲那年,家中揭不開鍋,吃完了米面,又吃光了山芋、南瓜,已開始吃樹葉,挖野菜。明珠得了病,全身冷一陣、熱一陣,時時高燒,燒糊了,不斷在喊:“肚子餓、肚子餓,我要吃供果、供果。”看看小命要保不住了,奶奶說:“沒法子,送到廟里去試試,死馬當作活馬醫。”于是,奶奶和媽媽抱著他到觀音寺,跪在寺門口。
“做什么?”
“家里窮,沒吃的,孩子又病了,請法師行行好。”
“什么病?”
“不曉得,沒得錢請郎中。”
當家法師叫一塵,懂一點醫術,摸摸額頭,把把脈像,說:“有點像瘧疾,時間拖得太長,比較難醫。”
“阿彌陀佛、菩薩保佑。”奶奶不斷叩頭。
在再三哀求下,一塵法師收下了他,用自制的草藥喂他,幾天后,病奇跡般地好了。
次年春,一塵在寺中為明珠落發剃度。一塵法師說,名字就不用改了,法名還叫明珠。這一年為民國三十七年(1948年)。
觀音寺是個小廟。前后兩進,前面是天王殿,供著四大天王,后面是大雄寶殿,中間供著釋迦牟尼佛、大勢至佛和藥師佛,兩側是十八羅漢,背后是觀音菩薩。大殿后面是幾間寮房,西側是一個放生池和幾畝廟田,東側是一條大河,直通黃海。
觀音寺共有兩個和尚,大師傅一塵是方丈,二師傅是一凡。一塵讓明珠學文化,先從《三字經》《百家姓》《龍文鞭影》學起,慢慢地學到《論語》《中庸》。明珠偶爾開小差,師傅就用柳枝做的戒條打手掌心。
剃度之后,和尚從觀音心咒“唵嘛呢叭彌吽”開始念,學禮佛儀規,朝時課誦從楞嚴咒、大悲咒、心經、三皈依—學起,暮時課誦從阿彌陀經、懺悔文、西方發愿文等—背誦,開始讀不懂,手敲木魚,口念經文,死記硬背,真是小和尚念經、有口無心。慢慢地,他有所領悟。
和尚印象深的是十八歲那年,一塵法師帶他到鎮江定慧寺受戒。
定慧寺是千年古剎,建在長江南側的焦山上,四面環水,綠樹成蔭。一塵把明珠交給小沙彌,自己就去拜訪定慧寺的僧值,他們是同門師兄弟。定慧寺廟大,規矩更大。上百人在寮房喝粥,竟然一點聲音都沒有。晚上,三十多人睡在一個房間,每人只有一尺多寬的床板,只能側身睡,沒有一個人敢說話。走路也有規矩,一人怎么走、二人怎么走、三人怎么走?都有說法。一切是那么陌生,又是那么新鮮。二個月后,這一批受戒的一起在戒臺上剃了頭,剃得橫摸順摸都摸不出頭發茬子,要不然一燒,就會“走”了戒。用棗泥子先點在頭皮上,然后用香頭子點著。燒了戒疤就喝一碗蘑菇湯,讓它“發”,不能躺下,要不停地走動,叫做“散戒”。傍晚,在焦山上散戒時,一個一個穿了新海青,光光的頭皮上都有黑點子—要等到黑點子掉了,才會露出白白的、圓圓的戒疤。明珠遇到了一塵師傅。
“疼嗎?”
“疼……不疼。”
“燙了幾只?”
“十二只。”
“具足戒呢。”
“放戒的師傅說我嗓門響,叫我留下來。”
“留下來可以做沙彌尾的,將來可以留下來做僧值、知客、監院的。”
“還沒定呢,要等主事的和尚商議。”
“你留嗎?”
“我不留,隨師傅回觀音寺。”
回到觀音寺,當天晚上,一塵指著他房間掛的一幅字畫,上面寫著“(一個字)。”
“這是什么字?”
“不認得。”他不知是讀“來”還是讀“去”。
“你出去。”他走出去。
“進來。”他又走進來,一只腳跨進門檻。
“停,你說你是進來,還是出去?”他茫然不知,嚇得縮回腳。“啪”,一塵和尚用戒條狠狠抽在他的膀子上,疼得很。回到房間,膀子上紅了一道杠。去問二師傅,一凡也不認得。查字典,沒有這個字,真是怪了。
第二天晚上,再去師傅的房間,當他一只腳跨進門檻時,一塵問同樣問題,他想,昨天出去挨打,那我今天進去試試,猶猶豫豫地又跨進一只腳。“啪”,師傅又是一戒條,打在另一只膀子上。他回去,想了一夜,還是沒想明白。
“師傅,你說我是進來,還是出去?”第三天晚上,當一只腳跨在門檻上時,他主動問。
一塵不吱聲。
“我出去了。”不等師傅表態,他自己出去了。
“我進來了。”他豁出去了,自己走進來,坐在師傅旁邊的椅子上。
“這就對了。”一塵點點頭,接著說:“這個字是你師爺爺自創的,讀來讀去不重要,你心里想‘來’就是‘來’,心里想‘去’就是‘去’,來去皆在心間。”
和尚似有所悟。
1966年春天,一塵常常嘆氣,自言自語:要起風了。明珠不明白:外邊天好好的,怎么要起風呢?
一塵開始講《佛遺教經》,足足講了三個月。一塵說此經是佛陀一生事畢、臨入涅槃、戒勖弟子及一切眾生的遺囑,精簡扼要,字字珠璣,句句悲切,你當謹記:“常當一心,勤求出道”,如慈父訓子。
秋天到了,紅衛兵沖進觀音寺中,勒令三個和尚一起跪在地上,先宣布,宗教是精神鴉片,和尚是牛鬼蛇神,寺廟必須拆掉,和尚必須還俗。接著用繩子捆住佛像,“一、二”、“一、二”眾人打著號子,“轟”,佛像倒地,佛頭、胳膊散落一地。三個和尚痛苦地閉上眼睛,“罪過,罪過,阿彌陀佛。”
晚上,一塵在宣紙上用毛筆寫下:
我有明珠一顆,
久被塵勞關鎖,
今朝塵盡光生,
照破山河萬朵。
一塵對明珠說,這是宋朝柴陵郁法師的一首悟道偈,“明珠”就是向佛之心,“塵勞”就是人世間的各種煩惱孽障,說的是柴陵郁法師一心向佛,總勘不破,一天,他經過一個獨木橋,失足掉到山澗里,抬頭看,天空中一輪明月,頓時悟道。接著,他從墻上摘下那幅“”字。
“明珠,你還俗去吧,將來重修山門,你一定要將這兩幅字掛在寺中。”老和尚雙眼含淚。
“師傅,那您呢?”
“佛不棄我,我不棄佛。”
第二天,明珠和尚還俗了,老和尚不知所蹤,寺前的一只盛水救火用的大缸也不見。
回到村里,此時村已改稱大隊了,很少有人喊他名字,多叫他和尚。窮鄉僻壤,既沒有資本家、地主,也沒有特務,斗誰呢?斗和尚。罪名有兩:國民黨后代、和尚。先開批斗會,要他招供,怎么偷聽敵臺,怎么吃葷、殺生、嫖女人,他說:“沒有。”“不老實”,就是一巴掌,一棍子,然后是五花大綁游街,紅衛兵用繩子牽著,一群小孩跟著,大喊:
“和尚、和尚。”似乎,“和尚”是最毒惡的罵人話。
斗過一陣,也沒太多名堂了,他開始接受勞動改造,不敢再剃光頭,蓄起了頭發,不敢再穿百納衣,改穿中山裝,不敢在家中念經、打坐、敲木魚。
大隊每年都要演戲,都是革命樣板戲,男主角是大隊支書的侄子開山,女主角是揚州插隊知青杏子。和尚是沒有資格演戲的,因他會畫畫,于是他負責畫布景、跑龍套、提臺詞。
這一年春節,公社要調演,各個大隊去比賽。路上,開山不小心跌了一個跟頭,腳崴了,這下怎么辦?支書急得直抓頭。和尚說,我來試試,抓急時也就不問什么“成分”了。替身上場,竟然比正角演得好,贏來一片掌聲,獲得全公社第一名。本來,和尚長期念經,嗓子洪亮,人長得帥,又有文化,每天提臺詞,臺詞也熟。根據公社要求,他們到各個大隊去調演,越演越嫻熟,越演越精彩。
女主角杏子長得漂亮,瓜子臉,丹鳳眼,皮膚白白的,胸部挺挺的,蠻腰細細的,屁股翹翹的,看得和尚心里跳跳的。回到家中,他就自責:癩蛤蟆也想吃天鵝肉,你的定力哪去了?更何況支書早就看上了杏子,托婦女主任做媒,將她許給了侄子開山。
“我喜歡你。”一個月黑的晚上,隊里草垛間,杏子主動表白。
“我不配,你是城里人。”
“城里人現在不也下鄉了嗎?”
“我當過和尚,成分不好。”
“我不問,你人好,有才華。”
“你與開山已有婚約。”
“那是逼的,現在提倡婚姻自由。”
幾支手電筒同時亮起,照著兩個人,開山帶著人跟蹤捉奸來了。開山將和尚吊在樹上,往死里打,支書站在一旁不說話。最后還是開山的叔奶奶來喝住。
“別打了,再打就出人命了。”
“不管怎么說,人家也是娘養的。”
支書與開山商量,早點把婚事辦了,以防節外生枝。結婚的前一夜,新娘子沒有了,到處找,找不著。有人說,看看和尚,和尚也不見了。
和尚和杏子私奔。那是一個買東西憑票、出門靠路條的年代,他們一路向東走,沿路乞討,路上倆人都不敢一起走,怕被捉住。到了百里之外的鹽城境內,那里有和尚的一個遠房親戚,編了一個謊話,說是家中遭了災。黃海邊人口稀少,到處是灘涂、魚塘。灘涂里野獸多、蛇蟲百腳多,于是,他倆在魚塘邊用毛竹搭起一個吊腳樓,幫助看魚塘。
深夜,和尚發現一個熱乎乎的身子緊緊貼住自己,馬上就明白是怎么回事,熱血涌上腦門,下體頓時硬邦邦的,沒一點驚訝,也沒有絲毫遲疑,很像是虛席以待了很久,他翻身上去……
“原來,你會呀?”
“才學的。”
“騙人!”
“真的沒騙,這是我第一次,我是和尚嘛。”
“過去怎么忍得住的?”
“忍忍就好,時間長了就忘了。”
“太監為什么要割掉?”
“那我也去割了。”
“昨天同意,今天我就不同意了。”
“你真是個狐仙!”
“狐貍有大尾巴,你摸摸,我有尾巴嗎?”和尚摸著杏子光滑的屁股,心中一片溫暖。
半年后,支書和開山帶人找到魚塘,用繩子捆了倆人,押回去交給公社革委會。最后,和尚以流氓罪被判了三年徒刑。杏子肚子大了,已經六個多月,于是免了。
坐滿三年牢,和尚回到老家,杏子生的兒子已經會叫爹。知青回城,杏子堅持留了下來,于是倆人結婚。因為窮,什么酒也沒辦,點了一對蠟燭,倆人對拜,兒子在一旁看稀奇。多年以后,他兒子愛說:“我爸媽結婚時,我吃了兩只草雞蛋。”
大隊里人從此喊他“花和尚”。
和尚覺得欠了杏子許多,萬事搶著干,起早貪黑,像頭黃牛,不知疲倦,對杏子百般呵護。對于別人的恥笑、對于支書的欺負,不去管他。日子再苦,也是甜的,家中常有笑聲。
后來,和尚摘掉帽子,案件平反。宗教政策已作調整,和尚的心又活了,開始每天打坐、念經。他到縣宗教局要求重修觀音寺,局里人答復,寺廟已拆掉,變成糧庫,沒有資金,修復有困難。于是就想到20里外的奶奶廟去當和尚。他和杏子為此吵了好多次。最后,倆人協商,每月初一和十五以及佛教節日和尚到奶奶廟去幫忙,其余時間仍在家中勞動。
新千禧年到了,事情有了轉機,縣里決定重修觀音寺。農業學大寨時,當地人想,大寨人能將荒山變梯田,我們為什么不可以把沼澤變良田。于是,把低洼處泥土挖上來,造出一個個垛田,一大片種了水杉樹,更多的種了油菜花,現在開發成水上森林景區和千垛菜花景區,和觀音寺三點連成一片。和尚主動報名,家中爭吵再起。最后雙方讓步,和尚白天到觀音寺重建處打工,晚上到杏子在景區邊開的“般若素齋”飯店幫忙。飯店名字是和尚取的,開素齋也是他再三堅持的,不過,素齋的生意一直不怎么好。
縣里給觀音寺派了一個和尚來做方丈,叫智真,宗教局一個副局長、旅游局一個副局長三個人作為籌建負責人。明珠已還俗,沒有和尚身份,只能是打工。因他做過和尚,就讓他參與設計和建設。
他隨宗教局長到外地考察。三個月后回來,和尚大驚,“般若素齋”已不做素齋,開始殺生,招牌菜改為“活殺雞公”“生烤麻鴨”“狗肉燒老鱉”,生意很紅火,杏子忙得不亦樂乎。
回家吵架是不可避免的。早晨起床后,他照例在香案前打坐念經,杏子拎起一桶水,迎頭澆下。
“做素齋,誰去吃?”
“念你個大頭經。”
“小伙要上大學,錢呢?”
“你媽媽誰養?”
“為了你,我揚州都沒回,你要當和尚,對得起哪個?”
杏子已沒有當年的嫵媚,一臉的兇悍。她的聲聲責問,如棒槌一般打在他心上,看來,家中是呆不下去了。
到了重建處,他更郁悶。智真不大念經,整天就談錢,動腦筋讓企業家、施主再多掏一點腰包。人少的時候,竟然在交談,附近的鎮上又新開了一家洗浴中心,新來了幾個漂亮的川妹子。聽說,智真在外還包養了一個19歲的小妹子。這哪像出家人?他跑到宗教局去告狀,被局長訓了一通。
“你多管閑事。”
“沒有錢怎么重修寺廟?”
“包養小妹子,你有證據嗎?”
“再這樣,你就不要來上班了。”他悻悻而退,百思不解。
工人在放生池邊挖到一個密封的大缸,以為是文物,趕緊把大缸挖起,抬到空曠處,一不小心,缸跌破了,里面淌出黑色的液體,露出一堆尸骨,空氣中彌漫著一股酒味和尸臭味。
和尚跪在地上,淚流滿面。他頓時明白,大缸就是當年寺前的貯水救火的缸,尸骨是師傅一塵的。古代不少高僧就有用酒把人封在缸中圓寂的。
眾人早已散去。和尚已經跪了一夜,他不斷在自問,我該怎么辦?
天亮的時候,他看到,遠處晨靄中村莊升起裊裊炊煙,身后工地矗立著塔吊,大河里的水靜靜地流向大海,一群白鷺從眼前飛過。突然,仿佛師傅的戒條在抽打他的膀子,一下,二下……真是鉆心的痛。想起師傅的兩幅字畫,頓有所悟,他站起身,包起師傅的骨殖,把它埋在放生池邊,恭恭敬敬地叩了三個頭,立下宏愿:再難也要建好觀音寺,其它以后再說。
從此,和尚變得沉默寡言了。在家不說話只干活,在重修處不發表意見,只做事。
觀音寺終于修好,開光的這一天,很多高僧大德來了,各級領導來了,很多捐過功德的施主來了,真是熱鬧。他獻上前任方丈的遺物:兩幅字畫。
和尚失蹤了,家里人不知道去向,觀音寺里也不知道去向。
有人說和尚自殺了,有人說出去打工了,還有人說到臺灣找他師叔去了……
十年后,南方某知名寺廟出了一個方丈叫明珠,他佛學深厚,善行廣布。
他在南方大學作題為《叢林森森》的演講,講述慶友、鳩摩羅什、玄奘、慧能以及近代的虛云、印光等法師弘法經歷。大廳里座無虛席,過道里都擠滿了人。最后,與大學生互動。
“大師,您為什么出家?”
“肚子餓的。”
“您受過戒嗎?”
“具足戒。”
“您破過色戒嗎?”
“破過,有老婆,還生了兒子。”
眾人驚訝。
法師微笑,不語。
■讀者來信■
編輯同志:
您好!
我叫李衛,我是常年訂閱者,在宿遷市宿城區一家單位上班。近日閱讀了《雨花》上《文學的舞臺—拍打皮球的人》一文,倍感親切。尤其是這句話:“雜志是個平臺或者說是個舞臺,一手托兩家。作者固然很重要,但觀眾也很重要,甚至更為重要。”這也是小說《福扣》修改后發出的感慨。
《福扣》寫得很實在,全文找不到一句華麗句子,盡管看似平鋪直敘,然而,故事里人物刻畫耐人尋味:福扣、三丫、崔二伙形象刻畫都很生動。仔細想想,回想過去的生活畫面,我覺得他們就在我身旁。無疑,這篇小說成為照見當下時代生活的一面鏡子。如今,寫小說的人很多,雜志也很多,可是能像《福扣》這樣過目不忘的小說是少之又少了。期待《雨花》的春雨滋潤出更多的不似《福扣》勝似《福扣》的小說來。
此致敬禮!
李 衛
2015年5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