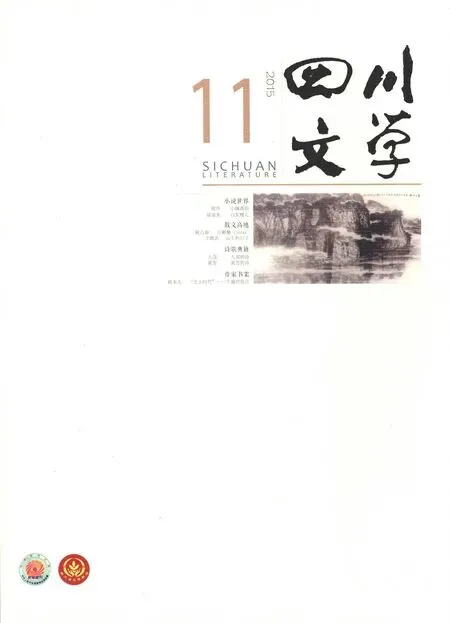最后的古村落
趙良冶
當游人的目光紛紛聚焦包裝一新的古鎮時,我將視線投向那些最后的古村落。
歷史上的南方絲綢之路,以及后來的川藏川滇兩條茶馬古道,古村落多如星辰,沿線散落,供商人背夫馬幫吃飯住店。近二十年來,沿著絲路古道,走了幾個往返。每一次,原生狀態的村落不斷從眼前消失,原住民紛紛遷離,成為最大的遺憾。
數據告訴我,中華大地上,有代表性的古村落已經不足三千個。規模大一點的,打造成我們常說的古鎮,終日游人穿梭,面目全非。
心既向往,最近一次南絲路之行,幾個頗具特色的古村落,專程一一尋訪,讀解原住民心靈的軌跡。
迤沙拉
金沙江畔,有村名迤沙拉。
國慶大假尾聲,探訪南方絲綢之路,再次游歷攀枝花。承蒙文聯朋友美意,不僅力薦彝族古村落迤沙拉,還特邀民俗專家劉勝利全程作陪。
對迤沙拉,事前茫然無知。所幸,劉勝利從事文物考古多年,攀枝花歷史文化,知根知底。沿途聽他說古道今,陌生模糊的迤沙拉,一下子變得熟悉又清晰。
車子沿著108國道,抗戰時的史迪威公路,過金沙江,爬上一個陡坡,眼前豁然開朗。對面山坡,一個頗具規模的村落,房屋參差錯落,從上向下延伸,直到山腳。這便是迤沙拉,今天的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兩千年前南方絲綢之路的一個驛站。
攀枝花氣候炎熱,天干少雨。迤沙拉更顯艱難,周圍無溪流,地底石灰巖層,水無法蓄積。彝語的迤沙拉,翻譯過來即是:水漏下去的地方。
彝家耿直,有啥說啥,漏水的地方,自然就叫“迤沙拉”。
迤沙拉兩千多人,彝族占絕大多數,屬于“里潑”這一支系。彝語的“里潑”,也挺有意思,“里”是女人,“潑”為男性。“里潑”連一起,意思是女人勤勞聰慧,男人強壯勇猛。
剛進村口,迎面即見大水塘。這個重要的水利設施,前些年落成,除解決生活用水,也給村落帶來些許靈氣。
除了這水塘,迤沙拉一切未變,依然固我,維系著原有的生存方式。沒有客棧,沒有飯館,沒有歇腳喝茶的地方。除去我和劉勝利,沒有一個游客,盡管正逢大假。
直覺告訴我,這個地方沒有打造痕跡。也就是說,旅游開發的浪潮,還沒有波及迤沙拉。這種原生狀態的古村落,即便在偏僻的絲路古道,如今也沒剩幾個。
村落多巷道。窄的兩人相遇,側身禮讓。寬的以三尺巷形容,絲毫不為過。一條小巷走不多遠,又分出另一條,彎來繞去,幾下就把不準方向。迷路不要緊,記著上坡進村,下坡出村,即可。
村民住宅,多建四合院,小巧別致,風格統一風貌古樸。木框架房屋,一樓一底,飛檐斗拱。就地取材,泥土筑墻,小青瓦屋面。富裕人家,正房和廂房門窗,雕飾花草。
彝族村落常年行走,見慣木房、竹房、草房、瓦板房、石板房,多為一層,結構單調。樣式獨特的也有,比如川西南的木羅羅,滇西的三坊一照壁,滇南的木掌房。只是難見迤沙拉這般,彝家民居,卻帶有蘇皖一帶建筑風貌。。
地處川滇交界,同幾千里外房屋,何以如此相似?心中泛起老大疑團,就教作陪人。
劉勝利指點迷津,何止房子的外觀,村中人家,到處走走看看,彝漢交融的風俗民情,感受絕對不一般。
堂屋高高,須拾階而上。屋內果然奇了怪,崇拜火,敬畏火神,被譽為“火的民族”的彝族家中,居然沒有常年不熄的火塘,不見祖先神靈牌位。中央靠墻,擺放精雕細琢的神龕,正中設 “天地君親師”牌位,兩側供奉歷代祖考妣和灶王菩薩,顯示出文化的差異。
服飾引人注目,男的不披查爾瓦,女的不穿羊皮褂。男女老幼,上裝的衣袖和領口,下裝的褲腳,佩戴的圍腰和飄帶,無不繡花。樣式和色調,則透射彝漢相融,合二為一。嬌艷可愛,莫過少女著裝。看那邊,過來的女孩,通身亮麗色彩。頭戴扣花帽,上衣圍腰做工講究,褲子繡花鑲邊,腳下一雙繡花鞋。無論花色樣式,還是刺繡手法,大有江南遺風。
至于談經古樂,悠揚婉轉,清雅柔和,起源江南絲竹和宮廷音樂。村中壩子,數十位樂手,拉著京胡二胡,吹著笛子嗩吶,彈著古箏三弦 ,聚精會神操練。《南清宮》《蝶落泉》《桂香頌》……一曲曲古樂,悅耳動聽。典型的漢族曲牌,彝家旋律自然無存。談經古樂,漢族地區幾近失傳,誰料絲路古道,居然有幸聽見。
提到音樂,不能不說迤沙拉民歌。
這民歌個性鮮明,風格獨具,成為絲路一種文化現象。村落的人愛說:“笛子一吹,調子就飛。”勞動與生活,情愛與傳說,喜怒哀樂,悲歡離合,一切皆在歌聲中。從漢唐的南方絲綢之路,到清朝民國的川滇商貿通道,經久不衰響徹古道。
這歌聲,源自生活,發乎真情實感,散發著山野的粗獷,蕩漾著江河的奔放,吟誦著“里潑”彝族的情懷。
不同的環境,不同的對象,自是唱出不同的心聲。
生離死別,有趕馬人與妻子對歌。
《大趕馬調》開篇,妻子那“砍柴莫砍葡萄藤,有女莫嫁趕馬人;趕馬之人良心狠,出門趕馬不管妻”的滿腔哀怨,記恨悲傷酸楚齊備,淚眼人恍若眼前。
《送郎調》中,癡情妻子義無反顧,誓言“踏爛布鞋千層底,跺爛花鞋幾十雙”,跟定趕馬人闖四方的決心,讓人為之動容。
男歡女愛,有情歌直白即興唱來。
阿妹戀阿哥,拋出歌來試郎心。一句“哥有心來妹有心,妹變花線哥穿針;哥是花針朝前走,妹是花線隨后跟”,感受癡心一片。阿哥愛阿妹,雙棲雙飛心連心。那句“妹有心來哥有心,一齊變對麻老鷹;半天云里同路走,雙飛雙落永不分”,可見情真意切。
接著聽來,向往太平盛世豐衣足食有《青棚調》,控訴戰禍連年兵荒馬亂有《募兵調》……
歌詞到唱腔,敘事風格到表現手法,漢族民歌的影響,隨處可見。
歷史變遷,民族融合,造就迤沙拉,文化可圈可點。一切的疑團,皆從村民姓氏中,尋找答案。
請出幾位老人,圍坐一圈慢慢擺談。
村落里,起、毛、納、張四大姓,彝族姓氏中極為罕見。要知道,四大姓源自幾百年前,并非這些年冒出來,也不是語言不通,采用諧音所致。
四大姓說起淵源,頭頭是道,各有來歷。
一句話,遙遠的江南,是祖輩故地所在。明朝初年,朱元璋派大軍平定云南,實行軍屯、民屯、商屯,鼓勵漢族同當地少數民族通婚。洪武開邊,四大姓做出貢獻;“里潑”祖先,多系屯田的軍戶民戶。
就如起姓人,當初并不姓起,本是軍中扛旗的兵卒。
千萬莫小看,扛軍旗也有學問。行軍途中,旗幟前導;安營扎寨,旗幟豎起;沖鋒陷陣,旗幟引領。
一旦解甲歸田,這扛旗的人,難舍生死與共的軍旗。既然“旗”與“起”諧音,“起”又含不倒之意,干脆就改姓了起。
毛姓人另有一說。他們這一族,追根溯源,竟然屬韶山毛氏一脈,與一代偉人扯上關系。
原來,毛氏先祖毛太華,洪武年間落籍云南永勝,膝下八個兒子。多年后,毛太華落葉歸根,帶走老大毛清一、老四毛清四,先定居湖南湘鄉,后轉韶山,是為毛澤東始祖。留居永勝的次子毛清二,后輩中有人遷徙云南大姚。清朝初年,迤沙拉歸屬大姚管轄,就有毛氏族人來此,世代扎根。
口說無憑,前些年,永勝、大姚和迤沙拉三地,將毛氏族譜湊一起。比對結果,竟然驚人的一致。
有趣還在,云南的毛氏后人至今是漢族。定居迤沙拉的毛氏后裔,則由于與彝家姑娘結為夫妻,搖身一變,依俗成了“里潑”彝族。
不過,此話兩說。上門給彝家當女婿的,既改族屬又改姓氏;娶彝家女為妻的,只改族屬不改姓氏。這樣一來,產生一種奇怪的現象——彝族人使用漢族姓氏,也就說清四大姓來歷。
納、張二姓的人則直截了當,都說祖先來自應天府,接下來便是四川、云南人大多會回答的那句話:柳樹灣石板橋。絕非胡編亂造,有歌謠為證:南京應天府,大壩柳樹灣;為爭米湯地,充軍到云南。
看我依舊似信非信,幾位老人急了,取來幾大本族譜,叫我仔細端詳。的的確確,五百年宗族輾轉,明朝洪武年至今,記個明明白白。
相信了吧!別說你,就是國外大學者,見到族譜,馬上信服。
老人們提到的大學者,即是斯蒂文·郝瑞,美國著名的人類學家,攀枝花的老朋友。劉勝利一旁補充,紛繁的民族變遷史,吸引了不少國內外學者前來。斯坦福大學畢業后,郝瑞開始將迤沙拉列入研究課題,記不清陪他來村落多少次。
絲路之上,民族紛繁交織。古老的西南夷,我們的先祖們,早就蹤跡渺茫,不知去向何方。
從明朝的洪武開滇,直到清初的湖廣填四川,大批的移民從江南流向四川、云南。移民們,帶來江南水鄉的生產方式、風土人情、文化藝術,對絲路沿線各民族產生巨大影響。漢族、彝族、藏族、白族、納西族,來自不同地域的族群,相互碰撞,兼容并蓄,再創古道新篇章。
民族融合,文化交織,家庭直到族群,折射五百年風云變幻的迤沙拉,引起郝瑞極大興趣。
二十多年間,郝瑞深入絲路古道,研究西南少數民族史。這個只會講英語的美國人,首先要過語言關。為方便同民眾溝通交流,郝瑞從中國話到四川方言,從彝語到古彝語,逐一學來,無不熟練。
郝瑞做學問,細致認真,吃苦耐勞,毅力令人欽佩。田間地頭,隨處坐下,與村民拉開家常;午飯極簡單,晚餐常常不能正點;村中老人,反復登門請教,收集村史家史;不厭其煩,挨家登記財產土地,核算每年收入支出……來得多了,村里人同郝瑞親熱起來,感覺這個老外挺好,什么話都樂于對他講。
郝瑞成就了迤沙拉,使這個彝族村落蜚聲在外。迤沙拉也成就了郝瑞,有關迤沙拉的學術論文,在國際社會產生重大影響。憑著這些學術成果,郝瑞一步一個腳印,由華盛頓大學一位普通講師晉升副教授、教授,終成著名學者。
郝瑞漸漸老去,他帶的兩個博士研究生常來,中國的學者們也常來。看來,迤沙拉的文章還得做下去。
暗自慶幸,迤沙拉舊貌依然,沒有被打造。今天的學者們,方能興致盎然,與這個古老的村落頻頻對話。否則,原住民遷出,商戶們涌入,村落舊貌換新顏,一切痕跡不復存在。學者們,又將去向何方,探訪先輩昨天的足跡?
時至今日,打造已成時髦流行語。幾年前,也有人動過迤沙拉的念頭。估摸涉及到搬遷、水源、交通、旅游市場諸多麻煩事,也就不了了之。
不見盡頭的小巷,依舊只有我和劉勝利,再加兩個被夕陽拉得老長的身影。沒有游客不要緊,少了世俗浮躁,留下一方清凈。秋陽下的迤沙拉,與打造后的無數古村落相比,成為難得的風景。
是古村落離我們遠去,還是我們拋棄了古村落?
動問迤沙拉,古村落無語。
白沙
玉龍雪山下,有村名白沙。
白沙雖小,卻不可小看,古老村落,歷史文化可圈可點。粗略數來,納西族文化發源地,木氏土司發祥地,白沙細樂肇始地,白沙壁畫所在地……憶及當年,麗江申報世界文化遺產,大研、束河、白沙,三駕馬車并駕齊驅,一舉入圍。
順理成章,麗江之行,少不了白沙。
國慶大假剛過去,這里的早晨,已是寒意陣陣。
商業化之風,吹進這個原生態的村落。漁獵農牧,納西族人世代沿襲的生活方式,悄然發生變革。一條主街,餐飲、茶吧、店鋪,開辦幾十家。小巷也不甘落伍,古老宅院裝修一新,掛起客棧的招牌。
不過還好,與大研、束河相比,白沙尚處于開發初期,村落保持本真,民風依然淳樸。以至有人直言:白沙是麗江古城的最后一片凈土。
漫步凈土,地方小吃,納西族民居,各樣特色工藝品,民族服飾的老人小孩……手持相機一一拍來。
鏡頭中,閃現土特產商鋪。一位賣刺繡扎染的老媽媽,讓我興致盎然。老媽媽一臉慈祥,通身納西族服飾,雙手戴玉鐲,輔以五顏六色的刺繡扎染背景,十分出彩。
抓住時機,中景近景特寫不停變換,角度上下左右快速挪動。
右邊腳底,突然感覺不對勁,軟軟的,還有異味撲鼻。低頭看,踩到一堆牛屎,熱氣蒸騰。前面,一條黃牛,正昂首闊步而去,沒有絲毫歉疚。
好在,街邊即是水溝,趕忙清洗。
一塊肥皂遞到面前,抬頭看見老媽媽。沒來得及道謝,人已離去。轉眼間,老媽媽拿出掃帚撮箕,清掃路面的牛屎。掃完后,撒上取來的泥土,將殘留糞便盡可能清除。
我有些吃驚,默默地盯著。兩位路過的外國人,停住自行車,掏出照相機。我恍然大悟,顧不得擦拭鞋上的污垢,啪啪按動快門,記錄下整個過程,包括忙于搶鏡頭的兩位年輕老外。
拍人物像問姓名,多年養成的習慣。聊開來,知道這里是南街,老媽媽名叫畢藍芳,今年七十五歲,兒孫滿堂。幾間鋪面,加工扎染的院子,全是自家財產。
叫聲畢大媽,請問為啥掃除牛屎?畢大媽說:“看見遠方的客人踩在牛屎上,心頭不安。我對不起你,讓你弄臟了鞋子。”
這言語,樸實又至誠。這年月,聽到這樣的話,真懷疑自己的耳朵。
我忙回答:“是牛拉下的糞便,與你毫無關系。”“不,牛屎在我家門口,是我掃遲了,對你不住。”畢大媽堅持己見。
終于鬧明白,這條街的清潔,原本安排專人。只不過,村里牛羊多,放牧途經街上,隨時會遺留糞便。這時,有個不成文的規矩,誰家門前有糞便,誰就會主動打掃。剛才的事,畢大媽認為是自己動作遲緩,讓客人產生不好的印象。
有什么不好印象,純屬自個兒不小心。甚至暗自慶幸踩到牛屎,否則就遇不到這樣的好心人。
為讓老人放寬心情,我岔開話題,指著鋪子里五顏六色的繡品,與畢大媽聊起納西族刺繡。
話匣子打開,畢大媽居然是一位刺繡高手。
刺繡藝術,作為納西族少女,個個都要學。小時候,看著媽媽飛針走線,面料上鳥兒飛翔,花兒綻放。心頭羨慕手發癢,吵著媽媽教刺繡。
里邊太多講究:面料隨意,綢緞、棉布、麻布均可;技法多變,平針、勾針、倒針、挑針、鎖針各具其妙;色彩考究,除著意古樸厚重外,姑娘追求鮮艷,老婦講究素雅;圖案豐富,花鳥魚蟲到幾何圖案,寫實夸張手法多變。
聊到高興處,畢大媽邀我進屋,翻出幾塊繡片,說是奶奶和媽媽留下。繡片老舊,但做工精細,尤其各種幾何形圖案和色澤搭配,讓我見識到上品刺繡的精妙。
畢大媽道來,村中刺繡代代相傳,民間高手多,名聲在外,以至譽為白沙三寶之一。哪三寶?就是壁畫、刺繡、和氏中醫,你都可以看看。
壁畫是不看的了,收費太高。轉身向北,往和氏中醫,準確地說是玉龍雪山本草診所而去。
小巷拐彎,一座老房子,門前掛診所招牌。
走進小院,幾間木屋,三五看病求醫者,依次候著問診。有村民,有游客,還有一位外國人。
診所簡樸,設施簡陋。一看便知,門邊端坐把脈的,必是醫生和士秀。和醫生慈眉善目,白頭發白胡子,再加一身白大褂,格外打眼。
見有客人,和醫生笑臉相迎,起身遞上一杯熱飲料。輕輕一抿,便知不是茶。清香的草藥味,讓人回味甘甜,解渴生津。
屋里屋外,陳列不少中外報刊,上邊的文章,大幅的照片,皆同和醫生關連。一墻的錦旗,印著“醫德濟民,神藥奇方”“玉雪仙翁,醫德高尚”之類褒獎之詞,想必是病愈者感恩之舉。
很是吃驚,和醫生滿口英語,同老外溝通交流。見我好奇,一位本村患者,講起和醫生往事。
和士秀一生坎坷,青年時學過外語,當過解放軍。一身戎裝的照片,放大后懸掛墻壁,可見當年瀟灑英俊。各種原因,身患重病的和士秀,歸家務農。為治病,踏遍玉龍雪山,采集中草藥,逐一熟悉藥性。十余年矢志不渝,不僅身體康復,還久病成良醫,掌握了不少草藥的奧秘。
診所開業至今,一晃近三十個年頭。先是給村民看,以后給游客看。慢慢地,名氣越弄越大,連外國人也知道納西族神醫和士秀,英語不錯,言語謙和。這一來,中外游客到白沙,有病沒病的,總愛跑來瞧瞧。
聽那邊,和醫生正問診,換了個中國人,通身游客打扮。飲食起居,情緒嗜好,逐一問個明明白白,再對癥下藥。
診所的藥好奇特。藥房內,堆滿瓶瓶罐罐和布口袋,里邊全是碾細的藥面。和醫生親自配藥,這個罐子倒一些,那個口袋取一點,分量不等,顏色不同。配齊,摻和均勻,用紙一一分包。
“一日三次,一次一小包。開水浸泡幾分鐘,當茶慢慢喝。”和醫生反復交代。
除了藥,每一位求醫者,還將得到一張紙條。中國人用中文,外國人用英文,和醫生分別書寫“病人要有治好病的信心”“樂觀是最好的藥”“不吸煙,不喝酒,簡單的食品,樸素的生活”等話語,算是一種告誡或臨別贈言吧。
時近中午,診療告一階段。忙一上午,和醫生依舊精力旺盛,與我交談,從草藥到診所再到人生,反應敏捷思維縝密。
收費不高,病人給多少是多少。遇到沒錢的,也就不收。反正藥來得便宜,不是山上采的,就是自家地里種的。來的病人再多,都得花時間與病人溝通。熟悉病人,是醫生的職責。取得病人的信任,二者合作,才能治好病。
和士秀醫術怎么樣,一面之交,委實難以評判。不過,醫者德為先,年近九旬的和醫生,懸壺濟世之心,的確讓我欽佩。
腳步聲響起,又來病人,告別和醫生,再去四處轉轉。
天不作美,飄起蒙蒙細雨。
那就歇歇吧,尋一個背風遮雨處,就著石凳子坐下。吃完干糧,想喝口熱茶,擰開杯蓋,水已冰涼。偏偏這時,肚子不爭氣,一陣陣的隱痛,大概剛才吃急了。
出門最怕兩件事,找開水和上廁所,運氣不濟,這下都碰上。
水火無情,推開一戶人家的大門,撞撞運氣。
景區上廁所,曾經遭遇多種尷尬。飯店茶館的,收錢還好說,無非一元兩元敲個竹杠。有的厲害,只要不在他那里消費,根本沒商量。至于住家戶,都是一推二關門,拒絕了事。
聽到開門聲,出來一位老人,是個男的。心里直發毛,經驗告訴我,男的更難商量。
吞吞吐吐,迂回婉轉費半天口舌。老人鬧明白了,手一揚:“解手是吧,廁所在左邊。”
如逢大赦,急忙如廁。
出來告辭,感激的話一大堆。老人笑著擺手,說不用謝,出門在外,誰沒個為難事。外面下著雨,屋里坐坐吧。
正有此意,就勢順水推舟,入客廳坐下。
客氣的老人,叫老伴泡茶遞煙,端來瓜子。我連忙阻攔,取出茶杯,摻上開水。幾口滾茶下肚,寒氣消退,周身舒坦。
老人告訴我,自己叫和振林,世居白沙,農技員退休,平日里栽花種地。得知我干了幾十年文化,對文物也略知一二,感覺投緣,一把拉住到處看。
房子雍正年間修建,歷代維修,至今完好無損。正房的六扇大門,兩廂的窗戶,全部鏤空雕花。那工藝,一望便是老一輩留下的玩意兒。圖案除了茶花和水仙,還有鳳凰亮翅、仙鶴起舞、喜鵲鬧梅等,滿屋子喜慶祥瑞。
新蓋的客廳廚房,風格也與正房統一,門窗同樣鏤空雕。仔細看,雕工不差,可見老人品位。
墻角邊,數十盆花木,點綴老宅院。
非常好的老房子,尤其是門窗上的雕刻,更是招人喜愛。前些年,就有人找上門,非要買雕花門窗,開口就是三千元一扇。不賣,又有人不斷登門,價錢也一個勁往上翻。
叮囑老人,一定要好好保護,留給后輩子孫。都賣了,白沙也就毀了。老人說,不賣的。這個道理很明白,白沙的文化是無價寶,多少錢都不賣!
臨走,老人提一袋瓜子相贈:自家地里的,不值幾個錢。
麗江到大理的火車上,我是一路磕著瓜子,念著這個明事理的老人。
人心本向善!白沙偶遇,深深印在我的心底,成為此行麗江中,一段最美好的回憶。
綺羅
騰沖城邊,有村名綺羅。
不同于和順的如雷貫耳,綺羅少為人知,即便緊靠騰沖城。
決意前往,即便沒有公交車直達,那就走一段路。待見村頭一排古樹,棵棵亭亭如蓋,便知是了。
絲路之行前夕,翻閱《徐霞客游記》,方知綺羅。那“竹樹扶疏,田壑紆錯,亦一幽境”的溢美之詞,很是讓我向往。
僅聞綺羅之名,就知其美。今日親眼所見,果如一條娟秀的絲帶,彎彎曲曲,盤繞來鳳、水尾兩山之間。只是奇了怪,“綺”在當地不讀“qǐ”,找人問路,得入鄉隨俗,將綺羅叫“矣羅”。
村落不大,街小巷窄,清一色石板路。村落古老,風貌原汁原味,延續著祖輩的生存方式。
不同于別的村落,小巷口總多一道門,稱為“總大門”。
“總大門”飛檐斗拱雕刻精致,門柱繪牡丹錦雞一類吉祥物。巷內全是同姓族人,各家門戶自立。老房子一間挨一間,小青瓦屋頂,火山石、黃土磚砌墻,一望便知百年光景。
空壩子,一地黃橙橙的谷物,農夫翻曬手不閑;水井旁,村婦們忙于洗衣淘菜,忘不了家長里短;大門口,孩童追逐嬉戲,惹得狗們來回撒歡;小巷里,慢悠悠晃出幾頭牛,視人若無物 ……
秋高艷陽天,村落趣無窮。奈何除開我,再無一個游客。沒有多余人也好,幽靜古樸,纖塵不染,如回夢中家園。不解的是,當年絲路古道,類似村落比比皆是,綺羅怎么就被徐霞客高看,到此一游。
綺羅不簡單,兩千多人的自然村,幾處文化景觀巍然矗立,讓天下村落望塵莫及。
順著蜿蜒流淌的綺羅河,且去水映寺,探訪當年徐霞客游蹤所在。
鄉村中,寺廟如今常見。幾間瓦房,相貌寒磣;幾尊泥像,手藝粗糙。也不怕菩薩怪罪,說來惹人笑。
水映寺不同,依山傍水,山蔥郁,水清澈。五百年古寺,逐一看去,玉皇閣、觀音殿等明代建筑氣概不凡,尊尊塑像工藝精湛。尤數觀音殿前,玲瓏水池半圓,清泉一涌千載。寺映水中,倒影清晰可見,水映寺得名,由此而來。
寺僧殷勤,古往今來講述周詳,提及徐霞客,卻又語焉不詳。莫怪僧人,徐霞客游記中,水映寺原本就一筆帶過。
百米開外,省級文物保護單位―文昌宮莊重古樸。
按照常理,村落有文昌宮,簡直不可思議。可綺羅不僅有,而且規模宏大,典型明代風格,融文廟規制與道教風格于一體。沿宮門、泮池、欞星門、文昌殿、至圣樓、魁星樓逐一走來,無不雕梁畫棟,氣韻不凡。
狀元橋前,凝望文昌殿,高大宏偉。正面楠木大門六扇,鏤空精雕范公書院、斐渡還帶、明刑弼教等六個典故。崇文尚教,褒揚正氣,綺羅民風淳厚。
民間傳說,功名大事,莫不出自文昌帝君恩典。祖輩寄望文風昌盛,州縣多建文昌宮,供奉帝君。科考前夕,天下士子必沐浴更衣,跪像前焚香化紙,乞求帝君開恩,鯉魚躍龍門。
文昌宮和順曾見,只是規模小許多,年代要晚兩百年。和順實屬不易,于今的鄉鎮,乃至更高級別的縣或市,文昌宮已成稀罕物。就連成都和昆明,南絲路兩個省會城市,文昌宮早已銷聲匿跡。
小小綺羅,對文化的尊崇,讓人肅然起敬 。
彌足珍貴,還在幾塊明清匾額。書法自然不錯,內容高屋建瓴,有“虛室生白”“偃月拳經” “精忠詣極”一類,意在警策勵志。尤為看重其中一塊,赫然大書兩字:文明!
如此見地,如此境界,驚訝之后是欽佩。無論文教昌明,還是文治教化,綺羅先輩的遠見卓識,我是五體投地。
文昌宮,寄托綺羅村民的精神追求,讀書求功名,讀書識禮儀,讀書知廉恥。朗朗書聲,延續幾百年,一方文明百姓安居。無怪乎,明清兩朝,綺羅可謂人才濟濟,文有學識淵博的進士舉人,武有保家衛國的將軍校尉。就說今朝,多有讀書人,村里每九個人中,就有一人有大專以上文憑。
這就是了,殷勤好客誠邀徐霞客的,便是綺羅讀書人李虎變兄弟。
山好水好莫如人好。徐霞客鐘情綺羅,蓋因此方人好,沐浴文明之風,知書識禮,情投意合。
聞貴客入住騰沖,李虎變兄弟趕往縣城,登門拜訪。一番交流,盛情難卻,方有徐霞客綺羅之行。
崇禎十二年(1639年)農歷五月四日,天不作美,下起濛濛細雨。李虎變備好馬匹,冒雨赴城中客棧,恭迎徐霞客。初見綺羅,徐霞客觸景生情,在游記中這么寫道:“時微雨,遂與之聯騎,由來鳳山東麓循之南,六里,抵綺羅”;“綺羅,志作矣羅,其村頗盛,西倚來鳳山,南瞰水尾山,當兩山夾湊間”;“是夜,宿李君家”。
游綺羅及周邊山水名勝,歷時七天,除一夜未歸,徐霞客在李家住宿五晚。村民告訴我,李家老宅位于玉虎巷,雖經風吹雨打,但保存尚好。
玉虎巷名稱,至今沿用,里面住李虎變后裔。正對巷口,兩棵香果樹,高大粗壯。小巷盡頭,老宅雖破敗,但大門氣派依舊。
主人自然姓李,面對我這不速之客,笑臉相迎,端茶倒水請坐。院墻高大,門樓雕花彩繪,房屋古香古色。道出來意,主人手一指,邊上那間廂房,便是先祖留宿徐霞客的地方。
廂房看去古舊,的確有數百年光景,可徐霞客是否就住這里,誰也無法認定。既然李姓后人這么說,村民們這么說,我就姑且這么聽著。
住哪一間房屋不打緊,徐霞客的游記沒有記錄,后人自然無從考證。至于和李虎變的交往,游記倒是屢屢提及。隨手摘抄,晨曦中攜手同游有“初五日晨餐后,即從李君循南山之麓東向行,先半里,過水映寺”;黃昏里遠迎有“李虎變以騎候于馬鹿道中,不遇,甫返”;美味佳肴招呼自己有“煮竹鼯相待”;酬答李虎變有“作田署州《期政四謠》,以李君命也”……
徐霞客滇西行,最南端游歷的村落,就是綺羅了。有此際遇,村中世代傳為美談。有好事者,就著泥墻,粉白后大書特書,廣而告之。
何止書生,綺羅有武將。
武將之一姓李名國珍,大清光緒年間,任騰越守備總兵官副將。
又是一處小巷深深,又是一棟衰敗的老宅。不說不知道,里邊藏龍臥虎,住過一位抵抗外辱的英雄。歷史教科書里,早就熟知“馬嘉理事件”, 景仰李國珍。殊不知,今朝有幸,得以瞻仰英雄故居。
1875年,英國組織一支勘探隊,二百來人全副武裝,氣勢洶洶從從緬甸入境。英駐華使館派馬嘉理為翻譯,率隊前往接應。侵略者氣焰囂張,槍殺百姓,揚言攻占騰沖。李國珍勸阻無效,率騰沖軍民英勇還擊,馬嘉理死于非命,英軍被迫撤出中國邊境。
清王朝腐朽,伴隨英雄的自是悲劇。安撫友邦,李國珍成替罪羊,從此命運多舛,歸隱家鄉。
綺羅多俊杰,歷史不會忘記。李國珍故居小巷,村民敬稱大人巷。文昌宮墻上,鑲嵌 “綺羅三李功烈碑”一通, 銘刻李國珍功績。這碑來頭不小,由騰沖名士、國民黨元老李根源題文,大名鼎鼎的于右任書寫。
另有“綺羅圖書館碑記”, 看來平鋪直敘語不驚人,亦非名家撰書。但碑刻言及的綺羅圖書館,傳承文明,造福鄉邦,堪稱表率。
民國之初,中國農村混沌未開,綺羅村民即捐錢捐物,創立圖書館,啟智育人。幾年下來,購買了《萬有文庫》《小學生文庫》等大型叢書,藏書達到兩萬多冊。另外,訂閱了《大公報》《文匯報》《覺民報》《仰光日報》等報紙,添置了風琴、油印機、動植物標本、人體生理模型,創辦了刊物《家鄉通訊》《新綺羅》。
1942年,日寇入侵,圖書館被洗劫一空,書籍蕩然無存,文明慘遭荼毒。
文昌宮附近這座圖書館,系1993年修建。雖為新館,設計者構思獨到。整座小院古意盎然,大門典型的滇西民居照壁樣式,主樓飛檐歇山式雙層木結構,周邊回廊甬道交錯,體現出濃郁的地方建筑風格。
傳承文明,服務村民,綺羅圖書館堪為楷模。藏書上萬冊,訂有報刊幾十種,書庫、閱覽室、休息室一應俱全,小橋、池塘、花圃休閑又養眼。恕我坦言,村一級沒見過這等檔次的圖書館。時興的農家書屋,無論面積、藏書量、讀者量,都不可與之相提并論。
窗明幾凈,幾個村民手握書卷,沉浸其間。兩鬢斑白的圖書管理員,格外引人注目。與之交談,方知圖書館沒有編制,沒有專職人員。老人退休后,就來這里上班,一晃十來年。盡義務的,不拿一分錢。幾十個春夏秋冬,先后五十來位老人,在這里維系著圖書館的運轉。
腳步輕快,跑進兩個小孩,老人轉身迎上前。
村落古老,但文明的進程代代相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