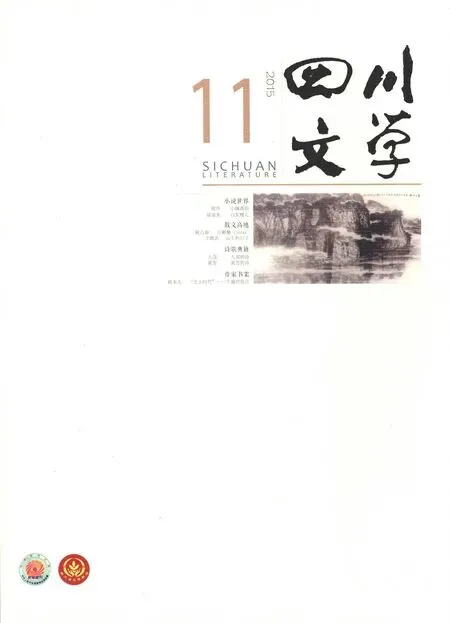大淖尋夢
周 游
大淖尋夢
周 游
昨夜,我做了一個怪夢―大淖干涸了。文游臺蕩然無存。鷦鷯無枝可棲。汪曾祺彷徨在沙漠里,前不著村后不著店……于是,我醒來匆匆來到了大淖。
大淖不大,但是很美―
淖,是一片大水。說是湖泊,似還不夠,比一個池塘可要大得多,春夏水盛時,是頗為浩淼的。這是兩條水道的河源。淖中央有一條狹長的沙洲。沙洲上長滿茅草和蘆荻。春初水暖,沙洲上冒出很多紫紅色的蘆芽和灰綠色的蔞蒿,很快就是一片翠綠了。夏天,茅草、蘆荻都吐出雪白的絲穗,在微風中不住地點頭。秋天,全都枯黃了,就被人割去,加到自己的屋頂上去了。冬天,下雪,這里總比別處先白。化雪的時候,也比別處化得慢。河水解凍了,發綠了,沙洲上的殘雪還亮晶晶地堆積著。(《大淖記事》)
這是汪曾祺筆下的大淖,就是這個大淖曾經令人意氣軒軒!
臺灣作家施叔青曾向汪曾祺提出要到高郵來看看大淖,素來好客的汪曾祺斷然拒絕了:“不能看,就如同我自己一樣。”后來,汪曾祺解釋說―
我去年回鄉,當然要到大淖去看看。我一個人去走了幾次。大淖已經幾乎完全變樣了。一個造紙廠把廢水排到這里,淖里是一片鐵銹顏色的濁流。我的家人告訴我,我寫的那個沙洲現在是一個種鴨場。我對著一片紅磚的建筑(我的家鄉過去不用紅磚,都是青磚),看了一會。不過我走過一些依河而筑的不整齊的矮小房屋,一些才可通人的曲巷,覺得還能看到一些當年的痕跡。甚至某一家門前的空氣特別清涼,這感覺,和我四十年前走過時也還是一樣。(《〈大淖記事〉是怎樣寫出來的》)
其實,大淖曾是沒有文化的“大腦”,就因為汪曾祺發表了《大淖記事》才得以正名,并且出名。隨著旅游經濟漸成熱門,加之尋訪汪曾祺筆下大淖的游客日漸增多,政府終于投入六千五百萬元整治了大淖環境。目前大淖,石欄圍岸,桃柳交錯,梧桐招鳳……可惜沒有了沙洲,沒有了茅草、蘆荻和蔞蒿,沒有了炕坊、磨坊、漿坊和草行,沒有了水車、牛棚和烏篷船,沒有了賣糖的、賣風菱的、賣熟藕的、賣紫蘿卜的、賣山里紅的和賣眼鏡的,沒有了錫匠、銅匠和挑夫……那些大淖人家似乎不翼而飛了!
他們還像候鳥一樣飛回來嗎?我在大淖岸邊徘徊了半天,看見各種鳥雀跳躍在樹枝上,惟獨沒有昨夜夢見的鷦鷯,悵惘之情油然而生。就在這時,文友姚云打來電話:“你在哪里瀟灑?”我答:“我在大淖,無法瀟灑。”姚云問道:“高郵修復汪曾祺老先生故居了嗎?”實話實說:“沒有。”姚云又問:“你看過梁由之新著《從鳳凰到長汀》了嗎?”我說:“聽說海豚出版社出版了這本書,我還沒有買到。”姚云快人快語:“梁由之在這本書里罵了你們父母官,我看了很解氣,先拍其中兩段文字轉發給你!”不一會兒,手機收到一條彩信:
沈從文夫婦的墓地,黃永玉立的碑,對時人、后世,以至千秋萬代,將構成強大而恒久的吸引力,是一筆無形、珍貴、巨大甚至難以計數的財富。而投入甚少,完全不成比例,簡直可以忽略不計。
由此及彼,嚴重鄙視江蘇高郵的地方官。那些伙計多是吃干飯的,無知無識,不知補救。汪曾祺生前想在故鄉有“一枝之棲”,他們無動于衷。汪老去世,葬在北京西郊福田公墓——那兒肯定不是老頭喜歡待的地方;墓地系有償限時使用,5萬元20年。地方當局為什么不跟汪老的后人商量,將老頭歸葬故里的文游臺呢?
讀罷信息,舉頭看見一株石榴攔住我的去路,那些花蕾儼然緊握的拳頭,其中定然包含著怒火。轉身走進草巷口,苦艾的氣味嗆得我喉嚨難受。
跨過東大街,我直奔竺家巷九號和十一號。兩戶間有標志:汪曾祺故居。九號現住著汪曾祺妹妹汪麗紋和妹婿金家渝;十一號現住著汪曾祺弟弟汪曾慶。兩戶只有六十平米左右,中間有個尕尕大的過道相通,且有大大小小的花盆,自有一番幽香的韻致。金家渝說:“這里只是當年汪家大宅院的后門偏屋,大門在東邊的科甲巷(今傅公橋路),有庭院,有花園,有客廳,有店面房好幾十間!此外,汪家在臭河邊還有一二十間房,另有兩千多畝地,多為草地;開了萬全堂、保全堂兩爿藥店,這些都是在他祖父汪嘉勛手上置的家產。”汪曾祺生前多次找“父母官”要求政府落實政策,歸還幾間閑置的汪家舊宅,改善弟妹的生活條件,以便自己回鄉小住寫作,結果大失所望,只能望房興嘆:“曾祺老矣,猶冀有機會回鄉,寫一點有關家鄉的作品,希望能有一枝之棲。區區愿望,竟如此難償乎?”(《致戎文鳳》)
坐在局促的汪家,我也局促,一股充溢在房間里鏹水似的悵惘不期而至……就在我將離開的時候,汪曾慶說:“新來的韓方書記和方桂林市長最近都到這里來考察了,大家都說他們值得期待!”我想也是。現代人對歷史的關心程度往往是越久遠的越關注其遺跡,或登樓眺望,或憑蹤遐想,然后像陳子昂一樣“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登幽州臺歌》);而對于近代的當代的,我們更關注的是名人的事跡,雖有遺物可以引發我們的感思,畢竟時過境遷,而被忽視的很多遺跡經過一番追尋與探討之后的東西則顯得更為可貴。高郵市政府應當根據人民的愿望以及海內外知名人士的提議修復汪曾祺故居,并將汪曾祺墓遷回高郵安葬,最好是在文游臺給他“一枝之棲”。文游臺定然會因汪曾祺而更崇高!
踅回東大街,我向文游臺走去,影子跑到了身子前面。不經意間,夕陽染紅了文游臺上的縹氣,暮色順著東大街漂流而下,流入了郭家巷、窯巷口、永安巷、草巷口、大淖巷、科甲巷、竺家巷……湮沒了吉升醬園、姜大升茶食店、連萬順醬園、如意泉、保全堂、邵家茶爐子、王家熏燒店、碗盞店、陶家炮仗店、戴車匠家、源昌煙店、馬家線店、嚴氏閣、如意樓、得意樓、萬全堂、七拳半燒餅店……于是,“很多歌消失了。”(汪曾祺《徙》)“很多人也消失了。汪曾祺也消失了。他的‘歌聲’依然在文壇回蕩,他的文字永遠不會消失。”(王干《向汪曾祺學習生活》)
站在文游臺下,站在汪曾祺紀念館門前,我看見鷦鷯頡頏在半空中,情不自禁地道了一句:汪老,魂兮歸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