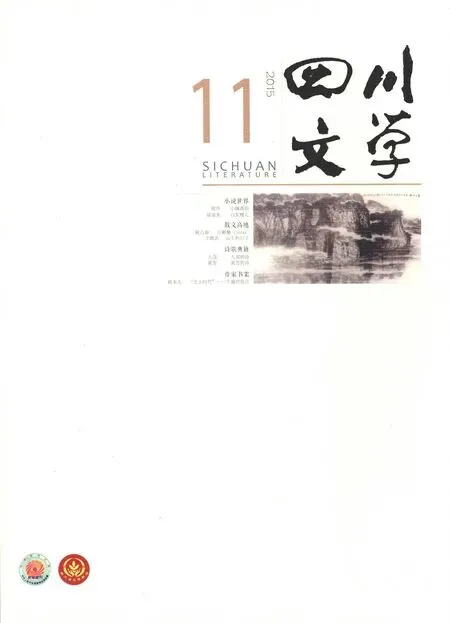“無土時代”:一個盛世危言
趙本夫
“無土時代”:一個盛世危言
趙本夫
趙本夫:江蘇豐縣人,一級作家,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享受國務院津貼的江蘇省優秀中青年專家。1988年畢業于南京大學中文系。1981年開始發表作品。198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代表作品《天下無賊》《刀客和女人》《混沌世界》《賣驢》等。
在中國,一直流傳著一個女媧造人的神話傳說:女媧用黃土和水,仿照自己的樣子造出了一個個小泥人,后來她覺得太慢了,便用一根藤條沾滿泥漿揮舞起來,泥漿灑在地上,就變成了無數的人。而在《圣經》故事中,也有上帝用泥土創造了男人亞當,又用亞當的肋骨創造了女人的記述。大家可以看出,泥土,在東西方的這兩個故事中都扮演了關鍵作用,它喻示著人來自土地,并將在土地上生生不息。土地才是人類真正的母親!
我在2009年初出版的長篇小說三部曲《地母》,是我對人類與土地關系長達二十三年思考的一個結果。《地母》最后一部長篇小說《無土時代》出版于2008年的年底,它也正是我對現代人類社會的一次寓言式寫作。
現在大家普遍認同一種觀點,即全球化正在使我們當下的世界處在四大沖突之中,而這四大沖突又分別引發了四個層面的生態危機:一是人與自然的沖突,引發自然生態危機;二是人與他人的沖突,引發社會生態危機;三是人與自我的沖突,引發精神生態危機;四是人與文明的沖突,引發文化生態危機。我的《地母》三部曲,對于這四種生態危機都予以了不同程度的批評。
《地母》的前兩卷分別是《黑螞蟻藍眼睛》《天地月亮地》。這前兩卷較多地關注了現代化之前的人與自然關系。《無土時代》作為《地母》的第三卷,它更為關注當下我們所日益面臨的社會生態危機與文化生態危機。因此,《地母》三卷,幾乎囊括了歷史上人類與土地的幾種關系方式―
土地―“萬物之母”:黃河是中國的母親河,但她曾經在歷史上多次決口和改道,都給兩岸的百姓造成一場又一場毀滅性的災難,但也因此給我們留下了豐沃的土壤和對苦難的承受能力。我曾經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騎自行車沿著黃河故道進行了一次考察,那次的感受至今難忘。土地浩渺無邊,每一塊土地都歷經歲月的流轉,經歷過無數的主人,但它從來沒有真正歸屬于誰,它只屬于它自己。在《黑螞蟻藍眼睛》這本書里,我描寫的就是黃河在上世紀之初的一次大決口,它沖垮了我們祖先建立的秩序和文明,大地重回洪荒時代。但就是在這片荒蕪的土地上,萬物重新繁衍生息,生命呈現出一派汪洋恣肆的繁榮景象。在幸存者與狼共舞的挑戰與冒險中,土地不再是引發無數次戰爭的財富,而成為人類的皈依和宗教,成為萬物之母。人們在渴求生存的同時,也在尋找著迷失的本性。
土地―淪為財富:歷史總是循環上演的,在任何一個國家的歷史上,發展的前奏,似乎永遠都意味著殘酷的圈地運動,大片大片的土地淪為被特權階層霸占、劫掠的對象,在民間社會,土地更加意味著財富,意味著夢想。但對于土地的激烈爭奪,也引發了種種人間悲劇。這是我在《天地月亮地》一書里的描述重點。
土地―被大片拋荒:現實發展中的中國正在為全世界所矚目。在進入21世紀之后,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中國的鄉村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有許多值得關注的社會、文化現象,我認為其中最令人觸目的就是土地被拋荒,鄉村即將消失這樣一些現象。這并非危言聳聽。我的老家在中國江蘇的北部,我曾經在一部短篇小說《即將消失的村莊》里面描述了我的那次蘇北之行。年輕人都外出打工了,村里只剩下一些年邁體弱之人,還有一口口的空屋子。那些屋子因為無人居住,年久失修,一場大雨往往就能把一座房屋壓塌。村長整天背著手在村里轉悠,看到哪家的屋子垮了,便從廢墟中搶救發掘出一點東西,等著房屋的主人哪天回來便還給他——但他們大多都一去不返了!成片成片的土地也變得荒蕪。我們習慣于把農村的勞動力外流說成是生產力的解放和發展,或者說是農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但很諷刺的是,這些所謂的“剩余”勞動力,恰恰是新型農村生產、發展最需要的中堅力量。年輕人對土地的厭倦和背離,正在日益加速著中國鄉土文明的斷裂。
《地母》這部長篇小說三部曲,應該說包藏了歷史上人與土地的全部關系類型,這也讓我們從中看到了歷史演變過程中的某種諷刺性“遞進”。人與土地的關系,能夠更為深刻而廣闊地折射出人性、歷史、社會、文化等多種領域的演變,這是我個人之所以如此看重“土地”話題的原因。
探討人類與土地的關系,也并非只為中國的文學家所熱衷,它還是一個世界性的話題。法國學者孟德拉斯有一本社會學經典著作,叫《農民的終結》。法國曾經是歐盟最大的農業生產國,但就是在這樣一個國度,孟德拉斯在上世紀六十年代就作出了“農民是即將消亡的群體”這樣一個驚人論斷。孟德拉斯把《農民的終結》一書視為“一個文明的死亡證明書”,“這個文明在生存了10個世紀之后死去了,結局證明我是有道理的:在一代人的時間里,法國目睹了一個千年文明的消失,這文明是它自身的組成部分。”在當下的中國,我們不得不承認,鄉村特有的文化與文明的消逝,堪稱當今影響人類生活最為重要的事件之一。這其中,也包括村莊的消逝這樣一個無奈的現實。
《農民的終結》這本書有一個總的出發點,那就是孟德拉斯所說的:“對于我們整個文明來說,農民依然是人的原型。”在我們中國,整個社會更是具有這種鄉土性。在我們的傳統文化里,“土”是一個有著濃厚文化色彩的概念,“土地”,也是人與自然親近、聯系的重要紐帶。但現代人拋棄了鄉土,遠離了土地。在我們的當下文化里,說一個人“土氣”,那等于是在批評一個人落了伍、過了時。因而,我們實質上生活在一個充斥著鋼筋水泥的“無土時代”。在中國國內,曾經有文學批評家提出,將今天的城市化時代命名為“無土時代”,是一個偉大的創見,但我無意于把這種“創見”視為我的個人所得,我更愿意認為,我只是說出了大家都沒有勇氣說出的心頭之語,心頭之痛!
古希臘詩人赫西俄德(Hesiodos)在他的長詩《工作與時日》中,借用神話故事對人類社會進行了“黃金時代”、“白銀時代”、“青銅時代”、“英雄時代”和“黑鐵時代”的劃分與命名。我們的文學史家,也常常借用這種劃分,來喻指文學的輝煌與低谷。而我們現在正站在21世紀的門檻上,面臨的是無處不在的現代化和無堅不摧的城市化進程,對于當下的中國而言,我們建立在這種土地之上的文明形式,以及這種文明所包括的道德倫理與種種文化符碼,都幾乎在一夜之間土崩瓦解了,失效了。“無土時代”最重要的表征之一,就是“一個人與自然對立的時代”,是一個“人與人失和的時代”,是一個“精神荒蕪的時代”。文學評論家們把《無土時代》視為一個寓言,我覺得它也是一個預言,這個預言,正在不斷地被我們生活的這個世界所證實,當然,我希望它也會被我們所警覺與防范。
我在《無土時代》里有這樣一個題記:“花盆是城里人對土地和祖先種植的殘存記憶。”這并不是我的臆測。身處任何一個國家的城市中,哪怕是最為繁華、喧鬧的市中心,我們只要抬頭仔細搜索,就能看到從陽臺、窗臺上探出頭來的綠色植物,當然,有些人家還幸運地在家門口擁有自己的一小片綠地——這在城市里,絕對算得上是一種奢侈的享受了。在我的《無土時代》里,木城出版社的總編石陀是一個迷失了自己,卻對大地情有獨鐘的人。他和生活在城市里的一幫志同道合者,試圖以各種方式,喚醒城里人對土地的記憶。終于有一天,他們使木城出現了361塊麥田,幾乎所有的城市綠地都被種上了麥子,城市的所有角落也都長出了莊稼和蔬菜。人們重新聞到了麥田的清香,沐浴在久違的星光和來自曠野的和風之中。這一夜,所有失眠的人都睡得極為香甜。《無土時代》是荒誕的,卻表達了另一種真實,那就是我們對土地由衷的懷念和對生態文明的深刻反思。
最近我很高興地發現,在中國現在有一個“夢田族”正在日益壯大。“夢田族”都是城市里的年輕人,他們喜歡在離城市不遠的城郊租下一塊菜地,利用周末或休假的時間,置身其中,種植、收獲各種農作物。現代通訊技術和發達的交通狀況正在為他們的土地夢想推波助瀾。我的太太也在我家附近開辟了幾小塊田地,零零碎碎,加起來也不超過半個籃球場大,全部使用有機肥料,我們收獲的黃瓜、生菜、茄子、土豆、辣椒等等,竟根本吃不完,還可以分出來一部分送給鄰居和朋友。
我是一個喜歡在土地上行走的人。前年,我曾只身在中國的大西北走了幾個月的時間,不乘汽車,不住賓館,沒有目的地,不要當地作家協會或文聯組織的安排與陪同,我只想做一次純粹個人的行走。我每天的行程都是漫無目的的,看到大路就走,看到村莊就歇息,我經常住在窯洞里,在老鄉家的飯桌上搭伙,和他們吃同樣的粗樸飯菜。這種行走,完全不同于走馬觀花式的旅游,有時候,我一整天都看不到一個人,也說不上一句話,實在走得累了的時候,我就搭乘老鄉的驢車。那是真正的自我放逐和漫游,也最為貼近大地和心靈,在那一刻,我時常感受到中國元曲里枯藤老樹昏鴉、古道西風瘦馬的孤獨意境。這一路上,我對人生、自然、物欲、價值、城市、鄉村都有了許多新感受、新看法。現代化本來就是一項充滿矛盾的事業,社會、歷史、人生進程本就是一體存在的,只不過,現在我們更要比任何時候都要在意一點:不要因此迷失了我們的自然與本性。這也是“無土時代”這個文學概念引起我國文學批評界普遍關注,并由此生發出許多社會、歷史、哲學話題的一個重要原因。
在中國,鄉土文學向來是一個根深葉茂的文學望族,它以獨特的“土氣息、泥滋味”而擁有深厚的美學意蘊。最近幾年,不斷有人站出來宣布,鄉土文學必將為城市文學所取代!這種觀念其實恰恰落入了城鄉二元對立的思想窠臼。中國的現代化,對我們的社會正產生著根本性的動搖。城鄉兩種文明、觀念的碰撞,也為中國的文學創作提供了一種多元、復雜的壯麗交匯場景。在這一特殊轉型時期,人們的種種現代性體驗與畸變在傳統文明的觀照下,都得以淋漓展現,文學題材的邊界也日益模糊化、多元化。我們的文學創作也絕非只能做出城市文學和鄉土文學、中國文學與外國文學這樣的簡單界定,未來的文學,一定是美學的融合,是對東、西方文化精髓的共同關注與提取。
有人還喜歡把鄉土文學視為對現代化歷史潮流的虛弱躲避,視為精神的無能與保守,但他們獨獨忘記了作家的責任是什么。作家應該是塵世的清醒者,也是一個孤獨的守夜者,鄉土文學對于塵世的提醒和現實批判,事實上,已經構成了獨具美學意蘊和精神重塑價值的寫作方式。鄉土文學作家所獨有的,通常也被批評為“落后的”、“土氣的”思想情感和美學方式,恰恰校正著畸形的社會發展軌跡,完善著我們的精神世界,就這點而言,鄉土文學創作具有著可貴的超前性,它是真正的危機時代的寫作。
朋友們,隨著經濟、文化的全球化,鄉土中國的現代性轉型,其中所包蘊的種種文化命題演變也并非僅僅是一個民族內部的個體現象,它已然匯入了一個世界性的話題之中。在此,我愿意和在座的諸位朋友有更進一步的交流與探討。謝謝大家!(本文為作者在2015年德國法蘭克福書市的演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