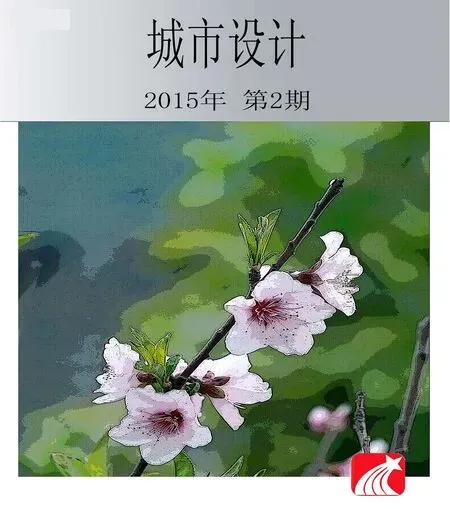香港開放空間:研討與啟發
祈宜臻
Tris Kee
褚英男 楊 滔[譯] 梁振鐘[校]
Translated by CHU Yingnan, Yang Tao; Proofread by LIANG Zhenzhong
香港開放空間:研討與啟發
祈宜臻
Tris Kee
褚英男 楊 滔[譯] 梁振鐘[校]
Translated by CHU Yingnan, Yang Tao; Proofread by LIANG Zhenzhong
編者按
Editor's Note
《城市設計》2015年第2期的特約專欄是《香港開放空間:研討與啟發》。專欄文章源自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專門舉辦的關于城市設計圓桌研討會的討論內容。這次研討會具有兩個特點。第一,參加人員既包括香港城市設計學會的成員,也包括獲得2014年城市設計相關獎項的專家學者等,體現了研討會的專業視角和開闊視野。第二,討論內容聚焦于香港開放空間,關注角度包括設計、使用、管理等多個層面,全方位地展現了香港城市設計的現況、成就以及未來愿景。“開放空間”作為主題,既展示了香港城市空間獨具魅力的特征,又體現了香港城市設計同仁的眼界和專業水平。文中可以看到,香港同行極富洞察力的觀點和具有前瞻性的理念以及批判性的視角。這對于大陸的城市設計發展,特別是公共空間的營造方面,具有很強的、直接的啟發和借鑒價值。
2013年冬,香港建筑師學會訪問北京,我受邀參加晚宴。席間,我遇到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林云峰前會長等同行,隨即向他約稿。在林云峰前會長、現任會長施培德博士、李嘉聲副會長以及祈宜臻教授等同行的積極推動下,香港城市設計學會舉辦了此次圓桌研討會。本期專欄文章的作者祈宜臻(Tris Kee)是香港城市設計學會(MHKIUD)會員、香港建筑師學會(HKIA)會員、香港國際設計協會(MRAIC)會員、香港室內設計學會(HKIDA)會員、香港建筑文物保護師學會(HKICON)成員以及香港城市設計學會(HKIUD)城市設計研究委員會成員。在此,對香港城市設計學會給予《城市設計》期刊的鼎力支持,表示特別誠摯的謝意!
朱文一
《城市設計》主編
2015年11月30日

祈宜臻(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城市設計研究事務委員會會員)Tris Kee, Urban Design Research Committee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HKIUD), HongKong
[譯者] 褚英男 楊 滔(北京市建筑設計研究院有限公司)
[Translator] CHU Yingnan, YANG Tao, Beijing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al Design Co, Ltd. Beijing, China
[校對] 梁振鐘(香港城市設計學會理事會干事)
[Translator] LIANG Zhenzhong, Council Member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Hong Kong
作為世界上人口密度最高的城市之一,香港有著高度控制的土地開發系統,特別是針對開放空間的規劃。這種管控性的規劃框架源于其獨特的社會、經濟、政治、地理因素。公私土地產權的內在聯系不斷挑戰著“公共”與“私有”空間的真實定義。本文借鑒2015年9月香港城市設計學會(HKIUD)舉辦的城市設計圓桌研討會的內容,定義并討論了與“公共”和“私有”開放空間相關的不同城市情境,從而更好地理解開放空間設計在今后如何更有效地促進城市設計的可持續發展。
公共開放空間;私人擁有的開放空間;城市發展;城市設計
“休閑設施與開放空間的規劃標準與準則直到20世紀70年代末才形成,1981年才獲準實施。從那時起,香港人口結構及社會經濟學特征都發生了明顯變化。生育率降低,家庭住戶平均人數減少,受教育程度提升,社會生活水平提升,以及最重要的是人口老齡化。”1
正如阿里·邁達尼普爾(Ali Madanipour)在牛津詞典中所概括的:“‘公共的(public)’一詞源于拉丁語‘人(people)’,有著非常寬泛的含義……作為形容詞,該詞指從屬于人們總體;或屬于、影響、或關于社區或國家;以社區整體的名義去實施,或構成、或代表社區;法律上形成社區,或代表群體;對社區所有成員開放、可獲得、可使用、或可分享;非私有的;作為一種服務、基金、便利設施等。”2
根據上述定義,可以將“公共的”一詞理解為個人生活在社會中的民主表現及其訴求。同理,公共空間可理解為,個體享有同等社會條件的空間,以此個體之間可自由交流,或個體與城市本身自由交流。
根據邁達尼普爾在《城市公共及私有空間》(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of the City)中所引用的內容:“社會自身組織的關鍵方式之一就是在社交空間和居住空間中區分出公共與私有領域。”3因而,城市的建成形態就是公共與私有概念分野的空間表達。個體在公共與私有領域中的交往行為由兩方面決定:一是社會教育方式,二是與城市的互動模式。城市中的社會活動行為取決于其活動場所是否為公共廣場、狹長街巷、聯誼會所、運動場或私人住宅。在這些不同類型的城市活動中,個體行為會遵循過去經驗、經濟限制、孩時記憶。城市可以輕易地接納我們,或排斥我們,并迫使我們回到私有空間中。
相似地,個體與城市的交流可以擴展到更為廣泛的城市空間和經驗,從類似城市廣場的“公共”空間,到另一個極端,即高度私有化空間,比如私宅。然而,最有趣的城市關系似乎就位于這兩個極端之間,構成了“公共與私有譜系”。在邁達尼普爾的《城市公共及私有空間》一書中,公共與私有的動態關系并非線性,也非界限清晰。事實上,二者不斷變換角色。公共與私有空間不應被理解為孤立體,而是互相依存、緊密關聯的。如果這種關系是互補的,而非分離的,那么公共與私有空間之間的關系概念將變得更加復雜。
為呼應邁達尼普爾的觀點,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在圓桌研討會上認為,公共空間與私有空間同等重要。在香港的大多數地區,市民在公共與私有領域間穿行毫無障礙。在《新城市空間》(New city spaces)中,揚·蓋爾(Jan Gehl)和拉爾斯·吉姆松(Lars Gemz?e)創造了一種城市分類方法,按照公共空間對日常生活的影響程度劃分為:
傳統的城市—交流空間、集市空間、交通空間等持續共存,并彼此平衡。
受侵蝕的城市—諸如車行交通的單一功能空間侵占掉其他用途空間。
被遺棄的城市—公共空間與公共生活消失。
復興的城市—采取強制措施,努力在交流空間、集市空間、交通空間等方面尋求新而可行的平衡。4
也許有人會說,香港并不適合上述任何一種類型。而如果采取純粹實用主義態度,則可將其歸入“被遺棄的城市”,類似于卡爾加里(Calgary)、溫尼伯(Winnipeg)、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亞特蘭大(Atalanta)等北美城市。“這些城市都有過街天橋,即步行橋系統;它們位于一層或二層,連接城市中心區建筑中的商店。”5氣候條件、經濟壓力和交通措施使得地面城市生活遠離了地面;復雜的人行天橋網絡連接了公共與私有空間,重構了街道空間,形成了空中步行系統。城市生活因而轉移到新的城市層面,其邊界不清晰,而又富有密集、緊張的城市體驗;而地面街道空間僅為交通服務。這與博迪(Boddy)的《地下與地上:構建類比城市》(Underground and Overhead: Building the Analogous City)所提到的卡爾加里情況類似:“當今,卡爾加里市中心被‘+15系統’(Plus Fifteen system)占據。地面空間史無前例地完全由交通占據。毋庸置疑,‘+15系統’中,大量商業空間的謹慎成功是以犧牲底層空間商業的數量與質量為代價的。”6
盡管香港似乎符合蓋爾和吉姆松提出的“被遺棄的城市”的范式,一些原本有活力的底層空間被封閉的私有空間代替,但該城市并不能被定義為“被遺棄的城市”,因為天橋、連廊、自動扶梯系統聯系著交通運輸、功能使用、零售業等領域。這套連接體系已經成為生活的另一個層面,調和了公共與私有領域,聚集了城市活動與活力(圖1)。
事實上,香港是世界上連接度最高的城市之一,具有高效的公共交通系統以及架空步行系統。這為城市核心區與海濱提供了多樣化的聯系。然而,公共空間的管理為規劃帶來了很多麻煩。在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圓桌研討會上,麥艾倫先生(Alan Macdonald)解釋道:“在香港,一共有23個獨立的政府部門負責城市公共空間的設計。然而,他們都沒把事情辦好。我們在中環有一個項目,開發商們發現如果改善周邊的環境、多考慮人們的感受的話,人們就會到這里來,尊重并享受這些空間”。
“不過城市公共空間的狀況已經得到了改善,幾個月前竣工的佐敦谷(Jordan Valley)是一個繁華、受人們喜愛的獨特地方(圖2)。觀塘項目(Kwun Tong)也取得了一些進步,成了一個高質量的場所。我仍然有些擔心參與公共空間管理的23個機構,但我現在看到了希望。就標準的場所而言,我認為觀念正在發生轉變,正在掙脫束縛、擺脫格式化。”
的確,復雜的官僚過程有可能妨礙開放空間城市設計的靈活性,但香港最明顯的特點之一就是這一系列由開發商提供的、復雜的開放空間。城市中,這種公共與私有領域的共生關系孕育了 “可識別的公共性”與“絕對的私有性”之間的豐富層次;同時,這也挑戰著我們對香港公共空間的認知邊界。盡管層次如重疊的馬賽克一樣復雜,法規嚴格、管理僵化,尤其是在土地發展控制機制方面,曾發展出一些有趣的空間類型,包括公共開放空間 (POS)和私人開發的公共開放空間(POSPD)7。
也有觀點認為,香港公共空間的情況是獨一無二的。香港政府認為公共空間是“為開放空間及公共康樂設施所設的法定用地區域。這部分也可指用于康樂的公共開放空間”。這意味著,香港公共開放空間由城市提供,滿足市民的基礎需求,從諸如閑逛和太極晨練這些被動式活動,以至積極的競技性運動等,私人領域并不一定能提供這些活動場所8。
香港政府部門的官方定義使我們不能忽視某些內容,正如米切爾(Mitchell)在2003年指出,“現代城市的空間越來越多地由‘由我們創造’轉變為‘為我們制造’。”9結果是,公共空間變得平庸,其設計僅僅為了滿足合約上的各項限制條件,而非真正考慮到市民生活需求。
香港發展局在2010年頒布的私人擁有的開放空間法則中更具爭議的概念是:“私人開發的公共開放空間條款的首要任務是使設計質量更高、場地使用更積極、場地規劃更合理以及平衡公共空間與開發利益之間的關系。通過恰當的設計與管理,私人開發的公共開放空間將致力于改善娛樂休憩空間品質以及香港的生活環境。”10
私人開發的公共開放空間被定義成香港公共開放空間中由私有業主開發的重要部分,納入私有開發計劃。這意味著私人開發的公共開放空間必須對公眾開放,同時由業主方進行管理。實踐中,這類開放空間是城市中最具爭議的話題。“……一些開發項目中已經出現了偏差,例如鎖門、關閉公眾電梯、妨礙通行等,令這些公眾康樂設施難以吸引公眾去使用。”(引用自《南華早報》) 私人開發的公共開放空間被批評為“無法接近,維護不力”。11公共開放空間的私有化正在破壞公共與私有的權限的傳統分野,并阻礙了公共領域的連續性。
由政府以及開發商建立的公共開放空間的模糊邊界,可以用理查德·桑內特(Richard Senett)在1977年提出的觀點來解釋,其觀點令人警醒,尤其是考慮到去宗教及產業資本主義等問題時。“……我們正緩慢地摧毀‘公共領域’,并將私有開放空間的期望值與分類提升至如此荒誕的程度,以至于私有開放空間對公共生活產生制約乃至摧毀。”12這種觀點與邁達尼普爾的公共和私有領域之間都有豐富和互補層次的理念形成鮮明對比。
歐華爾顧問有限公司董事羅健中(Chris Law)先生在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圓桌研討會上對此發表了富有見地的觀點:
“……顯而易見管理仍然是個大問題。我認為公共空間需要合理的管理體制,但是正如麥艾倫先生剛剛所說,目前的管理體制還不夠完善。我認為我們應該認真審視目前的管理體制,我們是需要對目前的管理機制進行完善還是要制定另一套管理體制,還需要考慮要對現有的公共開放空間管理機制進行改善需要多長時間。目前有很多公共開放空間正在建設,比如九龍東區和西區,所以對于香港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誰將管理這些地方?它們將會怎樣被管理?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私人開發公共開放空間的本質致使人們簡單地認為私人開發公共開放空間不好,公共開放空間好。如果它們太過自私、單純地滿足個人興趣,那么它當然不是一個好場所。但是也有一些非常負責的私人開發公共開放空間。最終問題還是落在了管理上,誰來負責這些項目。
我們有沒有一個開明的公共部門?我們有沒有一個像非政府組織(NGO)一樣潛在的發展第三方部門來管理公共空間?在公民社會推行強有力的機構體制,香港已經有150年的傳統。現在我們可以用該系統來為公共開放空間服務。我認為,一個方案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管理問題。我看過不少解決方案,它們綜合考慮了各項因素,不像現在這樣把責任都推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為了強調香港公共開放空間研討的獨特性,香港城市設計學會通過以下問題,試圖尋找在未來操作、管理和城市設計中的關鍵概念以及確定結論。
香港公共開放空間的實際情況是如何?
至2015年,香港總人口已達7,264,100人13,分布在1,108 km2范圍內。建成區域只占25%,公園、自然保護區占66% 。14在這種情況下,只有2.3%的香港土地被用于公共開放空間,而居住用地占6.9%。如果區分城市與鄉村用地,那么公園和自然保護區就不屬于城市用地范圍,剩下的開放空間總面積僅為2,343 ha,因而成為嚴重匱乏的資源。規劃署曾設立的標準是城市中人均享有最少1 m2公共開放空間,這意味著700萬人享有23.43 km2公共空間,主要由公園、游戲場和私有公共空間構成。
與其感嘆公共開放空間的明顯不足,不如深入理解導致這種情況背后的原因,這會使我們重新評估人口對城市的需求。主要出發點應包括:公共空間被占用的豐富性;公共和私有領域復雜關系;市民能在提升空間品質中扮演什么積極角色。
城市設計如何優化城市人行體驗?我們如何預期理想的公共空間?
在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圓桌研討會上,明確的一點是公共交通是香港發展的關鍵因素,幾乎貫穿整個歷史。城市發展資源優先用于提升公共交通的連接性與效率,而非人行環境。大多數非建設空間用于汽車、公交、地鐵,而人行空間則壓縮至標準尺寸的人行道。自20世紀80年代起,開發商開始將不同高度的商業和廣場連接起來,創造出“公共—私有”這種香港獨特的公共空間。
政府規劃文件關于開放空間的標準與導則在實踐中意味著開放空間的配置基于空閑場地,而非便捷性。大多數公共開放空間的開發分布在高密度城區的邊邊角角,并顯示出高度的標準化。例如,大多數兒童游樂場有相同的鋪地和設施,事實上,完全一致的長凳與種植使“公共”空間變得古板保守。
米切爾在2003年提到的“公共需求的異質化”意味著成功的公共開放空間需要提供豐富的空間層次以及活動的多樣性,但香港目前的政策對于這個理念而言是僵化的。公共空間是多樣性生存的地方,香港對于“公共”空間的規劃明顯抑制了多樣化的需求。
歷史文化豐富多樣的地區,例如廟街,已經成為香港公眾記憶的一部分。這些區域的歷史關聯已經脫離使用者,獲得獨立詮釋。這些集體經驗定義了城市中獨特的區域。
邁達尼普爾在2003年曾引用穆頓(Moudon)的觀點,強調公共空間可達性的必要,“大多數公共空間的定義強調可達性的重要,這包括可達空間以及參與其中的活動兩部分。即使空間是私有的,公共可達性也需要由法律保障”。15其可達性以及交通需求在香港某些地方由緊密連接的人行天橋所強化,這些區域在周末從人行基礎設施變成公共空間,從而獲得了延伸功能,既反映了交通連接,也反映了空間功能。
當人們體驗到本該是“公共”空間的可達性差的時候,就會常常選擇尋找替代品,例如將基礎設施變成另一種形式的公共空間。在香港,有證據表明不同形式的公共空間可由人口統計數據定義。法定的公共空間本該供老年人和孩子活動,而周末中央商務區的封閉道路卻被外傭所占據進行社交活動;私人經營的商場則最排外,經常僅由外國人及本地富人使用。
公共及私有空間中的產權體系
香港所提供的公共空間無法理解成簡單的城市元素,而是一個復雜的公共、私有連鎖體系。極端的城市條件,諸如缺少土地、超高的密度,已經培育出了私人開發的公共開放空間。裙房屋頂的空間已經成為公共開放空間的一部分,但是大眾并不熟悉這些協議條款和出租授權;而開發商則利用這一點,通過遮擋來減少公眾使用,比如安置警衛、增設欄桿、設置分區出入口等。這很明顯抑制了公眾對于私人擁有的開放空間的使用。
然后,問題應著眼于公共開放空間分配體系上,這意味著公共開放空間的可獲得性。我們需要解決的是管理的復雜性問題,即公共開放空間與私人開發的公共開放空間的關系。
以邁達尼普爾的文章作為參考,另一種應對這項挑戰的方式是重新定義我們對私有的理解。16通過重新審視私有的含義和限制,城市可以被重新定義為“公共”與“私有”兩個部分。因此在城市中不需要再將公共與私有開放空間區分得界限清晰。
香港熟食市場是一個闡釋公共私有產權界限相互關聯性的經典案例。這類建筑常被設計成相似的形式,并不是非常精致的建筑形式,然而這卻提供了公眾溝通的獨特機會。當近年規劃的公共空間限制了空間的使用方式時,相反地,熟食市場卻提供了不同社會階層溝通的平臺。
更多可持續的開放空間
在香港,公共空間的可持續性是一個重要的課題。理論上,公共空間從設計上應符合不同背景、不同年齡段、不同社會階層的人使用。由于香港人均居住面積非常緊張,因此享用公共空間對維護社會可持續性而言尤為重要。
為了顯示決心,城市的系統需要回應居民的需求、渴望及享受,尤其是對于貧困人口。居民之間的不平等關系是現代城市的一個非常棘手的問題。在世界上的很多城市中,貧富人群的差距相當大。因此,創造真正意義上的公共空間尤為重要,它意味著社會的全體人員都有相同的權利去使用,為社會的可持續性提供了著力點。
米切爾(Mitchell)在書中提出預示著城市未來的挑戰是“公共空間引起的恐慌,源于公共空間將成為失控空間,將成為易碎之處”。17根據這種觀點,恰當的開放空間規劃需要填補由私有空間稀缺性所導致的空隙,同時需要強調紳士化所帶來的社會后果,以使未來香港可持續發展。
根據香港設計學會代表夏樂彬(Bernie Harrad)先生所說,“社會的可持續性與環境的可持續性都非常重要,但是我認為更重要的是確保社會不同階層在不同時間對于公共空間都享有可獲得性,因為這正是人們享受公共空間的方式。因此,清早有人打太極,上午有父母帶著孩子來玩耍,緊接著中午有工人,下午有學校的學生,也有下象棋的人圍攏來,晚上有人來打籃球或從事其他運動。這正是我愿意看到的,空間設計的靈活性使得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利”。
結論:城市設計的關鍵注意事項
為了研究什么是“好的”城市空間,需要明確幾個與社會完整性相關的現實空間方面的有趣問題。“……人工創造的公共空間好至何種程度?18……公共空間的邂逅功能是什么?社會凝聚力和對隔離的擔心與此有多大聯系?19……。”在海耶爾(Hajer)和瑞金喬普(Reijndorp)看來,問題源于缺乏來自于管理者、設計師和開發商等不同“參與者”的視角,以及在公共空間設計上所采取的線性工作模式。空間內在的復雜性常被忽視,空泛的對策常被采納,這忽視了內在豐富的差異性。
“差異化”(difference)和“異質化”(heterogeneity)是米切爾、海耶爾和瑞金喬普文章中的兩個關鍵詞。在他們看來,自相矛盾的是,規劃好的開放空間之所以成功,恰恰是由于其缺少規劃。香港大多數公共開放空間被規劃為休閑功能,并采用過時的規劃導則和嚴苛的限制條件。因此必須考慮協調之外的其他事情,因為協調無法變成人們涌入的全部誘因。聰明的城市會吸引異質性。例如,韓國政府正在改革,提升城市中公共空間的體驗,允許在公園和海邊港口地區搭帳篷露營。
公共政策成功激發城市活力的案例之一是中環半山扶梯。扶梯的建造是為了解決中央商務區和中間層居住區的聯系,而事實上該區域建成后已成為外國人和本地人共享的活力地區,這是規劃上所沒有的。另一方面,以法定守則及相似理念進行規劃的薄扶林(Pok Fu Lam)地區的電梯,增加了很多柵欄,卻僅用于交通,阻止其他的社會活動。香港正在逐步成為“智慧型城市”,像西貢海濱公園及前已婚警察公寓改造成的元創方(PMQ)(圖3—圖4),就鼓勵功能混合使用,這種協同會吸引更多不同目的人群聚集。諸如此類的公共開放空間激發了周邊區域與城市整體的社會價值。
此外,還有許多未被充分利用的機會,可用來發展獨特優質的香港公共空間。例如高密度城區以外的香港郊野公園就是絕佳的機會。如果城市公園能與城市綠道相連,那么香港的公共空間情況將會大大改善,形成一個綜合了公園、人行道和廣場的網絡。這種創新需要規劃予以貫徹,當然也應該指出,香港的發展從來不是由總體規劃自上而下產生的,而是由每個獨立開發計劃的集合所形成的。
成功的關鍵:社會不同聲音的平衡?
作為總結,當談到公共空間時,社區大眾應該是話語權最強的一方。因為社區大眾是最終的使用者,他們需要在項目的前期就參與其中,包括收集公眾意見、公眾參與項目、宣傳教育等。另一個重要課題是,利益相關的人要積極參與到公共開放空間的規劃設計過程中。為打破先入為主的概念,透明度也是重要的問題。現實中,互有交集的“社區”“政府”和“開發商”都是城市發展中的重要角色。拋開社會經濟指標,對“社區”正確的理解應當由簡單的標準與導則所設計出來的公共空間向高效滿足人們各項需求的公共空間轉變。
“既得利益者”是在很多城市發展研討會都被提及的一個重要因素。例如,開發商的形象是好或壞,僅僅取決于其盈利動機,這常常使得開發商獲得消極的形象。“開發商的主要驅動力是補償和利益,他們認為城市開發只是商業運作。”在香港,城市設計者和房產開發過程是完全沒有任何聯系的。20
在香港,私有開發商在歷史上很少屈服于城市設計為公眾利益所做的限定條件。私有開發商前期階段缺乏管理,直接降低了獲得高質量公共空間的可能性。21
為了公平競爭,各方既得利益者必須樹立良好的公眾形象,而密切相關的社區大眾也應充分表達對空間的切實需要,這將是重新思考公共領域設計所邁出的重要一步,使公共開放空間的設計超越現有水平。

圖1 / Figure 1中環半山扶梯和步行系統Central-Mid-Levels Escalator and Walkway System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圖2 / Figure 2原址為堆填區、占地約6.3公頃的“佐敦谷公園”Jordan Valley Park: Formerly a landfill site, the Park occupies an area of about 6.3 hectares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圖3 / Figure 3“元創方”的中庭為活動和展覽提供場地Central courtyard within PMQ for events and exhibitions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圖4 / Figure 4由中環荷李活道已婚警察宿舍活化而成的“元創方”PMQ: Former Police Married Quarters located in Hollywood Road, Central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附錄 A
香港城市設計圓桌研討會
Urban Design Roundtable Discussion
Suzy Annetta 陳祖聲 夏樂彬 何文堯 景國祥 林云峰 Rebecca Lo 麥艾倫 Aisha Speirs 譚寶堯鄧文彬 鄧兆基 溫灼均 黃國揚 嚴觀偉
Suzy Annetta, Joel Chan, Bernie Harrad, Ivan Ho, KC King, Chris Law, Bernard V. LIM, Rebecca Lo, Alan Macdonald, Aisha Speirs, P. Y. Tam, Stephen Tang, ShiuKee Tang, Thomas Wan, Edwin WONG, Michael Yen
受2014年香港城市設計學會獎及公布獲獎項目的影響,香港市民希望香港城市設計學會能批判地討論優質公共空間的設計原則及城市設計者們如何借助優質的公共空間來改變我們的城市。
此次研討會談將圍繞“城市設計與公共空間”這個主題展開。城市是我們的家,而公共空間猶如家里的客廳。那是我們與人碰面和上下班的所經之地,也是我們聚會、消遣的地方。合理規劃的公共空間必然會提高城市生活的質量,公共空間也能給我們的日常生活增添不少樂趣。
鑒于公共空間的復雜性及其很少被人們理解的情況,要合理設計公共空間并不容易。下面是五條合理設計公共空間的重要原則,其適用于公園、購物中心、公共廣場、街道、人行道、車道等公共空間的設計。這五條原則也是此次討論會的重點。
第一,把空間轉變為地點。
第二,私人供應,公眾受益。
第三,確保公共空間的可持續性。
第四,使其充滿活力并保持多樣性。第五,公眾參與的街道。
會談文本
0:00 祈宜臻女士: 阿爾多?羅西已經談論了場所精神,也就是一個地方的場所感。這讓我們意識到建設我們城市場所感的重要性。然而,環顧四周不難發現我們的城市已是高樓林立,購物中心和汽車也隨處可見。因此,我們需要考慮怎樣才能創建一個以行人為主、車輛少、活動空間更充足的城市。
4:11 Rebecca Lo女士: 前幾天,我在荷李活道上發現了一個公共空間。在那里我意識到,香港的公共空間是“普遍糟糕的”。它們的功能設想過多,服務對象也設想過多。比如,一個純色的攀登架與其周圍的一切格格不入;專門為孩子們設計的橡膠地板是那么丑陋,且從未被孩子們使用過,因為沒有人會讓他們接近那塊地板,最根本的原因是那不是一個舒服的場所。同樣的支出,它原本可以規劃得更好。
5:20 Suzy Annetta女士: 在香港有許多不能行走的街道。這些街道上要么沒有完整的路徑可走要么你根本不能穿過這些街道,因為街道中央設有路障。城市規劃者們待人如羊,以為每個人都需要引導。
對公共空間而言,去年的示威活動是一個關鍵的時刻,許多香港人首次有機會真正走在街上。我認為,如果人行道和公共空間真的適合步行的話香港將會大有不同。
6:33 Aisha Speirs女士: 我認為這座城市最有趣的事之一就是每到星期天它就大變樣。那時,你可以充分利用這些原本被占用的人行道,下雨的時候你可以在上面奔跑。并且,在星期天它們就成了外傭們的公共空間。該事件確實給城市帶來了很大變化,舞蹈、音樂、修剪指甲、推拿都在這里進行。事實上,這是一個能讓我們能使用這些空間的有效方法。那么,我就想問,為什么周五的時候這些人行道上沒有活動呢?這些地方是如此具有“香港特色”,對這座城市來說,它們也是這樣獨具特色。
策展人
李嘉聲先生(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副會長,負責對外事務;研討會策展人)
Mr. Charles Li, Vice President (External Affairs),Curator
主持人
祈宜臻女士(香港城市設計學會城市設計研究事務委員會會員,研討會主持人)
Ms. Tris Kee, Member of Urban Design Research Committee of HKIUD,Moderator
參會者
Suzy Annetta女士(Annetta工作室創意總監,出版人和總編輯)
Ms. Suzy Annetta, Publisher & Editor-in-Chief at d/a, Creative Director at Studio Annetta
陳祖聲先生(理事會干事)
Mr. Joel Chan, Council Member of HKIUD
夏樂彬先生(義務秘書)
Mr. Bernie Harrad, Hon. Secretary of HKIUD
何文堯先生(副會長,負責公共事務)
Mr. Ivan Ho, Vice President (Local Affairs) of HKIUD
景國祥先生(建筑署得獎代表)
Mr. KC King, Reprehensive of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Awardee of the HKIUD Awards 2014)
羅健中先生(歐華爾顧問有限公司得獎代表)
Mr. Chris Law, Reprehensive of The Oval Partnership Limited (Awardee of the HKIUD Awards 2014)
林云峰教授太平紳士(上任會長)
Prof. Bernard V. LIM, JP, Immediate Past President
Rebecca Lo小姐,自由設計作家
Ms. Rebecca Lo, Individual Design Writer
麥艾倫先生(雅邦規劃設計有限公司得獎代表)
Mr. Alan Macdonald, Reprehensive of Urbis Limited (Awardee of the HKIUD Awards 2014)
Aisha Speirs女士,《Monocle》雜志香港總編輯
Ms. Aisha Speirs, Hong Kong Bureau Chief at Monocle
譚寶堯先生(理事會干事)
Mr. P.Y. Tam, Council Member of HKIUD
鄧文彬太平紳士(副會長,負責專業發展)
Mr. Stephen Tang, Vice President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of HKIUD
鄧兆基先生(理事會干事)
Mr. Shiu Kee Tang, Council Member of HKIUD
溫灼均先生(建筑署得獎代表)
Mr. Thomas Wan - Reprehensive of Architec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Awardee of the HKIUD Awards 2014)
黃國揚先生(理事會干事)
Mr. Edwin WONG, Council Member of HKIUD
嚴觀偉先生(得獎代表)
Mr. Michael Yen, Awardee of the HKIUD Awards 2014
贊助者
The Madison Group
7:35 羅健中先生: 香港有一個世界一流的公共空間——廟街和它前面的廣場,它們被評選為世界上最好的公共空間之一。我個人認為原因是它滿足了世界公共空間的所有要求。我們能從廟街學習的地方有很多。
8:31 祈宜臻女士: 我們想強調的是一些好的公共空間應該具備的關鍵點。比如,廟街是以行人為主,許多活動在那兒舉行,人們也可以在那兒表演。
9:00 羅健中先生: 一個炎熱的周六,我參加了廟街的一個在樹下舉行的活動,真的很好。它正如一個供每個人使用的公共客廳,街上有各種各樣的活動,有小商店也有國際連鎖店。就管理而言,白天它由警察管理,到了晚上就歸社區管理。因此它實現了管理多樣化,這是公共空間管理的關鍵。它滿足了合理設計的標準也具有豐富的多樣性。
廟街的故事眾所周知,但是不同的人持不同的觀點。人們對公共空間的看法受個人背景的影響。而事實上,正是這些事件使廟街成為世界頂級的公共空間。
10:55 麥艾倫先生:在香港,一共有23個獨立的政府部門負責城市公共空間的設計,然而,他們都沒把事情辦好。我們在中環有一個項目,開發商們發現如果改善周邊的環境、多考慮人們的感受的話,人們就會到這里來,尊重并享受這些空間。
不過該城市公共空間的狀況已經得到了改善,幾個月前竣工的佐敦谷是一個繁華、受人們喜愛的獨特地方。觀塘項目也取得了一些進步,成了一個高質量的場所。我仍然有些擔心參與公共空間管理的23個機構,但我現在看到了希望。就標準的場所而言,我認為他們的觀念正在發生轉變,他們正在掙脫束縛、擺脫格式化。
12:00 祈宜臻女士: 佐敦谷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因為它同樣是由一個垃圾處理廠轉變成一個公共空間的。我記得我看到的那些禁令標志。但是我認為人們的態度正在發生變化。例如,除了麥艾倫先生提到的23個管理機構外,灣仔的管理更具多樣性(圖5—圖8)。
13:52 鄧文彬先生: 在香港行政機構的管理下,開放空間的設計受到一些保守的政府機構的限制。例如,為了避免落水,禁止在游樂場、開放的場所使用水;不管需不需要,四處設欄桿。但是,我認為一些充滿激情的致力于實現公共空間合理設計的專家能讓這些情況有所改觀。事實上,目前也已經取得一些成效。在啟德,既未設置路邊欄桿,并且原計劃修建的環城路現在成了人們散步的場所。想要把這些轉變成“標準”就需要政府高層的統一,還需要設計專家們額外的努力來與傳統的思想作斗爭。
管理是設計公共空間的又一重要問題。一些公共空間的管理機構不喜歡花,因為當花瓣落地后,清掃工作就會增加。香港迪士尼外的迪欣湖的設計者引用了一個極端的案例:有座位的地方沒有頂棚,有頂棚的地方沒有座位。這樣的設計防止人們在同一地點逗留太久,可以把管理需求降到最低。這樣的“管理才能”和與之相對應的風險最小化態度是我們在空間設計中必須克服的障礙。
16:50 祈宜臻女士: 我認為“工程思想”和“管理才能”是很難克服的,尤其是還要管理720萬人口。另一方面,我明白他們之所以要在路上設置禁止行走的標識是因為他們不希望人們處于危險之中,但是我認為在此期間一切都在發生變化。
我想問的問題之一是管理:私人供給,公眾受益。在香港,歸屬權問題一直是比較棘手的問題。我們有復雜的歸屬權系統,存在一些私人擁有但大眾也能進入的地方,比如和昌大押 (The Pawn)。和昌大押的屋頂是公共空間,但是幾乎沒人知道這里的情況。我們面臨著許多所有權的問題:我們需要克服哪些障礙?除了強制管理和那種狹隘工程方面,我們還面臨著什么問題?你想要在香港看到些什么?
18:14 羅健中先生: 幾位發言人已經談論到了管理的問題,顯而易見管理仍然是個大問題。我認為公共空間需要合理的管理體制,但是正如麥艾倫先生剛剛所說,目前的管理體制還不夠完善。我認為我們應該認真審視目前的管理體制,我們是需要對目前的管理機制進行完善還是需要制定另一套管理體制?我們還需要考慮,要對現有的公共空間管理機制進行改善需要多長時間。目前有很多公共空間正在建設,比如九龍東區和西區,所以對于香港來說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誰將對這些地方進行管理?它們將會怎樣被管理?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私人場所的本質致使人們簡單地認為私人場所不好,公共空間好。如果它們太過自私、單純地滿足個人興趣,那么它當然不是一個好場所,但是也有一些非常負責的私人場所。最終問題還是落在管理上,誰來負責這些項目。
我們有沒有一個開明的公共部門?我們有沒有一個像非政府組織一樣潛在的發展第三方部門來管理公共空間?香港在公民社會推行強有力的機構體制,已經有150年的傳統。現在我們可以用該系統來為公共空間服務。我認為,一個方案不可能解決所有的管理問題。我看過不少解決方案,它們綜合考慮了各項因素,不像現在這樣把責任都推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
21:44 譚寶堯先生: 我們應該掙脫常規意義上公共開放空間概念的束縛,如果我們遠離那些成見,就會產生一些新的機會,就不會把私人空間和公共空間劃上明顯的界限,也許我們可以讓其他機構來負責管理或把所屬權交給它們。這讓我想到了一項好的設計可能帶來發展機遇,那么剩下的問題就是我們怎樣用專業的城市設計原則來使其發生變化,并且讓公眾明白。那時,我們就不會抱怨不好的事物。相反,我們應該鼓勵那些有思想的、想要為城市發展做貢獻的開發商,為他們提供好的案例,這些案例也是我們建設高質量公共開放空間所追求的目標。
24:40 Rebecca Lo女士: 我認為,公眾對什么是公共空間、什么是私人場所仍然存在疑惑。還是拿和昌大押來舉例,有誰會知道那是一個私人場所?有些購物中心看起來像公共空間,但如果有人要坐在那兒,保安就會把他攆走。這樣的情況在公共空間很常見。很明顯,在公眾的心中,那樣的地方就是公共空間,但實際上它們并不是。所以,為什么和昌大押會是一個公共空間呢?誰會知道,又該如何向廣大市民解釋呢?
25:37 Aisha Speirs女士: 我認為香港最有趣的公共空間之一是熟食市場,在那里可以看到來來往往的人群。它就像一頓公共/私人午餐,因為那里的私人食品店出售各種各樣的商品,每位顧客都可以享受一樣的待遇。在這些公共空間你既可以免遭雨淋,還可以吹著空調品嘗美味的意大利美食,同時你的朋友也可以享受美味的中餐,其他人還可以品嘗泰式美食。因此你會感到自己像是在公共空間舉辦的私人派對上,可以任意選擇自己喜歡的美食。然而,在城市里當我們擁有許多這樣的公共空間時,該如何利用這些空間又會成為一件令人煩惱的事。
27:00 嚴觀偉先生: 談到“管理心理”及“工程心理”問題,我認為應該再增加一個“開發商心理”,因為在香港開發土地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例如,修建商業街每平方英尺的成本是100,000港幣,如果政府不提供任何優惠政策,這樣的工程是很難實施的。此外為了公共利益而削減我們的利益,這對我們來說也是極具挑戰性的。但不知怎的,情況正慢慢發生變化。比如,以前我曾為一位開發商工作。他們家族第一代人追逐的主要是數量和最大化的利潤。并且,在談及公眾對位置的傾向性、空間感以及幸福感時,第二代人仍然持相同的想法,仍然很難擺脫利益沖突的困境。
最近,我正與歐華爾顧問有限公司和羅健中先生合作一個項目。為此我們不得不與政府打交道,并且為了給公眾多留一些空間,我們也盡力不去占用所有的建地面積,但是我們仍然收到來自政府部門的許多反對意見和通知。因此我認為,關于心態還存在一個問題,那就是是否所有的開發商總是試圖從投資中取得回報,在20年前往往是這樣的。但情況正在發生變化,因為開發商已經明白即使他們不能利用所有的建地面積,他們也會盡量給用戶留出更多的公共空間以創造一處更加令人向往的場所。
30:00 祈宜臻女士: 如今,我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社會責任問題以及它是如何開始影響一些開發商的。但香港卻是一個例外,因為只有少數開發商能意識到這個問題,顯然開發商也是要賺錢的。但是我認為貨幣價值并非唯一的價值,社會再投資可能也會是一種長期投資。
這也讓我想起關于可持續發展的第三個話題。社會可持續發展算是可持續發展的一種,但是當我們談到可持續發展一詞時,人們會立刻想到綠色可持續發展或者環境可持續發展,而這些都并不是我所說的可持續發展。那么,我們如何才能使空間發展更具可持續性呢?
31:04 夏樂彬先生: 可持續發展和環保固然重要,但是我覺得讓社會各階層的人在白天或夜晚的不同時間都可享有開放空間才是更重要的,因為這是一種人人都可以享受的生活方式。這樣,在清晨你可以打打太極,然后早上晚些時候你會看到父母帶著孩子,到了中午你又會看到一群上班族,下午又會涌來一群學生。可能有些人只是來逛逛,有些是來下下棋,到了晚上可能還會有人過來打打籃球或者做一些其他運動。所以以一種靈活的方式設計公共空間讓人人享有相同的機會才是我想看到的情景。
33:36 羅健中先生: 我認為在現代城市這已經變得越來越重要,因為我們的城市面臨的主要問題之一就是貧富差距,同時這也是一個全球性的問題。在香港,我們不知道如何解決這個問題,但我認為無論是在倫敦還是在紐約人們也一樣不知道如何處理,因為這是一個大問題。公共空間是讓所有人過上“城市生活”,享有平等的權利和機會去利用公共空間來改善生活的主要區域。無論是在商店還是其他任何地方,人們都可以在那里學習或者是演奏音樂。我認為在未來的5年里,它將成為可持續發展的重要區域。到那時你會發現相比過去5年,空間政治事件越來越多。除此之外,依我看空間政治將成為建筑的另一大問題。同時城市規劃和公共空間也將會是未來空間政治發展的一個重要場所。
34:22 麥艾倫先生: 我們曾經設計過一處非常棒的中國式空間,但它后來卻成為販毒者、酗酒者和吸毒者的完美場所。所以你必須意識到,當你以自己的方式設計一處開放空間時,其中許多封閉空間可能會吸引一些不良人群,因此你必須要注意這一點。最近,我們剛完成一個項目,也特別注意到了環境設計。但同時,在設計這些公共空間時也考慮到人們在享受它們的同時會不會吸引不良人群。
35:08 羅健中先生: 我完全同意這一點。雖然砍掉城市中央所有的樹木非常可怕,但是最終可以擁有更多的開放空間,這樣人們就沒法吸毒或進行毒品交易了。事實上,我們在灣仔做過一項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人不喜歡植物,他們甚至不喜歡樹木,因為有了植物人們就可以隱蔽在里面進行毒品交易,而有了樹人們就可以爬到樹上然后直接跳到人行道上。
36:03 Aisha Speirs女士: 我明白孩子們可以在我們創造的公共空間盡情玩耍并且不與毒販接觸。但是我們生活在一座非常安全的城市,我們不是在討論70年代的紐約,而且香港也不應該是一個讓人擔心會有人從樹上竄出來的地方。
36:50 Suzy Annetta女士: 與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相比,我們所討論的是一個個人居住空間非常緊密的城市,并且公共空間變得更加重要,因此設計和可達性仍然是反映城市人們意愿的主要問題。
37:20 祈宜臻女士: 還有就是在安全提供和貧富分化問題上有一條很好的分界線。但是我們談及城市時,這始終是一個敏感的問題。當我們的生活得到改善,貧困地區也會得到完善,但與此同時一些人也會因此而離開。所以總會有一條精細的邊界將我們與鄉紳化分開。
38.10 祈宜臻女士: 為了實現談論話題的多元化,在此我想拋出一個問題,我知道之前已經談論過廟街,但是關于佐敦谷我們還有一些例子。就心理和多樣性問題,我們討論的其他公共空間類型是什么?城市設計師應該能夠將哪些主要問題匯集在一起,作為創造更加開放空間的一部分?
39:19麥艾倫先生: 我就說說PMQ,這是一個了不起的項目。因為你們所了解的僅僅是使用的多樣性和巨大協同作用,而協同作用是以不同的理由吸引人們只身來到這里。有人會想逛一逛商店,而有趣的商店又有那么多,想要到達那兒又是極其的困難,但你又不得不走過去,而這又意味著需要下定很大的決心,而事實上人們還是很有決心的。
40:13 祈宜臻女士: 有新聞對PMQ項目進行了強烈的譴責,稱該項目本身并沒有產生任何的收益。我們也曾討論過為什么它總是與經濟利益分不開,而且我認為這項方案還是需要一定的補貼。每次談及PMQ項目,我發現對該項目投入的資金還是很多的,但是我認為要想建立一個像PMQ這樣的公共空間,在個人投資和公共補貼上還是應該達到一種平衡的狀態。
40:51 鄧文彬先生: 我個人認為,PMQ項目在場所營造上還是很成功的。但一開始,人們批評該項目,稱完全可以將這塊地用于可盈利的住宅房地產開發,而最后卻被用于建設公共空間。但我們也知道當前這個創意中心的運營商已經承諾為該項目捐贈一億港元。我認為這個項目產生了許多社會價值,比如它除了通過補貼租金的方式而孕育出了一批新興藝術家之外,還沿著好萊塢路創造了一處融藝術和創造性氛圍為一體的空間。
說到補貼,當你的第一想法是通過拆除周圍的建筑來開發房地產時,實際上是可以找到一個平衡點的。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保持原先的發展狀態就代表獲得了巨大的補貼。當然,一方面項目總監可能會持相反的意見,因為他的發展利益與他人不同,但另一方面總會有人愿意為這樣的項目出資。所以我認為,社會應該平衡好兩者的關系,因為我們不可能為事事發放補貼。
44:30 祈宜臻女士: 我們有一位內部人士在這里,你想點評一下檢測值與“其他”之間的差額嗎?
45:00 麥艾倫先生: 關于PMQ項目的另外一件重要的事是開發商需具備一定的項目管理能力。因為在城市,這的確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并且在城市的中央為人們創建這樣一個可呼吸的空間也是一個非常偉大的想法。
45:15 祈宜臻女士: 當然,我認為這也實現了文化與經濟收益之間的平衡,因為要想創建一處成功的公共空間,這些都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47:00 景國祥先生: 我認為人們想要的不光是協調,因為它并不能給予人們足夠的動力遷移到城市。我覺得一座智慧型城市應該既具備適應性特征又具備可持續性特征。看到韓國,我認為我們正在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但是因為所有的城市都在做著相同的事,所以我們需要將自己的風格融入進去。
48:30 祈宜臻女士: 發展我們自己的風格,你有什么好的建議?
48:33 景國祥先生: 我們其實是在現有的城市肌理里建設一座智慧型城市。不過我想看看,各個家庭是如何適應這樣的城市的,因為我認為我們還是缺乏一定的適應能力。
49:21 譚寶堯先生: 我曾專門去過一趟韓國,去看看智慧型城市是如何運作的。我看到人們在許多地方搭帳篷露營,比如公園里和海濱邊。這使我想到我們仍然還在中環搭建帳篷。既然Tris Kee談到風格,我認為我們需要保持自己的風格,但同時也要為一些未知的事留出空間。比如社會互動的自發性,我們應該將其設計為“偶然事件”。
52:14 祈宜臻女士: 我認為,從本質上看應該精心策劃一些活動。比如,回到廟街的話題,每次你去那兒都會有些正式的意料之中的活動,但同時也會在街上發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我認為這一點挺好。香港所有典型的元素,比如密度大、場所多、餐飲業范例PMQ以及藝術中心,都是發生在一座大樓里,不過我們的街道也是非常有趣的。
我們之前一直在討論復興,我覺得要想把香港建設得真正“香港”,復興的想法發揮著關鍵作用。所以我認為我們在朝著“思想性和多樣性”發展時忽略了一些因素,我想聽聽專家們對此的意見。
53:45 溫灼均先生: 我認為香港有許多獨特的特質,這是許多其他地方沒有的。香港擁有許多很棒的郊野公園,人口眾多。不過問題與這兩者沒有真正的關系。郊野公園和城市人口稠密,兩者需要用一種策略更緊密地結合起來。
54:59 鄧文彬先生:回到之前人行天橋的觀點,可能我們都不想要人行天橋。但是我覺得,建設人行天橋很不錯,香港得天獨厚。設計人行天橋時要考慮到人口稠密、多層連接的特點以及如何將兩者聯系起來。我覺得中環自動扶梯事故的原因是,它并沒有打算讓這個地區充滿活力。它只是解決交通問題的替代品,但是快速的人口流動可能引發了事故。如果讓更好的設計師來設計這些地方,他們將會創造出更好的城市體驗。香港大學附近薄扶林對面的那個建筑實在是“丑”。不知道為什么,20年后,它成為了一個復制品,并且還有很多防護欄桿。為什么我們會讓這種事發生?我覺得問題的原因是我們沒有在“城市設計”中加入足夠的城市設計元素,而解決這些主要城市問題的人員又缺少訓練。
從我個人在香港的生活經歷來說,你可以隨意閑逛。就像溫先生所說,從城區到郊野公園也不容易,而事實上兩地是挨著的,誠然更好得連通創造更好的城市。對于我來說這才是“香港風格”。
58:14 夏樂彬先生: 說到城市和郊野公園之間的關系,我找不到人口稠密和港口間的直接聯系。許多發展都是依靠港口,不過它們似乎不相關,我覺得關系是另一個需要強調的重要問題。
58:46 譚寶堯先生: 除了連通的問題,我還想說一下說移動和速度,這才是我們開始把過往車輛和行人隔離開的重點。當你仔細觀察人們時,你會發現他們的速度不同。那么問題就是如何讓速度快的人和速度慢的人并行,而非把他們分開。當這個分割出的區域對連接兩點更方便時,那么街道就失去了活力,所以需要在連通和活力之間找到平衡。
1:00:00羅健中先生: 我認為香港最大的優點之一是,我們都是干涉藝術大師。我們從沒成功提出適合城市的主規劃,無論人們做出如何努力往往都會以失敗告終。但是我們成功提出了可行的解決方案。比如,如果這個地方需要一座橋,那我們就建一座實際發揮作用的橋。我覺得這就是香港的力量所在。我明白當人們說香港沒有落后于上海、北京等世界上其他城市時他們如此自豪的原因。我們更有能力提出不同的解決辦法,這種做法性價比高、行之有效、最終能發揮其作用。這就是我們生活在香港比其他地方更幸福的原因。
1:02:00 何文堯先生: 20世紀80年代,我曾在香港的房屋署工作。那時候有些條款規定政府提供公共住房,公共空間應視為生活空間。因此他們在風景和在公共房屋的購物中心上面投入大量資金。我覺得這仍是對香港目前狀態的一種解讀。我們的家是我們的臥室,公共區域是整個城市的生活空間。
跑馬地一處正在施工的項目有一處地下空間,上面是綠色的坡地,我們提出公眾也可以使用這塊空間。建筑概念很簡單,不過我們花了一年半的時間才得到康樂及文化事務署的批準。另外,我們需要和所有政府部門打交道,這意味著對于一個非常基礎的城市設計,你需要克服重重難題。不過我很高興,新的政府部門似乎思想開放,開始關注城市問題提出不同解決方案。
我認為作為城市設計師,我們不應按照人們使用空間的方式進行設計。我們要做的是提出一個框架,對人們如何使用、如何享用此類空間提供指導。作為一名設計師,我不會根據人們能做什么或不能做什么來打造一處公共空間。我認為我們的工作是為了創造出讓公眾成為掌控者的場所。這才是我認為的真正的公共空間。
1:08:00 祈宜臻女士: 誰才是公共空間真正的使用者?這個問題讓我回到上一個話題。城市設計中一個非常重要的考量就是利益相關者,包括開發者、設計師、政府和使用者。我認為在當前政治復雜和社會交融的現狀下,我們需要讓公眾參與到設計日程中,讓不同城市社區、利益相關者和使用者形成社會凝聚力,創造真正的公共空間。我認為解決問題需要一個更成熟的體制。
1:08:00 鄧文彬先生: 我想分享一下我在公眾參與方面的經歷。在保護啟德龍津橋項目中,我們的公眾參與分幾個階段,在告知公眾這個項目的背景和技術信息后,我們才征求大家的想法和意見。公眾在充分了解后才發表看法,以這種方式討論更加富有成效、更具有建設性,也避免了許多錯誤的假設。
1:12:00 嚴觀偉先生: 從我的經歷來看,一個項目80%的時間都用于處理媒體和公眾方面。公平地說,公眾普遍存在反對開發者的敵對態度,隨之而來的是開發者無論做什么都是錯的。個人開發者和政府間也很難達成聯合參與項目和土地租借。
1:14:00麥艾倫先生: 我們嘗試一開始就向不同的利益相關者解釋清楚我們想做的事、我們的目標、對實際情況的看法以及我們認為需要哪些改進。所以你必須充分了解利與弊、對問題作出良好評估,并且對人們持開放態度。事實上,你永遠不會達成共識,在任何工程上都不要抱此想法。不過你可以讓大部分人們支持你,盡管這是一個費心勞力的過程。
附錄 B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簡介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HKIUD)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HKIUD)成立于2010年6月,我們是一群專業人士,致力以教育、討論及評審來促進城市設計。我們的核心成員均是現有相關專業學會的成員并曾長久參與香港的城市設計。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的會長是施培德博士;負責專業發展、對外事務、公共事務3個方面的副會長分別是鄧文彬太平紳士、李嘉聲先生和何文堯先生;義務秘書是夏樂彬先生;義務司庫是何干忠先生;其他理事會干事包括陳祖聲先生、Stefan Krummeck先生、梁振鐘先生、麥艾倫先生、譚寶堯先生、鄧兆基先生和黃國揚先生;學術顧問是伍美琴教授和田恒德教授;上任會長是林云峰教授太平紳士。
附錄 C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獎項2014年獲獎項目HKIUD Awards 2014 Winning Projects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HKIUD)
香港城市設計學會頒布很多關于城市設計的獎項。2014年,歐華爾顧問有限公司的“活化灣仔舊區”項目獲得了“建成項目設計大獎”;雅邦規劃設計有限公司的“‘中央城市風光’— 街景美化工程”項目和建筑署的“西貢海濱公園”及“赤柱海濱”等項目獲得了“建成項目優異獎”;雅邦規劃設計有限公司的“港島東海旁研究”項目,李嘉聲、倪佩茵、陳子誠、嚴觀偉等的“新加坡榜鵝區整體規劃—城市設計方案”項目以及房屋署(發展及建筑處)的“蘇屋邨重建及發展計劃”項目獲得了規劃/概念優異獎。
Hong Kong Open Space : Discussion and Revelation
Hong Kong, as one of the densely populated cities in the world, has a highly constrained land development system when it comes to planning open spaces in the city. Such a controlled urban planning framework has been a result of its unique social, economic, political and geographical factors. The intrinsic relationship between public and private land ownership constantly challenge the true definition of “public” and “private” spaces for its inhabitants. This paper aims to identify the different urban scenarios related to public and private open spaces and draws references from the Urban Design Roundtable Discussion held by the Hong Kong Institute of Urban Design (HKIUD) in September 2015 to best understand how urban design of open spaces can achieve a more sustainable urban design for the future.
Public open space; Private open spaces; Urban development; Urban design

圖5 / Figure 52014城市設計大獎“活化灣仔舊區”Revitalizing Old Wanchai (Grand Award of Urban Design Awards 2014)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圖6 / Figure 62014城市設計大獎“活化灣仔舊區”—社區參與和街頭表演花絮Revitalizing Old Wanchai (Grand Award of Urban Design Awards 2014) —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street performers highlights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圖7 / Figure 72014城市設計大獎“活化灣仔舊區”—社區參與和街頭表演花絮Revitalizing Old Wanchai (Grand Award of Urban Design Awards 2014) —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street performers highlights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圖8 / Figure 82014城市設計大獎“活化灣仔舊區”—社區參與和街頭表演花絮Revitalizing Old Wanchai (Grand Award of Urban Design Awards 2014)— community engagement and street performers Highlights香港城市設計學會提供.
2015年11月11日
Received Date: November 11, 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