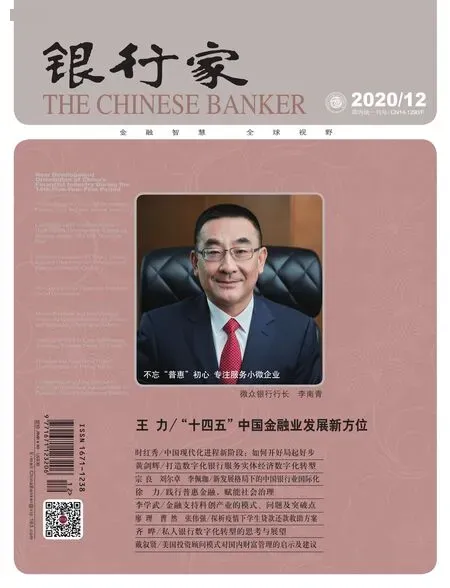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對銀行業監管工作的影響
肖鷹+趙安平
2015年5月1日,《存款保險條例》(以下簡稱《條例》)正式實施,標志著我國銀行監管體制改革又邁出重要一步。《條例》賦予存款保險基金管理機構(以下簡稱“存款保險機構”)較為全面的監管職能,對未來銀行監管工作產生深遠影響。
存款保險機構被賦予監管權的背景分析
按照監管職能大小劃分,各國存款保險機構可以分為“付款箱”型、“成本最小化”型和“風險最小化”型。其中,“風險最小化”型存款保險機構的監管職能和權限最為寬泛,而“付款箱”型存款保險機構基本不具備監管職能。前者以美國FDIC(聯邦存款保險公司)為代表,其不僅負責對存款人進行理賠和機構破產處置,還肩負對特定機構(州立非聯儲體系銀行)的主監管者職能。
理論上,在制度層面賦予存款保險機構監管職權可以和已有的銀行監管部門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監管競爭”格局,有利于促進監管部門積極有效履職,提高監管規范性和透明度,防止出現監管真空和監管寬容問題,從而有效保護存款人利益。但從國際經驗看,只有在一部分銀行沒有其他部門進行監管并可能產生監管真空的情況下,存款保險機構才會被賦予對特定銀行的監管權(如FDIC)。
通過對《條例》的研讀我們可以發現,《條例》賦予存款保險機構較為寬泛的監管權(包括規則制定權、非現場評估權、現場核查權、審慎監管措施執行權和破產銀行處置權等),這種制度安排反映出社會對我國銀行業及銀行監管工作兩方面“擔憂”:一是對利率市場化改革后我國中小商業銀行發展前景的擔憂,既擔心會有一批城商行、農商行和村鎮銀行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破產倒閉,又擔心新建民營銀行經營穩健性和可持續性,希望通過存款保險機構的事前和事中監管維護金融穩定;二是對現有銀行監管機構的效能并不充分放心,認為銀行監管部門監管偏“軟”,在一些重大案件風險隱患的處置上難以杜絕“不愿管、不敢管”現象,對現有銀行監管工作有效性存在疑問。
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對現有銀行監管體制的影響
賦予存款保險機構監管權,促進其與現有監管部門形成有益的“監管競爭”,從而健全我國金融安全網提高監管效能,是《條例》出臺后社會各界希望看到的良性互動局面。但實施存款保險制度對現有銀行監管體制的影響應當受到足夠重視。
監管邊界不清可能降低監管權威。《條例》賦予存款保險機構多項監管職責,但與監管機構在類似職責方面的履職邊界仍然模糊。例如,《條例》規定存款保險機構可以制定風險差別費率。根據國際經驗,風險差別費率通常與銀行監管評級結果掛鉤,若監管評級結果不被認可,將對監管權威性及差別費率制定的科學性造成負面影響。
存款保險機構或在縣域地區成為基層銀行監管的主力軍。目前,我國數千家城商行和農村中小金融機構主要分布在廣大基層縣域地區,當地銀行監管力量相對薄弱,而目前代行存款保險職能的部門在縣域地區擁有大量分支機構和較為充裕的人員及預算安排,將在一定程度上替代基層監管部門的職能。
導致高風險存款機構處置過程復雜化。理論界有觀點認為,為避免因償付存款造成基金損失,存款保險機構更傾向于要求實施再貸款等救助措施,而不希望高風險存款機構清算退市。而一旦救助無效,可能貽誤破產清算時機帶來更大損失,并會因增加基礎貨幣投放干擾正常貨幣政策。
可能造成多頭監管引致監管成本上升。與美聯儲和美國貨幣監理署(OCC)僅承擔部分聯邦注冊銀行的監管不同,我國銀行監管部門職責范圍已經覆蓋全部存款類金融機構,如與存款保險機構在監管職責上不能明晰邊界、有效協調,客觀上容易形成多頭監管局面,造成監管成本上升。
發達國家協調銀行監管與存款保險的經驗值得借鑒
銀行監管機構與存款保險機構間職責劃分清楚,保持溝通協調通暢,是有效降低監管成本、提高監管效能的必然要求。經過多年發展,西方發達國家的銀行監管機構同存款保險機構間已經形成了較為成熟和穩定的協作關系,一些做法值得我國借鑒。
合理確定職責邊界
明確監管范圍。如,美國FDIC與FRS、OCC雖然單從監管職責上看幾乎全部重疊,但三者各自監管的機構卻并不相同。其中,OCC負責監管聯邦注冊銀行(國民銀行)、FRS監管州注冊聯儲成員銀行,FDIC監管州注冊非聯儲成員銀行。FDIC對聯儲成員銀行雖負有輔助監管職責,但并不能替代OCC和FRS的監管意見和結論,從而避免了監管職責重疊。
明確檢查對象。國外多數存款保險機構將檢查或調查對象嚴格限定為有破產隱患的投保機構。如,韓國《存款人保護法》規定,存款保險公司獨自調查或派員參與監管部門檢查的投保機構,須受到喪失清償能力威脅;美國《多德-弗蘭克法案》雖授予FDIC對系統重要性金融機構的備份檢查權,但明確規定該權力不得對經營穩健的機構行使。
明確劃定監管分工
國外銀行監管機構和存款保險機構的監管授權和分工機制主要有兩種模式。一是委托監管模式,即存款保險機構負責制定相關監管標準,具體監管工作則通過銀行監管機構的代理審查實現。如,CDIC(加拿大存款保險公司)制定“金融業穩健標準規定與實踐”系列規定,明確風險、資本和內控管理標準,并通過OSFI(金融機構監理署)對銀行進行代理審查,如果OSFI認為某家機構沒有遵守標準,CDIC有權對其征收附加保費。在委托監管模式下,CDIC可以保持較為精干的員工隊伍,截至2014年末其正式員工只有110名。二是分工監管模式,此種機制下,監管部門和存款保險機構一般采取輪流檢查、結果共享,或者聯合檢查、各有分工的方式對銀行進行監管,例如,FDIC把檢查精力主要放在可能給保險基金帶來損失的問題銀行上,而對穩健安全銀行的檢查間隔較長(有的間隔長達三年),期間則由其他主監管機構負責檢查。
有效開展溝通協調
在明確職責邊界和分工授權的同時,部分銀行業規模較大、金融安全網成員復雜的國家為處理好銀行監管機構與存款保險機構之間的關系,還建立了專門的協調組織及機構間溝通機制。
一是完善議事平臺和機制,建立平等的溝通協調渠道。如,美國在1970年成立了FFIEC,由OCC,FRS,FDIC和OTS(儲貸機構監督辦公室)官員輪流擔任主席,促進各機構攜手提升監管效能;日本則規定其央行和存款保險機構應向金融廳出示檢查結果并允許金融廳人員查閱相關資料。二是統一監管標準和報告形式,降低溝通和協調成本。如,美國各監管機構都采用統一的CAMELS評級標準,而FDIC對其不承擔主監管責任的參保機構則參考主監管機構提供的評級結果以采取相應監管措施和保費標準,從而減輕銀行監管負擔。三是制定法規、協議或工作指南,協調各機構間的監管行為并建立有效的信息共享機制。如,CDIC和OSFI之間聯合設計了一個“干預指引”以協調雙方監管行動;美國OCC、FRS和OTS需要定期將檢查報告提供給FDIC。
科學構建治理機制
目前,世界多數國家的存款保險機構采取公司制形式,很多國家通過吸收其他銀行監管部門進入存款保險機構的董事會(理事會)或管理委員會來加強相互之間的協作。如,FDIC董事長由總統任命,地位與美聯儲齊平,其董事會五名成員當中包含了兩名監管官員,分別來自OCC和OTS,但不包含美聯儲官員;韓國存款保險公司董事會中包括金融監管委員會副主席;CDIC董事會成員則分別來自央行、財政部和OSFI;丹麥存款保險機構由中央銀行管理,金融監管當局負責批準存款保險機構董事會決策,并由監管當局與中央銀行共同協商后確定保險年費標準。
提高銀行監管有效性的建議
為充分體現我國存款保險制度的優越性,降低潛在職責重疊可能對銀行監管和存款保險工作帶來的影響,有效發揮銀行業監管在國家金融安全網建設當中的重要核心作用,切實維護國家金融安全,建議監管部門做好以下三項工作。
完善工作機制,切實提升銀行業監管有效性
一是完善審慎監管規則后評價和更新機制,對相關審慎規則持續開展后評價并及時補充和更新,最大程度實現審慎規則對相關領域“全覆蓋”。二是完善依法監管機制,在工作理念上盡快從行政管理轉向依法監管,在監管組織架構和工作流程設計上要以監管執法為中心,真正做到嚴格執法,樹立監管權威。三是完善現場檢查機制,建立以檢查能力和檢查效果為導向的績效考核體系,引導檢查人員自覺提高現場檢查水平和主動發現問題的積極性。四是完善信息溝通機制,實現監管信息的標準化。可率先制訂監管信息披露規則,通過與相關機構簽訂信息共享協議,有效實現信息共享。
加強頂層設計,處理好金融安全網成員間關系
做好日常監管協調機制的頂層設計。一是完善與風險早期糾正相關的協調機制。如協調有關部門適時召開存款類金融機構監管會議,明確糾正措施的實施方式和步驟。二是盡快厘清現場檢查職責邊界。可借鑒發達國家成熟經驗,由監管部門負責對存款機構進行風險識別,并授權存款保險機構依《條例》對高風險存款機構的存款業務相關領域實施現場核查。
做好高風險存款機構處置的頂層設計。積極推動高風險存款類金融機構處置相關法規或指引的出臺,以有效銜接《銀監法》第三十八、三十九條和《條例》第十九條之規定。相關法規或指引應詳細規定有關部門在存款類機構破產清算工作中的職責分工及合作機制,動用存款保險基金的標準和程序。
參與制度建設,積極推動存款保險機制持續完善
縱觀世界各國存款保險制度的發展歷程,存款保險機構職能定位與組織架構都不是一成不變的,總體發展趨勢是成立獨立公司法人。在我國存款保險制度剛剛確立,存款保險工作機制尚未成熟之時,應不斷推動存款保險制度和機構的健全和發展,切實維護我國金融穩定。一是引導存款保險機構明確機構定位,將職責權限側重于“成本最小化”,即負責存款賠付、破產銀行清算處置和保險基金運作,提高基金運作透明度。二是引導存款保險機構完善治理模式和組織架構,如可借鑒國際經驗,推動存款保險機構成為獨立的公司法人,通過董事會進行公司治理,并在董事會、管理層中引入相關金融監管部門工作人員參與管理。
(作者單位:北京銀監局,其中肖鷹系紀委書記)